資料
歸國後,一邊從事設計、插圖,一邊開始創作圖畫書。佐野洋子曾創作過《我的帽子》、《紳士的雨傘》、《請等一等》等大量的兒童圖畫作品,其中《紳士的雨傘》曾獲產經兒童文化推薦獎,《我的帽子》曾獲講談社出版文化繪本獎。《活了100萬次的貓》是她的代表作。
2004年4月,她因為《活了100萬次的貓》 《老伯伯的傘》等對圖畫書的傑出貢獻,獲得了日本政府頒發的以藝術家為對象的紫綬褒章。她的丈夫,是日本著名的詩人、圖畫書作家谷川俊太郎。
佐野洋子-創作
最後的作品展現四合院
 佐野洋子
佐野洋子《活了100萬次的貓》是佐野洋子的代表作,她的其他作品也以貓為主角進行過創作。但昨天她卻表示,其實自己並不喜歡貓。“大家都把我當作畫貓人,其實我並不喜歡貓,之所以畫貓,僅僅是因為畫狗我擔心畫不好,而貓比較好畫。”
談到作品的創作靈感,她說那時,她只有30多歲,“有一天突然一隻活了100萬次的貓出現我的腦海中,然後這個故事就基本成型,可以說這個故事的創作是一氣呵成。”說到這裡,佐野洋子突然像個孩子似的笑了:“所以說,我也算得上個天才。”
佐野洋子表示,“我要創作一個關於北京四合院的作品,要表現出自己兒時在四合院中看到的四方天空,以及第一次跨出院子時感受到的世界。這將是我最後一部作品。”
佐野洋子-感情
遇到好多次的真愛
《活了100萬次的貓》是一本講述“愛”的書。一位女孩子告訴佐野洋子,她看完最大的感受是希望自己能找到生命中的真愛。隨即她問佐野洋子:“請問您找到生命中的真愛了嗎?”佐野洋子緩慢地說:“愛情經常是這樣的。當你遇到時,你以為是真愛。可過了三年,你突然發現原來那不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遇到過好多次的真愛。”她還表示,很多年後她才明白過來,創作這本書反映了她當時本能的願望。
佐野洋子-來京尋舊
 佐野洋子
佐野洋子2007年5月27日下午在首都圖書館與中國讀者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聚會。69歲的佐野洋子已是癌症晚期,回到出生地北京看看是她最後的願望。在與讀者交流時,她表示雖然自己現在只想好好休息,不想再工作,但她還將創作最後一部作品,在這部作品中她將展現自己兒時的北京,兒時的四合院。佐野洋子對北京感情很深現場:優雅作家傾倒讀者看過《活了100萬次的貓》的讀者都會在腦海中構想過作者的模樣,69歲的佐野洋子應該至少是“老奶奶”模樣的人吧。
但5月27日出現在讀者面前的佐野洋子讓不少讀者吃了一驚,她雖然臉上皺紋很多,也有老年斑,但姿勢挺拔,氣質典雅,讓不少讀者驚呼“好年輕”。在活動中,佐野洋子與讀者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交流,表現始終端莊得體。一直陪同她的編輯苗輝告訴記者,佐野洋子已是癌症晚期病人,能堅持這么久讓她十分感動。佐野洋子此次來京主要是尋舊。因為她出生在北京,並在這裡生活了7年。
因此,回到出生地看一看成了她最後的願望。昨天佐野洋子用發音不很標準的中文說:“北京是我的家鄉,我是北京人。”還表示,如果她會說中文,恨不得現在就成為中國人。活動中,她對北京的回憶感染了不少讀者。“我小時住在西城區口袋胡同甲16號的四合院裡,小時候看天空總是四方形的。我記得有一天中秋節,家裡招待客人,那天的夜空和月亮美麗得讓我終身難忘。”苗輝說,這次在北京佐野洋子還專門找到兒時生活的四合院。
佐野洋子-成長記憶
漂洋過海
 佐野洋子
佐野洋子一個日本女孩兒,1938年生於北京(那時還叫北平)。在西四胡同深處一個有著四棵棗樹的四合院長到6歲後,在一個有霧的初春早晨,被父母帶上火車遠行。那條帶她離開北平的路,有好幾個月那么長,蜿蜒北上,還漂洋過海,最後的終點是戰爭完敗之後的日本。
童書界才女
60多年後,她早已是那個島國萬眾矚目的“童書界才女”:她的書能賣到150萬冊;她的作品被收入日本小學生課本;因為她對圖畫書的傑出貢獻,日本天皇頒給她紫綬帶勳章。她有著日本人的名姓、日本人的國籍,她做了日本人的妻和母親,她也已經想不起咿呀學語時那些悅耳的京白,只會用日語發音。
可是她,從不認日本是她的故鄉。
北平的女兒”
2007年,當年北平四合院裡孤獨望天的6歲孩子已經年近古稀,她得了不能治好的病,沒人攙扶再不可能遠行。69歲就要到來的這個夏天,她收拾了行囊,讓朋友陪她跨海西來———在生命的日暮,“北平的女兒”想再看一眼故里。
故事簡單。聽過了要忘記卻難。
四合院
於是5月最後那幾天,初夏的北京,白日正一天天變得悠長,我們跟隨了佐野洋子那些烈風和驕陽下的足跡:四合院,她小時候住過那種,有魚缸和葡萄架;京郊順義,她父親當年做農村調查時到過的村莊;口袋胡同,她至今畫得出記憶中的街巷,卻再不見幼時的院落和鄰里;還有故宮和什剎海,童年那些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曾經她被父母牽著手,看到過那裡許多美景……
 佐野洋子
佐野洋子“老太太想看些古老的東西。”她同行的人說。可究竟什麼,是這個城市“古老的東西”,那么美、讓她懷念至今?多年以前,到底這世間,曾經存在過一個怎樣的北京?哪些東西,我們未曾珍惜,我們不再擁有?突然發覺,這么多年,自己是第一次真正地想知道。
老人在北京呆了6天。
老人回國兩天后,我收到發自日本的郵件,老人給我她小時候的照片。五張,照片發黃,看得我說不出話—那時候的老北京,那時候的人,那時候的時光。一個同事看了,說:“忽然很懷念梁思成。”
七十年。一座城和一個人,逝去的美麗和不老的鄉愁。
車子開到平安大道,正是黃昏時分,她看到路兩邊的青磚灰瓦,一下子就哭起來。24日,北京的天空微微揚沙。
佐野洋子走出機場,腰板筆直,利落的短髮,白衣飄飄。讓之前準備好要看到一個病弱老太太的我們,都心裡暗暗吃了一驚。
建國50周年大慶
這並不是她6歲遠行之後首度回京。第一次是1999年,建國50周年大慶。“那次我們也是從機場出來,車子開到 平安大街,正是黃昏時分,她一看到路兩邊青磚灰瓦的平房,一下子就哭起來,哭得可痛了。我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也不敢問。”唐亞明是佐野洋子的朋友、也是她書的中文譯者,8年前那一刻在唐先生記憶里清晰如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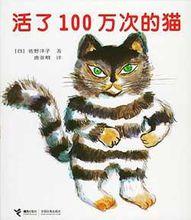 佐野洋子
佐野洋子二度來歸,佐野洋子望向窗外的眼神已經沒有任何陌生。向她提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天氣:“這樣的沙塵天,記得小時候在北京有過嗎?”她說有啊有啊,她記得那些起風的日子,不管門窗關得多緊,塵土都會鑽入縫隙,桌椅窗欞,用手抹一下到處都有細細的一層。她尤其記得那時街上“儘是駱駝”,那些龐大動物無比溫順的眼神之上,眉睫間總是掛滿塵沙。
有的駱駝給城裡運來水。“我小時候北京是沒有水的,都是人用車拉了木桶到胡同里來賣水。”那時稚齡的她曾因為淘氣把木桶的塞子拔掉,失去了水的賣水人在槐陰里的小巷佯裝追打。
“關於老北京的事你們儘管問我!”晚上的洗塵宴,被擺在大取燈胡同的格格府,一座幽美的三進老四合院裡,這樣的安排讓佐野洋子的心情儼然“找到了主場”般大好。“我小時候那個北京,跟現在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今天世界上的大城市都很像,北京跟東京、洛杉磯幾乎分不出來。可我那個北京是有城牆的,人們需要從四個城門裡出去。我的記憶力特別好,小時候的事我都記得。那種露天的理髮店你們見過嗎?夏天讓人昏昏欲睡的午後還有黃昏,走街串巷的理髮匠的鋼叉震動出悅耳的聲響,人們聽到了就去理髮。還有那種鋦碗,現在還有嗎?你們有沒有見過?”
《我的父親母親》
本來想要“搶答”的,但最後還是有些氣餒地收了聲。是,我“見過”鋦碗,那種古老得有些神奇的工藝。可那是從張藝謀的電影《我的父親母親》里、阿城的隨筆里。這,能算“見過”嗎?“我記憶中那個北京已經完全沒有了。那真是世上最美的城市。”迎來佐野洋子那夜,最後腦子裡迴旋著她這句嘆息,跟她別過、回家。被一個外國人這樣熱愛著自己身在的城市,溫暖感動之餘,為什麼還有那么點兒“受挫”?難道是因為被她證明了自己有那許多無可挽回的“錯過”?
“北平是命運將盡的一種奇觀,一種中世紀的殘餘。在這奇妙的城牆中,藏有若干世紀的寶物和掠奪品。在這城市中,有前朝的文武官吏,有學者和地主,有僧侶和匠商,有談吐高雅的洋車夫。這城市有活潑的溫泉,有蔥鬱的秋果,有在霜雪滿樹和結凍的湖上閃耀的冬季陽光。這城市有永久的退讓和輕易的歡笑,有閒暇和家庭愛,有貧乏和悲慘,有對於垢污的漠視。然而這地方也有出乎意外的壯舉,革新的學生們為全民族製造鬥爭的標語。由戈壁沙漠吹來的大風,使得華美的廟宇和金黃的殿頂蒙有最古老的生命的塵土。”
《城市季風》
這是另一個外國人斯諾的北平印象,我在楊東平的《城市季風》中與它相遇。捧讀之際,京城的夜正大風,仿佛有舊時塵沙,穿過70年的歲月,直撲上我的窗欞。
田園已蕪,可父親當年訪問過的農人還活著,曾經的18歲少年已是80多歲的老人
25日,大風。目的地是順義沙井。一次尋父之旅。
“我出生在北京,北京是我的家鄉,我是北京人。”這是佐野洋子每每向中國讀者們介紹自己時的開場。而父親佐野利一,則是這一切的原因。
《中國農村調查》
“我的父親很喜歡中國,在大學攻讀中國歷史,研究中國革命、研究孫中山。他在戰爭之前就來到中國,在北大做客座教授。後來加入滿鐵調查部,以毛澤東為榜樣,致力中國農村調查。他們七八個人的調查小組,歷時七八年,調查了北京周邊以及河北省的6個村莊。”佐野利一1947年離開北京回到日本,上世紀50年代出版了六大本專著《中國農村調查》 ,在日本非常轟動。當時世界上還沒有人對中國農村做過如此詳盡的調查。
當年,父親在做著怎樣有意義的工作,佐野洋子是不懂的。那時,她只是出生在北京四合院裡的一個小小女孩兒,和同樣年幼的哥哥一起被母親呵護著嬉戲成長。印象里那個瘦高個子、穿長衫、面貌英俊的父親經常離家,但每次出去工作回來,都會給她帶很多禮物,經常是一些京城見不到的點心,而且也沒有耽誤過為她的小哥哥修理火車頭玩具。
那時,她們的家境應該是優渥的吧。當年北平,人文薈萃、群賢畢至,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種國立大學的教授,月薪在300元以上。而那時北平的生活標準和物價水平是,“四口之家,每月12元一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
“我的父親喜歡花,喜歡八月十五在家裡聚會,好多人都來賞月。所以小時候北平天空的美麗和月亮的美麗是我永遠難忘的。”這樣一個父親,後來經歷了一個不得不離開中國、東渡回國的日本人必然遭受的諸多艱辛(因為需要在沒有財產、沒有職業的基礎上完全重建生活),最後在她19歲那年因病去世。半個世紀後,當佐野洋子自己也沉疴在身,她有一個心愿:想看看父親當年工作過的村莊。
巨大的懸念
順義沙井村在首都機場東北不遠的地方,今天去往那裡一路是大道通衢。而70年前,佐野利一卻曾在工作途中因為搭乘的卡車翻車,險些失去視力。佐野洋子一路沉靜,前方她即將到達的願想之地是一個巨大的懸念,孤懸在所有人的頭頂。最終,車輪止處,是一片樓。沙井村田園盡蕪,完全變成了商品房基地。大家都有些錯愕,倒是佐野洋子大笑下車,對著那片樓拍照不止。她說:“我想到了會是這樣。”
但後來的境遇卻又峰迴路轉。就在那片樓群里,佐野一行居然尋訪到了當年接受過佐野利一他們調查的農人。83歲的楊慶余在佐野洋子隨身帶來的父親書稿的複印件上,指出了他父親楊正和叔叔楊源的名字,每個名字後都詳細列出家裡人口多少、地多少、家中的財產,比如一頭驢、一輛大車。他86歲的妻子劉玉英慈眉善目,回憶當年曾為來調查的日本人做過飯,“給他們吃飯全是白面”。59歲的女兒楊秀琴則在日本人的書稿上看到了楊家祖墳的照片,當年那一棵大槐樹下的四座墳塋今天早已不見。臨別,佐野洋子把那頁紙鄭重地留下,送給這些純樸的人,幫他們貼補記憶。在另一家,當年18歲的張林富———接受調查者中最年輕的家長———還活著,而今已是84歲的老人,他的老伴兒拿出當年日本人送給他們的禮物,那一對不鏽鋼西餐湯勺,66年之後依然好用。
那是佐野洋子最勞累的一日,後面大半程都需人攙扶行走。但也是她自言最高興的一日,她在每一戶與那些老人細細言談,她關心當年幫助過父親調查的人們,在後來的歲月里有沒有因此受到磨難,她關心失去土地後的他們,今後生活何以為計。她問:“您有幾個孩子?”“日本人走了以後,農村變化大嗎?”“後來都種什麼?”“您現在幸福嗎?”那一刻她目光中有複雜的溫情,注視著面前那些60多年前注視過她父親的眼睛。
那天最後當我們要上車離開,回頭,忽見83歲的楊慶余不知什麼時候戴好了帽子,叫女兒攙扶著摸索到樓下,靜 靜地站在樓口,準備目送遠客。佐野洋子讓人攙著復又上前與之執手,兩個言語不通的暮年之人,在午後吹得白
83歲的楊慶余和佐野洋子
楊樹嘩嘩作響的夏日大風裡顫顫地相對笑著頷首。一個中國農夫、一個日本作家,生命深處居然還存在這樣的交集,相隔了60多年的歲月和浩瀚大海,他們尋找、相遇,現在要別離,那一點點緣分像流星,瞬息天際,但是他們仍在彼此珍惜。
棗樹陰里的長巷似是布著煙靄,斜陽下不知誰家吹笛,“我就當這裡是我的家了”
26日,最高氣溫三十七度二。西四小口袋胡同。回家的路。
“西城區口袋胡同甲16號”。這是6歲那年被父母帶走一去不回的地址,佐野洋子在北平的家。也是她古稀之年最後一次回家想要找到的地方。
“口袋胡同”
上網查,北京城叫“口袋胡同”的地方有8處。而且,中間隔著63年的城市變遷。而我們可憑藉的,只是一個69歲老人6歲之前的記憶,比如,“四合院裡有四棵並排生長的棗樹”。
最先去的,是西起西四北大街的“前口袋胡同”。在胡同頂頭兒,佐野洋子居然遇到了故人———78歲的白英魁老人認出了這個8年前就來過一回、尋尋覓覓想要找到小時候的家的日本女人。那次,老人還曾請佐野一行進家小坐。這回,他在我們離開時站在銀杏和槐樹陰里一臉慈藹地揮手,說:“甭著急,這回準能找著。”
在北平四合院裡度過的童年,是佐野洋子心中,這一生最好的時光。她記得父親的葡萄架,還有秋天早晨的牽牛花,那是四合院裡的北平人最尋常的享受—“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著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靜對著像喇叭似的牽牛花的藍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夠感覺到十分的秋意。”
她記得被父母領著去買小金魚,魚市里舖排開來一眼望不到邊的魚缸,和端著小魚欣喜地回家的自己—“在那個地方兒,常人家裡也有石榴樹、金魚缸,也不次於富人的宅第庭園。”“北平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也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和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周都有空閒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
郁達夫、林語堂、老舍,佐野洋子固然讀不懂文人們這些優美的漢語,但是那樣的生活之美卻只有她曾親見親歷。
她記得家所在的那條胡同是小石子鋪地,會在月夜反射著月光。那上面走過她那印象中“特別愛買東西,天天去王府井”的美麗母親,和溫婉順從、視她如己出的保姆,也跑過那些喜歡滔滔不絕說笑話、以文明識禮著稱的北平洋車夫—
“他們的生活之苦,也難以形容,但是無論他怎樣的汗流浹背,無論他怎樣的精疲力竭,他絕不會以失和的態度向你強索一個銅板;你若情願多給他一兩枚,他會由丹田裡發出聲音來,向你致誠摯的謝忱。如果你看見洋車夫在休息時讀書閱報,在他破陋的住所前還栽種著花草,也都不應驚訝。”
還有那些勤快的小販們,尤其冬天,不管白天還是晚上都會聽到他們叫賣甘美圓潤的凍柿子的吆喝聲,還有她小時候最愛吃的冰糖葫蘆,那串串鮮紅的甜蜜令她至今懷念,儘管,她已經不會說它的名字。
那天,藍天如碧,烈日灼人。佐野洋子堅持走著,一路上都在回憶。坐在大紅鑼廠胡同道邊稍事歇息時,也在根據印象手繪地圖,她記起距家不遠好像有一所女子中學,出了胡同有一條當年走電車的路。最後,當我們走進太平橋大街東邊的小口袋胡同,喧囂的市聲一下子變遠,下午四五點時分,棗樹陰里的長巷似是布著煙靄。來來回回跑著、急著四處打聽想幫她找到“家”的我們,曾經收住腳步聽斜陽下是誰家吹笛。“我有感覺,應該就是這兒了。”大家都按捺著興奮等待答案揭曉。
然而最終,還是沒有奇蹟。“甲16號”院早已不存。佐野洋子卻似乎已經心滿意足,她望著那條胡同:“就是這裡吧,我就當這裡是我的家了。”
《四方形的天空》
5月29日那天,佐野老師是很高興地走的,臨別告訴我,這人生最後一次的北京之行,她沒有遺憾。
她想再住住四合院。北京那種四合院式的旅店少到搶手,只能讓她住兩晚,而且那裡臥具的顏色和房間的裝飾更像不高明的電影布景,可她已經很開心。她說回去後,她要寫一本關於老北京的書,那可能是她此生最後一個繪本了,會叫《四方形的天空》,那是在北平四合院裡做小女孩兒時,她眼中天空的樣子。
她去遊了故宮。太和殿在修,她也只能坐著輪椅。她看著碧空、黃瓦、紅牆間飛翔的雨燕,驕傲著中國人的驕傲:“中國文化真是太豐富、太輝煌了。你看日本皇宮是那么的單調、樸素。日本當年真是太笨、太傻了,它怎么會想到要侵略中國,它怎么會認為它能夠戰勝中國!”
什剎海
她在離開北京的前夜去什剎海,那夜有很亮的月光。“在日本,我總覺得自己是個沒有故鄉的人。中日之間有過那么不幸的過去,可我心裡只有北京。我知道老北京的樣子,那是那么美好的家……”
“要是我也像你會說中國話就好了,我就不走了,我就留下……”在機場,佐野洋子笑著跟我們告別。童年已逝,故鄉已遠,那種櫻花般淡淡清香,繁盛留戀,又可以寂靜而坦然地走向離別的感情,神性般安詳。
被翻成中文書
佐野洋子被翻成中文的書,叫《活了一百萬次的貓》。那個著名的繪本,講的是一隻活過100萬次的貓,最後守在逝去摯愛的身邊,安然地辭世。
那是她為孩子們做的繪本。但聽說,更多是大人們讀了會流淚。
活了100萬次的貓
不死的貓
有一隻100萬年也不死的貓。其實貓死了100萬次,又活了100萬次。有100萬個人寵愛過這隻貓,有100萬個人在這隻貓死的時候哭過。可是貓連一次也沒有哭過。
發動戰爭
有一回,貓是國王的貓。貓討厭國王。國王愛打仗,總是發動戰爭。有一天,貓被一支飛來的箭射死了。正打著仗,國王卻抱著貓哭了起來。國王仗也不打了,回到了王宮,然後,把貓埋到了王宮的院子裡。貓還曾經是水手的貓、曾經是魔術師的貓、曾經是小偷的貓、曾經是孤零零的老奶奶的貓、曾經是小女孩的貓,他被鋸死過、被狗咬死過、老死過,還被背孩子的帶子勒死過,不過,他已經不在乎死亡了。
後來,貓不再是別人的貓了。他成了一隻野貓。貓頭一次變成了自己的貓。不管是哪一隻母貓,都想成為貓的新娘。有的送條大魚當禮物。有的獻上新鮮的老鼠。還有的去舔貓那漂亮的虎皮花紋。可貓卻說:“我才不吃這一套!”因為貓比誰都喜歡自己。
100萬次
只有一隻貓連看也不看他一眼,是一隻美麗的白貓。貓走過去說:“我可死過一百萬次呢!”“噢。”白貓只說了這么一聲。第二天、第三天,貓都走到白貓的身邊。有一天,貓問白貓,“我可以呆在你身邊嗎?“行呀。”白貓說。就這樣,他一直呆在了白貓的身邊。白貓生了好多可愛的小貓。貓再也不說“我呀,我死過100萬次……”了。貓比喜歡自己,還要喜歡白貓和小貓們。
小貓們很快就長大了,一個個走掉了。白貓已經成了一個老奶奶了。貓對白貓更溫柔了,嗓子眼兒里發出了“咕嚕咕嚕”聲。貓想和白貓永遠地一起活下去。有一天,白貓在貓的身邊靜靜地不動了。貓頭一次哭了。從晚上哭到早上,又從早上哭到晚上,貓哭了有100萬次。一天中午,貓的哭聲停止了。這一次,貓再也沒有活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