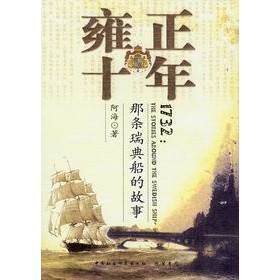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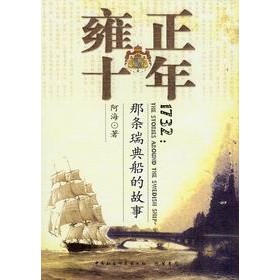 《那條瑞典船的故事》
《那條瑞典船的故事》作者簡介
阿海,本名桂民海,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後獲得瑞典哥德堡大學 歷史系 博士學位,從事北歐歷史及文化的研究,並於瑞典、丹麥各大學教書研究多年。曾出版《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史略》、《北歐的神話與傳說》、《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封建主義問題》等。現為歐盟戰略諮詢顧問。
內容欣賞
第一部分:
下船幹活和看守倉庫的船員,畢竟是少數;大量的船員,還是要生活在船上。雖然都是職業水手,長期待在船上,想來是一件很憋悶的事情,好在不許洋人下船的理論,主要用於糊弄皇上。當地的官府,對這一條根本做不到的禁令,基本上是眼開眼閉。所以船員無聊的時候,大可以下船,在黃埔村一帶,四下溜達。黃埔村也算個古老的村莊,早在元朝便有大戶人家遷徙而來;當地有胡馮梁羅四大家族,也建有不少祠堂,這種有趣的中國建築,想來也是十分吸引洋人的。
虎門口的一陣槍聲,藍旗國的外洋船到港了
雍正十年,西曆一七三二年,出夏入秋,一陣槍聲,突然在虎門口附近的珠江水面上響起。槍聲響了八下,又戛然而止。一艘停在虎門關前的外洋大船的甲板上站著八名高大魁梧、金髮碧眼的洋人軍官,手舉西洋火槍,依次朝天鳴放。另一側,一群綠營兵勇,簇擁著幾個胥役打扮的人物,剛剛上了這條外洋巨船。
這是外洋船的慣例,鳴槍歡迎粵海關虎門口的官吏按例上船檢查。雍正年間,西洋大船前來廣州貿易者,每年有近二十條之多。外洋船到,先泊於澳門外的洋面上,派人前往澳門前山寨的海關關口投訊,並延請海關衙門的引水兩名,其中一名上船引航,另一名則駕快船,先行至虎門口稟報來船的情況。虎門地勢獨特,兩側山頭虎踞,仿佛是老虎的兩顆牙齒,攔住珠江水域。既為海防天險,朝廷向來駐有一協綠營水師,由一名協統,領左右各一營,兵勇數百,進行守衛;粵海關同時設虎門關口,外船到虎門,必拋錨等待,由虎門口的海關胥役,在綠營的護衛下,清點船上的人員刀劍槍炮,逐一登記造冊。檢查畢,大船過虎門,泊於十數里外的黃埔錨地。
引水來報,這條船在前山寨投訊,自稱來自瑞典國,系首次來廣州;領船前來的洋人首席大班,叫做柯林·坎貝爾(ColinCampbell),卻在雍正四年來廣州做過貿易,所以也懂得前後規矩。果然,那艘自稱為瑞典國的外洋船離虎門關不遠,就拋錨等待檢查;海關胥役上船,又鳴槍八響歡迎;看上去,他們和英咭利國、法蘭西國、紅毛(荷蘭)國的其他西洋貿易船,沒有什麼區別。大船上的洋人,這時都上了甲板。這些洋人顯然是第一次來廣州,大都環顧四周,眼神中透著新鮮和詫異。那些洋人大多個子高大,頭髮金黃,臉膛兒很紅,似乎也有點靦腆。為首的大班坎貝爾,則粗壯胖大,說話和做手勢十分誇張。坎貝爾顯然對胥役的套路,十分熟悉,故在胥役們清點之前,就命人端來一個茶盤,茶盤裡面放有茶水,角上一塊紅布,包了幾塊銀洋。銀洋進了口袋,為首的胥役,用洋涇浜英語客氣地和坎貝爾寒暄起來,其他幾個胥役,就開始清點人員槍炮數量。瑞典船人數將近一百,火炮二十門,火槍也有不少支,清點造冊,也花了少半晌工夫。坎貝爾耐著性子,等到清點結束,又命人給胥役和兵勇,送上四瓶洋酒,算是感謝檢查順利結束。緊接著又是一陣槍聲,同樣是八響,歡送海關胥役和兵勇下船。官兵們帶走了引水,卻在船上留下了兩名胥役。
藍旗國外洋船遭遇颱風,並終於找到了澳門
這條船懸掛藍底黃十字國旗,船名是“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idericusRexSueciae)。彼時來廣東的外洋船甚多,船名固然是繁複異常,旗號也有七八國之多;當地人為了易於辨別,大都按照旗號之顏色和形狀,予以區別。比如奧地利,稱為雙鷹國,丹麥稱為黃旗國。瑞典國旗以大幅藍色為底,自雍正十年以後,幾乎每年都有外洋船前來貿易,當地人即稱之為“藍旗國”。這條藍旗國的外洋大船,是年陽曆二月九日,自瑞典港口哥德堡啟航,經過半年的航行,堪堪於八月底,到了南中國海澳門一帶的水域。從哥德堡到澳門附近,歷時半年,尚算順風順水,靠的是強勁的信風,這個季節,正好由西向東。八月二十八日,船到澳門西南幾十海里的地方,看到了一條正在航行中的中國帆船
第二部分:
秉圭是上三旗貴族,早年就官居廣西巡撫,所以府中自然有許多家人。所謂家人,大都是滿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他們在內是奴才,在外則是威風凜凜的大管家,經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權力。主人官當大了,也會提拔這種奴才,出去當官。有清一代,許多官至一品、位尊權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
當年這翻譯的水平,是否足以把坎貝爾先生的話,源源本本地翻譯給祖秉圭聽,很難判斷,想來大意還是明確的。問題是祖秉圭一是對瑞典,或者說藍旗國,幾乎毫無所知。按照粵海關的規矩,對和外國建立邦交關係,向來也沒有興趣;二是坎貝爾覲見祖秉圭的時候,正好趕上這位海關監督大人心情最為不好的時候。廣東總督和巡撫聯名參奏他貪墨海關稅銀,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狀。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這正是瑞典船的故事中最核心的情節,下文自當細述。
祖秉圭雖然心情大大地不好,但是還是很有風度。按照坎貝爾的說法,他對藍旗國外洋船的到來,表示高興和歡迎;承諾藍旗國的外洋船,也將一體享受其他國家貿易者在這裡的所有權益。最後,他祝願藍旗國的外洋船生意成功,財源滾滾。又送了這些洋人大班們幾塊絲綢,作為禮物,鏇即端茶送客。
祖秉圭官至二品,自然是官場老手,當海關監督也有數年,所以雖然不見得熟稔外交事務,卻也說得十分得體。其對洋人大班所說,基本是一些套話,放在每個國家的外洋船大班頭上,都毫無破綻。祖秉圭同時對坎貝爾提出的建立友好邦交關係,以及他的“瑞典國王特命全權大使”的頭銜,顧左右而言他,不置一詞,也算避開了這,一政策性的話題。想來這次接見,歷時很短,屬於禮節性的接待,海關監督大人,總共也沒有說上幾句話。否則依照坎貝爾的性格,肯定要在他的日記中,大大地寫上一筆。接見雖然簡短,而且是禮節性的,這次接見的意義卻十分重大。坎貝爾的“瑞典國王特命全權大使”的頭銜貨真價實,祖秉圭則是大清國負責外洋貿易的最高官員。所以儘管坎貝爾是曾經到過廣州的陳年老酒,儘管他是一個剛剛加入瑞典國籍不久的前蘇格蘭人,這次會面,還是意味著中國和瑞典兩個遙隔萬里的國家,有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觸。雍正十年西洋歷九月十日這一天,也就翻開了中瑞關係史的第一頁。
黃埔的丈量船隻儀式
祖秉圭擔任海關監督時的粵海關衙門,顯得效率相對很高。就在坎貝爾等覲見海關監督大人的第二天清晨,藍旗國外洋船的保商陳汀觀就通知這些大班們,海關監督大人當天將派人前去丈量船隻。於是,坎貝爾一眾,大清早就急急趕往黃埔,藍旗國外洋船的停泊所在,等候海關監督衙門官員的到來。崇義行行商陳汀觀和他們同船前往。
卻說丈量船隻,在廣州的外貿活動中,是一個相當隆重的儀式。這個儀式,既體現了大清王朝對外洋來船的理論和政策,又是粵海關徵收來船固定稅的一種方法。廣州一地,向來是中國通商重地,但是清朝以前,廣州的對外貿易,多少帶有一點中華屬國前來天朝進貢的色彩。所以這個丈量船隻的儀式,十分誇張和形式化:既象徵著泱泱中華大國,懷柔夷人,澤被四海,又標誌著外洋船到廣州以後,正式開始貿易的起點。
第三部分:
廣州的地主士紳,想來多少有點看不起行商,甚至於不屑為伍。讀書人的傳統,重文而輕商,雖然也講究書中自有黃金屋,但是得到這黃金屋的方法,一定是要考取功名,先當官,後貪污,才逐步達到這人生理想。行商們靠和遠夷洋人貿易致富,雖然會講咿哩哇啦的洋話,卻不會吟詩作賦,根本是渾身銅臭的俗物而已。
但是如果外洋船不交關稅,或者是對關稅問題產生了爭執,到了回程季節,如果不給外洋船頒發大票,卻也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對於外洋船來說,固然錯過了信風,不能按期回到歐洲;對於海關衙門甚至督撫來說,卻是犯了中外交通的大忌。蓋洋人不能隨信風而走,就要在廣州越冬,這不僅沒有先例,而且長期留在廣州,容易滋事生非,皇上怪罪下來,海關監督也好,督撫也好,都得吃不了兜著走。
最終放關的大票限制不了外洋船,反而會弄得兩相尷尬,像楊文乾這樣的能員,就動出比較刻薄的腦筋,轉而鉗制洋貨行。洋貨行當中,實力不足的,也不足以鉗制,所以任用其中規模較大的六行進行鉗制。這個鉗制的辦法其實是很妙的,外洋船到港,先要找這六家“行頭”之一,作為保商,才能貿易。出了問題,唯這六家是問。外洋船該繳納的關稅貨稅,完全可以落實到這些洋貨行身上,因為他們規模和實力不小,所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對於這六家洋貨行來說,被稱為“行頭”,固然多了一項負擔,但是也增添了一份榮耀。即使商人不重榮耀,畢竟只有這六家,才能給外洋船作保,生意上面,也多了一些機會。外洋船找了一家洋貨行,而且把辦事處設在該行裡面,不從這家洋貨行購買大量貨物,於情理上面,也有點說不過去。只是這樣一來,洋貨行當中不免有點兩極分化,使得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楊文乾動出這樣刻薄的腦筋,不愧是個能員,也堪稱對夷務十分練達。
但是這“行頭”的資格名目,都掌握在海關監督大人手中,所以“行頭”的數量,也多有變化。雍正六年,英國外洋船到港,得知這樣能夠包攬外洋船的大行只有四家。至雍正七年祖秉圭上任粵海關監督,仍是沿用了楊文乾的老辦法,選了五家大行,作為外洋船的保商,只是更改了一個名目,稱為總商。西文檔案中,楊文乾的“行頭”稱為HeadMerchant,祖秉圭任命的則稱為ChiefMerchant,因此也有可能叫“行首”。但是沒有找到中文檔案上有明確的稱呼,所以這裡稱為總商。
祖秉圭所選的五家總商,是為廣順行的陳壽觀,資元行的黎開觀,崇義行的陳汀觀,孚德行的陳芳觀,還有一家洋貨行的老闆李秦。李秦的這家洋貨行,大概有了什麼突然的變故,很快連自己的洋貨行也沒有了;李秦本人則轉而給財大氣粗的廣順行當了總賬房。孚德行的陳芳觀因為得罪了海關監督大人祖秉圭,雍正八年就給取消了總商的資格。這在接下來祖秉圭的故事里,還要講到。
五去其二,雍正七年任命的總商,只剩下了三家。但是到雍正十年,裕源行的張族觀,肯定也是總商之一,因為雙鷹國外洋船的大班,找了張族觀當保商,並且在裕源行里設立了夷館或者說辦事處。“9月15日:同一天早上,就在我們簽了茶葉契約之後,奧斯坦德公司的大班們到了。他們直接去了張族觀的行里,我們也在那裡見到了他們。”如升行的大官Quiqua在楊文乾手裡就是一家“行頭”,但是雍正七年沒有在祖秉圭手裡當上總商,然而他在雍正十年卻非常活躍,也是重要的行商之一。是否也成了總商,沒有明確的證據。
第四部分:
卻說雍正十年,還有一則兩個金元寶的故事,也充分反映了那個時候普遍的做派。紅毛國外洋船的首席大班舒爾茨(Schultz)和一個行商簽訂了一單茶葉契約,事先說好,每擔茶葉另外加價二兩銀子,然後這個行商給舒爾茨兩個金元寶。但是這位舒爾茨先生事後發現和黎開觀做同樣的生意獲得的回扣更多,因此也就撕毀了契約,改同資元行簽訂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