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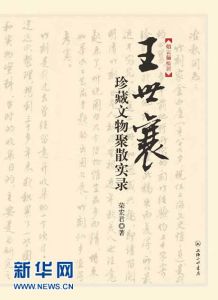 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
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本書大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分是王世襄先生的生平介紹,語言輕鬆活潑,可讀性強;後半部分是抄家檔案(原檔案圖片和還原文表對照,一目了然)和精選王世襄收藏之物。這對於研究王世襄先生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這是一部亦史亦論的專著,也是王世襄先生去世後,第一本研究其學術歷程的著作。
現今收藏很熱,王羲之草書《平安帖》拍出3.08億的天價。而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一直備受收藏界的關注。2003年王世襄先生委託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他的收藏之物,所拍之物無一遺留,全部以高價拍出。轟動了收藏界。在王世襄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為期3天的北京匡時五周年秋拍12月4日在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開幕,這次拍賣會上設有“王世襄藏爐”專場。相信7年以後的今天,這些文物定會身價不菲,在拍賣史上再創奇蹟。2004年,著名青年畫家榮宏君先生在一次偶然中得到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間的全部抄家檔案資料。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逝世的訊息傳出,出於對他的敬仰,榮宏君先生花了一年多的心血編寫了這本書,以紀其逝世一周年。
王世襄簡介
 資料圖片:王世襄賞《葫蘆鴿哨》
資料圖片:王世襄賞《葫蘆鴿哨》王世襄,1914年生於北京,祖籍福建省福州市閩侯,號暢庵,堂號儷松居。著名學者、收藏大家、文物鑑定家、明式家具研究界泰斗。曾任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全國政協第六、第七屆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1966年,“文革”的風暴席捲之初,王世襄耳聞目睹京城紅衛兵“破四舊”的“壯舉”,已經預感到家裡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銅器、鴿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會被劃入“四舊”之列,遭到滅頂之災。王世襄被迫起來“自我革命”。他主動跑到國家文物局,請求來抄家。他心裡不願意與這些朝夕相處的文物分離,但又不忍心看到它們毀在家裡。王世襄這種明智的選擇使自己的珍品躲過了一劫,並在日後又重新收回了絕大多數的心愛之物。著有《髹飾錄解說》《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鬥神作》《錦灰堆》(七卷)《中國古代音樂書目》《中國畫論研究》《竹刻藝術》《中國美術全集·漆器》《北京鴿哨》《蟋蟀譜集成》《說葫蘆》《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等三十餘部專著。2009年11月28日,於北京去世,享年95歲。
作者簡介
 榮宏君
榮宏君榮宏君,著名青年畫家。1973年生於山東省曹縣,幼喜翰墨,性近文史,是著名學者史樹青先生的弟子,並與國內美術、鑑定名家交往頗多。他現任全國青聯委員、北京朔源文物鑑定中心主任,著有《榮宏君畫集》五種、美術史論專著《世紀恩怨:徐悲鴻與劉海粟》等。
目錄
煙雲小記(代序)/1
民族文化的註解者(自序)/3
引子/1
第一章名門世家/6
家族顯赫/7
第二章風雨人生/27
南下受挫/27
中國營造學社/29
為國索寶/36
出使日美/41
第三章悲情歲月/50
華北革命大學學習/50
王世襄與故宮博物院/51
筆耕不輟/62
閉門治學/75
抄家/81
第四章王世襄“文革”抄家檔案/92
附錄/306
參考期刊、專著、文獻一覽/351
王世襄大事記/354
後記/357
贅言/361
煙雲小記(代序)
黃苗子
半年多以前路過北京東城南小街,這小街忽然變成大道。
二十多年前,王世襄先生以余屋讓給我們一家安身立命的房子,就在小街內的芳嘉園小胡同中的,也被推土機推得無影無蹤。我這才弄明白古人“滄海桑田”這句話的意思。
現代文明迅猛無情地掃蕩舊日子的一切舊痕跡,但永遠掃蕩不了的是,人的回憶與感情。
1957年一場人生風雨,原在棲鳳樓的房子不能再住了,便有幸和王世襄結鄰而居二十多年。那時世襄荃猷伉儷的儷松居在北屋,老家人還在,琴書椅案,收拾得清潔優雅,只有主人不修邊幅,大布之衣有時束一條藍腰帶,懷裡唧唧有聲,乃是大褂里籠中的秋蟲鳴唱。那時還沒有暖氣這玩意兒,冬天架煙囪,生蜂窩煤爐子,老家人不在後,都是儷松居主人的長期勞作,這在世襄是不在話下的。王世襄的一部老腳踏車,后座加一塊木板,老先生能夠一天來回四五次,把他心愛的明式家具、紫檀交椅、唐雕菩薩坐像這些稀世文物,沉重地、小心翼翼地捆在車後,自己騎著送到照相館拍照,使旁觀者感到險象環生。
這就是王世襄後來陸續出版的關於明式家具那兩本巨著以及近年出版的《自珍集:儷松居長物志》當年所付出的勞動代價。諸公休要笑話,三四十年前的專家學者如王世襄,生活上常常與勞動人民差距甚微的!
王世襄名門世家,平日耽嗜的書畫文玩、臂鷹牽犬……在別人只是玩物喪志在他卻是從民族文化角度、從民俗學角度、從藝術角度去挖掘探討鮮為人知的傳統文化。他半生蒐集的書畫古籍、明式家具、匏土革木、金石文玩,無一不是研究學術、著書立說用的活資料。這和世襄為了解說一本明代漆器的書,專門與當代幾位老漆工結為師友;專門到魯班館舊家具店向老師傅虔心請教一樣,王世襄的治學方法和鑑藏道路,是另闢蹊徑的。有道是“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儷松居的文物收藏,我那時有幸得一旁觀賞,主人面授指點,愚夫婦目瞪口呆、矯舌不下的樂趣,至今尚深印腦海中。
正如北京的南小街一變為康莊大道,我們也都變成為八九十歲老人。王老最近談到:儷松居的珍藏,也應有個更適合的安排,使之能發揮多一點社會文化效益了。我聽了深感老人的構想高妙,於是翻開蘇東坡先生的千秋名作《寶繪堂記》,給他念了當中的幾句:“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
於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乃援筆而為之記。
評價王世襄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走完了他95年漫長而又充實的人生路,作別了這個曾經給過他許多痛苦,也給過他無限歡樂的大千世界,並於次日火化。這定是先生早就做好的安排,因為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事張揚,死後也不願給別人添更多的麻煩。
王世襄,號暢庵,堂號儷松居,是當代註明的學者,當代的著名學者、收藏大家、文物鑑定家福州閩侯人,1914年出生於北京,受家庭影響,自幼摯愛祖國傳統文化。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早年畢業於南陽公學,曾任晚清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民國後任職於北洋政府外交部,後又擔任過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1914年王繼曾在北京東城芳嘉園置下一座四合院,同年王世襄就出生在這個四合院裡。王世襄的母親金章(號陶陶女史)是民國著名的魚藻畫家,有畫魚專著《濠梁知樂集》行世。王世襄的大舅金北樓是民國時期北方畫壇的領袖人物,1920年創辦中國畫學研究會,其人時至今日在畫壇上都有影響。二舅金東溪和四舅金西也都是影響一時的竹刻大家。20世紀80年代,王世襄曾整理出版了四舅金西的《刻竹小言》,在竹刻界引起不小的反響。殷實的家庭背景以及良好的藝術氛圍,使王世襄自幼就受到濃厚的傳統文化的薰陶,所以後來喜好文物、古玩的基因也就此在他的血脈里生根發芽。
離芳嘉園不遠就是東堂子胡同,我國著名的學者、文物鑑定家史樹青先生幼年時期就在這裡居住和生活。同樣對傳統文化和文物收藏的愛好,使他們自幼就結為好友,兩人還曾在20世紀的1950年以撿漏的方式,共同為故宮捐贈了一個宣德青花大盤而被文博界傳為美談。我是史樹青先生的學生,最初了解和認識王先生就是通過恩師史樹青先生的介紹和引薦。但2004年我偶然收藏到一批有關王世襄先生在“文革”中抄家的資料,後來決定創作《煙雲儷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一書,曾對這批資料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通讀,使我對王先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批清單約有一百多頁,除了查抄清單外就是王世襄寫給有關部門的信函,索要“文革”時被抄沒的圖書文物資料,以方便研究及著書之用。記得2004年,因為拙作《世紀恩怨——徐悲鴻與劉海粟》一書創作的一些問題,我正好去拜訪黃苗子先生,知道黃老與王先生是多年的摯友,就帶上了這批資料,順便向黃苗子先生了解情況。黃老看完後感慨頗多。“文革”被抄家時黃苗子先生就住在王世襄家,當年王世襄看著他的收藏品被一車車地拉走,心痛不已,但個人的命運只能依附於他所處的時代,那時除了服從命運還能做出什麼選擇呢?王世襄因為出身官僚家庭,又曾在國民黨政府做過事,所以自1949年後歷次的運動都沒有躲過去。“三反”“五反”時被原工作單位文物局除名,1958年後又被錯打成右派。可是王世襄卻並沒有因此沉淪,在有限的條件下,他依然在做著有關文物方面的研究,悄悄整理完了《髹飾錄解說》《清代匠作則例》《高松竹譜》等多部著作,並自費油印出版分贈朋友。“文革”的那次查抄,王世襄是作為自交戶將家藏文物圖書上交文管所的,據我所藏國家文物局文管所和北京市東城區查抄辦於1966年9月2日的清單記錄,共有文物2567件、字畫1242件、圖書8156本又24捆被抄沒。資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關文物的研究和寫作。
1969年10月,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背井離鄉和艱苦的環境也沒有使他對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一次在田頭,他看到一束倒伏於地依然開花的油菜而深有感觸,賦詩曰:
風雨催園蔬,根出莖半死。
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
詩言心聲,他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依然對未來充滿希望,他堅信一定有還他清白的那一天,此可謂身處九淵而不廢凌雲之志。那束“昂首猶作花”的油菜,也正是詩人彼時彼地對待生活的真實心態的寫照。
王世襄於1973年回到北京,根據中央落實政策,他便開始了漫長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圖書之路。1976年他寫信給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信中說道:“三十多年來我積累了一些圖書和實物資料,當時的收集目的,主要是為研究之需……至於圖書及實物資料,只要一旦使用完畢,自當捐獻國家……”為此他又多次寫信給相關部門,但所寫之信大多泥牛入海,沒有任何訊息。後來他想出了一種辦法,用複寫紙將一封信複寫若干份,向有關部門數次三番地郵寄,並鍥而不捨地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正是由於他的這種執著精神和不厭其煩的訴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文物和圖書絕大部分都回到了王世襄手中,也正是這些資料的順利回歸才使得王世襄的各種研究得以繼續。從“文革”結束時起,他的各種著作以井噴之勢陸續出版,所研究內容涵括了書畫、古玩、家具、漆器、音樂、民俗、匠作則例等幾乎與中華傳統文化有關的所有內容。其中如《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二書早已成為中國家具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的傑作。記得2005年,為紅學家周汝昌《詩畫紅樓》題詞一事曾去拜訪王世襄先生。當時王先生正在寫有關中國傳統觀賞鴿的生將題詞交付後說:“我沒有時間陪你們,我正在研究觀賞鴿,還要校訂《錦灰堆》。我九十多歲了,時間不夠用啊,來日無多,來日無多。”說完就伏案繼續工作了。那次見面時間很短,只有二十幾分鐘,但先生潛心著述、遠離浮躁的執著的眼神至今難以忘懷。
王世襄先生就這樣悄悄地走了,當然這也使關心他的友人和敬愛他的後學沒能見他最後一面,從而留下了無盡的思念和遺憾!但值得告慰後人的是,他給我們留下了幾十本、近千萬言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國學大師啟功先生在評王世襄《說葫蘆》一文中寫道:
他向古今典籍、前輩耆獻、民間
藝師取得的和自己幾十年辛苦實踐相
印證,寫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將出
版的書。可以斷言,這一本本、一頁頁、
一行行、一字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文化晚的註腳
正如啟功先生所說,那么這些書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無疑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註解者。
聽到王世襄先生去世的訊息後,我曾寫下輓聯,今錄如下以示對王先生的懷念:
芳嘉園外提籠架鳥鷹逐兔挈狗
捉獾秋鬥蟋蟀冬鳴蟲雖為玩物不喪志
儷松居內北京鴿哨清代匠作明式
家具刻竹小言說葫蘆成巨著堆錦灰
暢庵先生一路走好!
讀者評議之一
北京是舉世聞名的古都,文物古蹟豐富,再加上自元以來就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更成為各個朝代人文薈萃之地。無數的文人雅士在這裡創造並延續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歷史。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北京市政建設的開展,舊城改造的步伐逐漸加大,因各種原因一些單位或私人在搬遷的過程中將一些有價值的檔案、書信、字畫,甚至文物古玩都被誤當做廢品送進了物資回收戰。這時一些有點文化的“垃圾王”就開始將其中有價值的圖書、信札、字畫有意識地收集起來,然後再拿到北京朝陽潘家園舊貨市場出售,無意之中拯救了許許多多的珍貴文物檔案,使它們避免了被化成紙漿的命運,久而久之潘家園舊貨市場也形成了北京乃至全國最大的文物、舊貨交易中心。期間,不斷傳出有人從中淘出“寶”來,如見諸新聞的就有收藏愛好者用極低的價格淘到乾隆御批《十三經》,也有人從舊書中發現周恩來總理的手跡,至於名家信札,據我親身經歷就有陳夢家數百封名家往來信函在此現身。我在繪畫之餘耽於藝術家信札的收藏,因為這亦是研究美術史的重要資料,同時被潘家園裡發生的或傳說或真實的故事所吸引,逐漸也成為了這群淘寶者中的一員,所以說我的名家信札的收藏生涯是從潘家園開始的。在這裡我結識了一批收購經營舊物的朋友,並建立了長期的聯繫。記得2004年春,我正在家裡畫畫,接到一位經營舊物的朋友兼山東老鄉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剛剛發現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間的全部抄家檔案資料。出於對王世襄先生學識的敬仰,我毫不猶豫地將這批資料全部留了下來。當時北京嘉德拍賣公司剛剛以高值拍賣了王世襄先生的舊藏文物古玩,我對照嘉德拍賣圖錄仔細查看這批“文革”抄家資料,發現嘉德所拍賣的文玩全部經歷過被抄之苦,而且收藏於上海博物館的王世襄舊藏硬木家具也均在抄家名錄中出現。隨後我準備就此寫些東西,曾拿信札給恩師史樹青先生看。史先生和王世襄相識於少年,一生交好。“那個時候知識分子都難逃厄運。”史先生慨嘆道,然後看著這一堆資料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史樹青先生在“文革”中也屢遭迫害,顯然他不太願意重提那段往事。隨後,又去拜訪黃苗子先生,黃苗子曾租住王世襄的芳嘉園,兩人比鄰而居二十餘年,也是當年“抄家”的見證人。黃苗子先生告訴我,最好不要去打擾王世襄先生,他的夫人袁荃猷剛剛去世,家藏也拍賣了,可謂人去屋空,黃老擔心王世襄先生看到這批“文革”資料傷心。我遵從黃苗子先生的囑託,沒有因此事再去叨擾王世襄先生,即使2005年我曾經拜訪王老,也絕口未提此事。這批資料就這樣閒置下來,一扔就是幾年,因家中書籍資料越積越多,有一段時間甚至已記不清把它放在何處了。2009年整理圖書,無意中在書櫃的一角發現了這一批已布滿灰塵的資料,在重新翻閱這些資料時,我忽然靈機一動:何不把這批資料整理出版?記得已故中國佛教協會原會長趙朴初先生曾為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的收藏題詞:
觀其所藏,知其所養,餘事之師,百年懷想。既然社會上和學術界共同的認知——王世襄先生是當代的文博大家,那么套用一句當今的流行語——王世襄是怎樣煉成的呢?我就把這批資料全部原貌整理呈現出來,大家在“觀其所藏”時,自然也能“知其所養”了,我認為這也會對王世襄的學術思想的研究有極大的參考價值。於是說乾就乾,我很快就列出了提綱,並借用黃苗子先生為嘉德拍賣王世襄舊藏所寫的序文《煙雲小記》的“煙雲”二字,又因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的居所雅號為儷松居,於是書名就這樣定下來了:《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煙雲儷松居》,並請書法家王家新先生題寫了書名。隨後著手蒐集王世襄的有關傳記資料,拜訪文博界相關人士。但在整理資料的時候卻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文革”抄家時混亂,再加上抄家者文化水平不高,抄家清單上可謂錯訛百出,比如家具類器物的描述,因缺乏專業知識,皆以床、椅子等籠統名稱書寫,實在令人費解。於是又動了去拜訪王世襄先生的念頭,誰知已九十五歲高齡的王世襄這時已住進了協和醫院,據說身體狀況堪憂。2009年11月29日,《京華時報》的好友卜昌偉兄打來電話,告訴我王世襄先生已於前一天魂歸道山了。在默默懷念這位世紀老人的同時,我加緊了寫作的步伐,但創作的過程中也著實為本書的體例煞費腦筋。如何表述這段歷史,是寫成傳記還是只表述1966年到1986年王世襄從抄家到追回文物的經過,因種種現實情況,最後還是定下了書的前半部分敘述王世襄先生的個人成長及學識、文物積累的過程,後半部分則將這批資料原件印出。我出生在“文革”的後期,對“文化大革命”幾乎沒有任何印象,也從未做過深入的研究,為了尊重和還原歷史,所以對這些資料就不再做任何評述了。寄希望於王世襄先生的研究者能從中發現有用的材料,對於普通的讀者則可以從傳記中了解一位文博泰斗的成長曆程,如果能達到這個目的,也就不枉我的一番勞作之苦了。
讀者評議之二
聽到王世襄老先生去世的訊息後,患著感冒的羅哲文很是傷感,對於沒能見上老友最後一面也耿耿於懷:“上一次見面都是三年前了,我去看他,還在一起拍了合影?後來就聽說他住院了。這個月初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舉辦中國營造學社成立八十年的研討會,幾個老傢伙聚在一起都還在感慨當年中國營造學社的老人只剩下一個半了。沒想到這么快就走了。”
認識王世襄先生生的人都知道,2003年秋天,患難與共、琴瑟相和60年的王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後,王世襄的精神就大不如前,他曾在一首詩中表達自己的思念:“君刻大樹圖,我賦大樹歌。相濡復相助,歲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餘生待若何。”
這首詩中提到的“大樹圖”是有所指的。2000年,80歲的王世襄將自己一生所寫的大部分文章交?三聯書店以《錦灰堆》為名出版,在這套書中,有多才多藝的袁荃猷女士刻的一幀名曰“大樹圖”的剪紙,粗壯的樹幹,圓形的樹冠,丈夫王世襄一生的15種愛好,就像果實般隱藏於樹冠中,這其中有王世襄用得最多的三件明清紫檀家具、有代表王世襄最主要學術成就的漆器,還有王世襄使之死而復生的傳統工藝竹刻、葫蘆器,還有繪畫、鎏金銅佛像、蟋蟀(年輕時王世襄常常邀局斗蟲)、鴿子、鴿哨(王世襄專門為鴿哨寫了本專著)、鳥具、家常菜(王世襄精於烹飪,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幹校時曾買十四條二斤重公鱖魚,做鱖魚宴,名噪一時,他曾任全國烹飪鑑定顧問)、兩頭牛、大鷹、獾狗。這套大俗大雅的奇書,出版之後一紙風行,成為從事收藏和鑑賞者的必讀書,半年內重印四次。這些玩物看似“雕蟲小技”,在中國民間,喜歡這些玩藝兒的人不少,但能把這么些玩耍的事情寫成專業的著作,讓它們登上了“大雅之堂”的,除了王世襄並無第二人。
讀者評議之三
歷史上的博物學家往往都有一個不錯的家境以及放蕩不羈的少年生活。出生於富裕的醫生家庭的達爾文便是如此,他的父親有一次指責他:“你除了打獵、玩狗、抓老鼠,別的什麼都不管,你將會是你自己和整個家庭的恥辱。”
晚年的王世襄也曾自嘲:“我自幼及壯,從國小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挈鷹逐兔……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優越的家境和年少好動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別喜歡和京城諸多玩家交遊,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風貌,他從小就是有名的“頑主”,放鴿子、抓蛐蛐、玩葫蘆、飛鷹走狗,無一不精。
但“頑主”王世襄並沒有“玩物喪志”,而是成了“天下第一玩家”。先於王世襄四天去世的翻譯家楊憲益,曾多次贈詩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稱頑主,老大京華輯逸文”,意下王世襄雖為“頑主”,但不是一無所成的玩法。
王世襄位於芳草地公寓的家中,已經看不出王家曾經的盛況。王氏家族為官宦世家。高祖王慶云為翰林,任過兩廣總督、工部尚書;祖父王仁東?內閣中書、江寧道台。父親王繼曾則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語,還出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母親金章能書善畫,大舅金北樓是民國北方畫派領袖,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厓為竹刻大師。可見王世襄的風雅傳統更多源自母親的家族,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就是中國畫理論。
小時候,家中有私塾老師教古漢語、經、史和詩詞等。王世襄喜歡的是詩詞,對其他學科不太感興趣。後來父親又送他到北京乾麵胡同美國人為他們子弟辦的學校去讀書,從三年級開始一直到高中畢業,王世襄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讓人誤以為他是在國外長大的。
王世襄在燕京大學文學院讀書時,家裡為他在學校周邊購置了大宅,他在十幾畝的院子裡種上了葫蘆,因為鳴蟲要養在葫蘆里。他甚至在臂上架著大鷹或懷裡揣著蟈蟈到學校上課,當時在燕京大學名教授鄧之誠講中國歷史正興致勃勃時,忽聽一陣“嘟嘟”的蟈蟈聲,同學哄堂大笑,原來是王世襄揣著蟈蟈葫蘆進了教室,惹得鄧先生惱怒起來,把他趕出教室。
當時王世襄的玩家派頭被視為荒誕不經。他本有機會通過哈佛燕京學社選派哈佛留學,但當時在燕京大學教書的洪煨蓮教授把這個有精力但又“不務正業”的學生稱為“未知數”,校長也不願將這個?繫到學校大計的機會給這個“未知數”。
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是王世襄哥哥的同窗,曾將從燕大畢業的王世襄推薦到傅斯年主政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後來回憶此段,王世襄說傅斯年只講了兩句話:先問哪個學校的,接著說“燕大的畢業生,不配到我們這兒”。梁思成最後將王世襄安排到自己的中國營造學社,派他赴李莊考察、研究古建築,算是引導他走入了“正道”。
他玩的東西五花八門,他玩這些不為消遣,而是真心喜愛。為了得到愛物,他捨得花錢,搭工夫,甚至長途跋涉、餐風飲露亦在所不辭。
“文?”前,王世襄去黃山考察,挖到兩棵松樹從黃山回北京,他買了兩張火車票放兩棵樹,自己卻是一路站著回到北京。王世襄對“玩”成痴,讓傳統音樂協會理事李勁風記憶深刻。
“我們聊天時只要聊到小玩意,他就特別高興,那會王老先生還在養鴿子。”因為與王家住得近,李勁風常常去串門。那會,到王家的人各種各樣,有民間工匠師傅,做糊盒的,養花養魚的,來了也就是閒聊,對工匠技藝很有興趣的王世襄,常常是問得很仔細。
“有些對王世襄先生的報導過於淺薄、輕佻。如稱呼其為玩家、大玩家、老玩家等有點失之於表”,《天下收藏》主持人王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為王世襄正名說,“說王老是收藏、國學、文學大家都可以,叫情趣大師似乎也可以,但還是顯得輕了一點,他承載得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