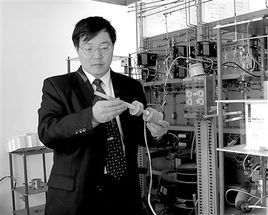《倆位教授》屬短篇小說,由作者朱墨創作,第一次登選在小說閱讀網內,2007年完成。
基本資料
作者:朱墨,寫過多篇短片小說 《小賣部》 ,《盼望一場雪》 ,《六指家》 ,《表姐》,《朋友妻》 , 《石大爺》等。
作品類型:短篇小說
書籍簡介:好玩的教授。睿智、幽默、滑稽。兩個互相不服氣的教授,鬥起來,那才叫有戲。在否定對手的時候,其實也完成了自我的否定。
原文欣賞
倆位教授
工作若干年之後,廖老和貢老仍然是同學間茶餘飯後談論最多的話題。而且談到廖老就免不了要談到貢老,說起貢老就不可能不說到廖老,廖老和貢老確實是兩位各具特色,對比鮮明,又相互間充滿了攻擊的教授,他們間的矛盾在學生中已是完全公開化了的事實。
一
廖老,六十來歲的樣子,一米六幾的個子,上身長,下身短,小鼻子,小眼睛,眉毛倒立,頭卻像雄雞一般高昂,有幾分怪裡怪氣的樣子。或許因了這幾分怪氣,廖老最愛講的一句話就是:“人的這張臉是文化的視窗,不在於它長得怎么樣,有沒有文化一看就知道。”這話說得懸乎,很有些意思,也提醒我們把廖老的臉當一檔子事來研究。廖老的臉長,而且瘦,屬於通常說的臉上無肉,必是怪物的那種類型。只要用心觀察,便可發現縱橫交錯的紋路里透著的隱隱滄桑,很耐讀,也很有文化內涵的樣子,只是打磨得粗糙了點,給人一種縮水的感覺。
廖老的文化視窗,自然成了貢老攻擊的重點目標,貢老說:“教師的形象是教學的門面,狀態如廖老者,校方還讓其在學生面前拋頭露臉,於廖老來講是一種殘忍,於學校來講根本就是對學生不負責任的表現。”
比之廖老,貢老確實有幾分風度逼人。貢老五十來歲,一米八幾的個子,儼然山東大漢。高鼻樑,大眼睛,厚嘴唇,蓄著濃密的日本人似的山羊鬍子,藝術家的長髮,上身常穿一件長到膝的體恤衫,下身著一條寬大的褲子,說是道家打扮,其實更像個流浪漢。貢老滿自信地撮著山羊鬍子在課堂上講:“男人的風度不是說出來的,而是一眼就能看出來的。”
對貢老的風度,廖老自然也有幾分不屑,廖老說:“貢老確實長著一把大而無當的強姦犯的身體。”從表面上看,貢老確實有幾分流氓樣。
二
廖老教的是古典文學。廖老上課不帶教課書,不帶講稿,也不需要粉筆,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在黑板上寫字的意思。一進教室,廖老便背剪著雙手,閉著兩眼,雄雞般高昂著頭,目中無學生,亦無教室、黑板,一開講便嘩嘩的念,我們便跟著涮涮的記。廖老講課不像是講課,倒像是背課,從頭至尾,古人的詩詞文章背,古人的生卒年月、歷史背景也如數家珍一般背。背到關鍵處,搖頭晃腦陶然亦樂然,很沉醉,很進入狀態的樣子,譬如莊子的《逍遙遊》,倒像是他老先生在逍遙似的。只是苦了我們,他背一句,我們寫一句,或者背幾句才能寫一句,聽得很累,筆記也做得很苦,生怕掉了關鍵處,記不下來的,只有下來找記得快的補上。因為廖老一開始講課便反覆告誡我們,他的課考試內容全在講課之中,不僅沒有額外的可供複習的參考資料之類,而且試題所涉及的內容在書上有一半以上無法找到現成答案。更絕的是,他不可能像其他教師一樣點題,勾畫重點。廖老說:“校方已三令五申強調不準教師點化考試題目,況且,鄙人偌大一把年紀的人了,也犯不著在這種小事上犯錯誤寫小楷。”
等死吧!廖老可是一個嚴格認真得有點過分的小老頭,考59.9分,他絕對不會讓你60分過關,這在上幾屆已有深刻而慘痛的教訓。
所以,儘管筆記做得很辛苦,我們也只有踏踏實實地辛苦下去,他背一句,我們寫一句,即便是口水話我們也會不折不扣的寫進筆記本里去。
我們總有一種感覺,聽廖老的課,好像從事的不是腦力勞動,而是徹頭徹尾的艱苦而又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廖老講課,生怕學生記下來似的,背過去就不再重複第二遍。記不下來我們也不敢要求再念,否則,打斷了他“背課”的思路,廖老的那雙尖利的小眼睛定把你刺出眼淚水來。於是苦了做筆記慢的學生,課後還要補大量的筆記,成了雙倍的體力勞動。更要命的是,廖老的課,每課必布置大量的作業,叫人一提起作業就頭綠眼睛花,有過敏般的感覺。
對廖老的授課,貢老曾有過一番精闢的論述,貢老說:“廖老上課純粹是死人上課,僵硬、教條,幾十年一貫制,沒有創新,沒有突破,是完全徹底的誤人子弟。”這些話算是撞到了學生的心坎上,只是校方未必聽得到,聽到了也未必聽得進去,因為畢竟廖老是學校的一面旗幟。
當然,廖老也不是省油的燈,廖老給貢老的回敬是:“貢老上課完全是流氓教學,有嘩從取寵之意,無實事求是之心,只會把學生誤入歧途。”
在教授中貢老屬於年輕一類,觀點新潮,語言時髦,屬於感悟生活感悟得比較快的那種類型。貢老基本上是坐著講課,只是偶爾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才站起來,而且寫的也是不多的幾個字。記得貢老上的第一堂課一開講就在黑板上神秘兮兮地寫了一個大大的“且”字,讓在座的幾十號男男女女猜猜是什麼意思,大家胡亂說了一通後,貢老終於鄭重宣布:“這是男性生殖器。”見有的女生低了頭,貢老就朗聲笑說,“別不好意思,說穿了就是這么一台事,中國的字開始都是象形文字,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那么一點意思。”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貢老寫在黑板上的“且”字確實耀眼得有些令人炫目,而且似乎是刻意為之。貢老見大家的眼睛都盯在了“且”字上,於是用粉筆把“且”字重重的圈了起來,又重重地點了數點,說:“請同學們開動腦筋好好想一想,古代的建築哪一樣與生殖器無關?”於是,我們就進入了“想”的狀態。貢老問大家想到什麼了沒有,大家都一臉高深地沉默著,貢老便撮著山羊鬍子說,“塔,男性生殖器,太極圖,女性生殖器,此謂古人生殖器崇拜是也。”貢老一雙有神的大眼睛在教室高高地環顧了一周后又在黑板上寫下了兩個字“文明”,貢老說:“什麼叫文明?不敢在大街上拉開褲子撒尿,這就是文明。”貢老在“文明”上重重地畫了一個圈,“所謂的文明就是大活人讓尿憋死。就是這一憋,才憋出了文明。”貢老又在文明上上重重地點了數下,“然而——文明並不等於談性色變,更不等於世間男男女女都去當和尚做到尼姑。”
貢老教的是《文學概論》,但貢老似乎對《文學概論》不大感興趣。在課堂上,貢老最喜歡談的就是唐朝。貢老說,唐朝那才叫開明,開放,皇帝老子明目張胆霸占兒子媳婦成為當然,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成為美談,要是放在之前、之後,或者就放在民主、文明的今天試試看?不要說“天子”呼你,只要你的上司一呼你,你不屁顛屁顛的小跑著去才叫怪呢。
貢老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泡杯泡妞,且毫不臉紅地稱,他有“兩好”:一曰好色,二曰好酒。好色他喜歡談絕色美人楊玉環;好酒他喜歡談詩仙加酒仙的李白。如對貴妃楊玉環,貢老就有許多經典的研究,甚至研究到楊貴妃的每一寸皮膚。貢老撮著山羊鬍子說:“楊貴妃的皮膚那才叫真正的皮膚,那絕對是在牛奶中浸泡得像牛奶一般白淨的皮膚,同學們想想看,有多白?要有多白就有多白?比雪還白?”似乎覺得不夠味,又用了一比,“比豬板油還白。”這一比不但無美感可言,而且有些庸俗了。見大家都有些不屑,貢老嘿嘿一笑,馬上又說,“其實,這個比喻是廖老的專利,貢某隻不過是借用一下而已。”想到這是廖老的比喻,大家嘴角的不屑也就變成了心領神會的嘿嘿一笑。再如說到白居易的《長恨歌》里描寫楊玉環的“侍兒扶起嬌無力”句,貢老斷然說,“那絕對是描寫性愛之後的軟弱無力。”說罷,雙眼環視教室,一臉的壞笑,像是撿了天大的便宜似的。逢到這種場合,我們就肆無忌憚地笑,笑得一堂課有些“黃”。
貢老講課,好海吹、神吹,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里,都吹得頭頭是道,有鼻子有眼。貢老為自己辯護說:“吹牛是一種智力體操,是一種思維的鍛鍊,是一個人的綜合能力的釋放。”貢老還說,“貢某做人的準則是把自己肚子裡想說的話全說出來,正如貢某上課的水平,就是把別人搞抽象、搞複雜、甚至搞糊塗了的問題具體過來,簡單過來,明白過來,從而達到講深、講透的效果。”客觀地說,貢老確實有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只是,貢老上課,生怕學生聽不懂似的,同樣一個意思,舉一反三,講了又講,好像我們都是弱智。而廖老講課,又生怕學生聽懂似的,講過一遍,決不再講第二遍,舉了一個例子,決不再舉第二個例子。廖老說:“恰當的例子可以以一當十,不恰當的例子,以十也當不了一。”這話聽來好像是針對貢老說的。
實在說,聽貢老的課,一是輕鬆,沒有筆記可記,也沒有危機感,因為學科考試之前,貢老會點題,而且範圍框得比較小,答案也是現成的。二是貢老的課沒有作業,貢老說,他有“兩怕一好”:怕的是改作業和監考,好的是講課。貢老用了一串形象的比喻說,改作業像洗碗,既瑣碎又無趣,簡直就是娘兒們幹的活計;監考像等飯吃,總覺得日子老長老長的,叫人心煩;講課則像炒菜,隨心所欲,個人才能得以發揮。而且炒菜有成就感,能夠引起別人的關注,菜合口味的,別人會問,誰炒的菜?洗碗卻不同,只有失落感,洗得不乾淨,別人才會問,這是誰洗的碗?三是貢老的課,似乎是為了逗樂,或者有意要把一堂課上得不像一堂課,所以,時尚話題多,花邊新聞多,什麼民謠、俗語幾乎是信手拈來,獵奇、新鮮而又刺激,類似於看街頭小報,雖無多少實際內容,卻比廖老的課多了一份情趣。
某日,可算是貢老授課最為尷尬,也最為無趣的一節課。那天,校長帶著廖老來聽貢老的課,貢老再也不敢不著邊際的神吹,也沒了泡杯泡妞作佐料,而是嚴肅著一張面孔一本正經地講,講的又是枯燥乏味純理論部分,完全失去了以往那份輕鬆、灑脫、愉快的風格,講得很吃力,也很無趣,我們聽得也很吃力很無趣,老是看錶,卻又老是不下課。結果一節課乾乾巴巴講了半節課,內容就完了。貢老望著校長乾笑兩聲,要大家複習一下前幾天講過的內容,然後,貢老從講台站了起來,走下講台,一臉謙卑地向校長陪笑說:“今天狀態不佳,可能是昨晚多喝了兩口。”校長看上去比貢老年輕,但對貢老卻冷著一張臉,說:“注意休息,特別要注意身體,酒不但傷身,也影響大腦。”貢老嘿嘿笑著,頻頻點頭。廖老卻趁機笑說:“這堂課怎么就這般乾巴巴的,一點趣味都沒有,一點黃段子都聽不到呢?”同學們一下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貢老臉都變了。校長和廖老起身要走,貢老差不多是點頭哈腰把比他年輕的校長送出老遠才又回到教室。貢老回頭向我們自嘲說,“沒辦法,權力大於泰山,這年頭在當官的面前你就得裝孫子。”有這個必要嗎?見大家臉上都流露出不屑,貢老又補充說,“這是課堂以外的學問,這是大學問呀同學們!而且,這肯定是老廖犯奸,存心要貢某下不了台,否則,再怎么說,校長也不會搞突然襲擊。”課堂上很多人都若有所悟地“噢”了一聲,貢老才又顯得語重心長地說,“同學們,如果連這一點你們都滲不透,悟不透,看不明白,將來的一天肯定有你們的好果子吃。”犯得著這樣嗎?貢老的形象在我們面前一下削弱了許多。
貢老苦口婆心地為自己解脫,你們不知道,我們學校教師多,壓力大,競爭上崗不得了。每次開會領導都要拿出一兩個人批評一下。但批評誰呢?批評老的吧,比如老廖,可能嗎?人家年齡大,沒功勞也有苦勞,沒貢獻也有資本。一是面子上過不去,二是也不容易拿下,而且老廖這些人也根本不買你的帳,弄不好,批評出個什麼病來你也吃不了。批評年輕人吧?年輕人易激動,怕收不了場,為批評個把人把自己推到尷尬的境地收不了場,也太沒領導水平。聰明的領導也不願冒這個險。批評脾氣好的神經脆弱的吧?動輒哭哭啼啼,鼻子一把眼淚一把也無多大意思。本來領導批評人是一種權力的享受,把你弄得哭哭啼啼,他還怎么享受?說來說去,受批評就只能是我們這號中年人。一是也經歷了一些風雨,二是性格開朗也看得開,三是也能站在領導的角度想問題,明白領導選自己作靶子,也是用心良苦,情非得已。反正總得有人作靶子,讓領導享受一下批評人的權力。何況,我們這號人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問題不少錯誤多,一是好發議論,好亂說一氣,這叫言多必失,二是我們這號人,工作也幹得多,工作幹得越多,錯誤也就越多,也就越能充分暴露自己身上的弱點。所以我們被批評的機會也就多。去年,領導就批評我上課離題,所以這次你們不能再提同樣的問題說我上課離題,這次離題,我就慘了,因為無實事求是之心,也無悔改之意。你們只需說我講得不深不透,或者統而言之,講得不生動就可以了。因為沒有任何人敢說他講得深講得透了,也沒有人敢說他講得生動了。
聽貢老的一席話,我們又多少覺得做人的艱難。
比之貢老,廖老的課確實知識容量大,水分少,但他也不單純的為了上課而上課。有時,為了調節一下沉悶的課堂氣氛,廖老偶爾也會中途吹點散牛。但即便是吹散牛,廖老也始終嚴肅著一張面孔一本正經地吹,而且就吹的內容來說,也好像是吹真的,讓你感受不到吹散牛的樂趣。譬如有一天,廖老說:“鄙人算了幾個晚上也算不明白,一頓飯要花七、八千元,上萬元,吃些什麼呢?”廖老要我們跟著他的思路算一算。我們就跟著他一本正經的扳著指頭算,但算來算去我們也算不明白。究竟是學生把老師攪糊塗了,還是老師把學生弄糊塗了。課後,我們終於明白是廖老的思路左右了我們,就覺得廖老好笑,笑他的迂,哪有什麼算不明白的?他只會就事論事乾算,把什麼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水裡游的算進去,再加兩瓶茅台、五糧液之類的好酒,哪有這種算法?豈不聞吃不了還要兜著走呢。再譬如有一天,廖老突然講到了牢騷,廖老說:“一個人連一點正當的要求都得不到滿足,通過發一點牢騷來釋放自己心中的不平,這屬於正常牢騷,像知識分子,連起碼的安居都不能解決,又談何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廖老是單身漢,住宿據說按的是單身漢標準,別人可不管你年齡有多大,學問有多高。廖老對此肯定有意見,而且還發了牢騷。廖老說,“其實,牢騷多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牢騷,沒有牢騷就潛伏著危險。有牢騷是正常的,關鍵是怎么對待,一個領導,如果連一點正常牢騷都接受不了,就沒有一點民主,而是純粹意義上的專政了。”“當然,也有非正常牢騷,”廖老說,“譬如,你什麼‘長’都不是,卻老想著住別墅,坐高檔轎車,不能滿足就罵社會分配不公,就罵別人腐化墮落,這就是吃飽了撐的,屬於非正常牢騷。”可能是廖老擔心他發的牢騷會影響我們對他形象的誤讀,於是解釋說,“牢騷是有檔次的,有高級牢騷,亦有低級牢騷,高級牢騷是有修養,有品位的,如犀利的雜文,聽之痛快,解氣;低級牢騷是沒有水平的,庸俗的,漫罵似的,這種牢騷不聽也罷。”按廖老的意思,他廖老發的自然是高級牢騷了,而牢騷如貢老者,發的就是低級牢騷了?
三
據廖老自己和其它一些相關人士的介紹:廖老是某大學建築系畢業的高材生,畢業後,工作不到一年就不明不白被打成了右派,下放農村教給貧下中農管制勞動。後政策落實,一心想從教的廖老才被請到了我們就讀的這所大學任教。
廖老下放到農村,就被分派了放生產隊里的牛。正如貢老所說:“在學生面前,廖老最值得炫耀的就是他那段‘牛屎’(實為‘牛史’)。”
放了六年的牛,廖老自然學會了不少“牛話”,大致可以和牛進行感情對流。“開始放牛的時候確實很無聊,”廖老說,“一個活生生的大男人,成天面對的就是藍天、白雲、大山,以及只顧低頭吃草的牛,那日子別說有多寂寞了。所以,通過放牛,鄙人真正理解了對牛彈琴的涵義。試想,一個人無聊了、寂寞了、委屈了,想找個人聊聊,卻連一個鬼影子都找不到,你不‘對牛彈琴’,難道你還能跳崖了不成?”講到這裡,廖老嘴角終於滑過了一絲不易被人察覺的笑,那種笑簡直有一點蒙娜麗莎的味道。
放牛期間,為了打發時光,廖老就從家裡帶了很多的古典書籍去讀,因為他父親是從事古典文學的專家,有的是這方面的書。讀書他從不滿足於一般性的瀏覽,而是背,老子的《道德經》,屈原的《離騷》等等,他都能倒背如流。“背詩,你也不能當作貧下中農去背,也沒有人會聽你背,唯一的忠實聽眾就只能是牛,牛是最勤勞、最有耐心,也是最有人情味的。那時候,我不但對牛背詩,而且還對牛作詩,牛也似乎能夠理解詩的意思。逢到作得好的,牛還會抬起一對牛眼睛導師一般鼓勵性地看著你。實話說,鄙人對牛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浮誇一點說,沒有牛為伴,也許就沒有站在講壇上的廖某了。”廖老說,“那時候放牛,一想起魯迅先生的話,我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和血,靈魂深處就會有一種顫慄,就會有一種要哭的感覺。”
廖老講莊子的《庖丁解牛》時,又說:“其實,莊子也是從牛身上得到了處世哲學的,事實上老莊和牛是相通的。通過放牛,通過讀老子、莊子的文章,鄙人終於悟出,牛是深諳老莊哲學的,你看它那安詳的眼色,那平和的態度,那無可無不可的處事風格,那甘為孺子牛的‘守雌’信念,無一不滲透著老莊哲學的精髓。”
廖老講的這些話,都被我一字不差地記錄在了筆記本上,現在翻看,廖老當年講課的形象及神態又如在目前,叫人在心中對先生又頓生一份感激與懷念。
比之廖老,貢老算是幸運的。貢老雖然也下過村,但當的是知青,據說在農村還有些風流故事。廖老就說:“貢老除了一身的風流債,也就只剩下那個不值錢的東西。”
貢老在農村當知青,還真的有個貌美如天仙般的叫小芳的姑娘愛他愛得死去活來,但回城後的貢老上了四年的大學後,就和省劇團的某演員結了婚,痴情不改的小芳也就草草嫁了他人。貢老自然不是無情之人,據說小芳的兒子就是貢老從國小到大學一手供讀出來的。現在貢老可是結了三次婚的男人。課後貢老常到我們宿舍轉,貢老說,現在他的第三任老婆是曾經在他家打工的保姆,沒文化,長得也不怎么樣,但年輕、性感,很會挑逗人的。貢老在說這些的時候從不害臊臉紅,像是拉家常似的。
貢老告訴我們,有人曾開他的玩笑說他有四個年齡:一個是他的實際年齡,四十八歲;一個是他的表面年齡三十八歲;一個是他的心理年齡,二十八歲;一個是他的生理年齡十八歲。我們表示不明白,貢老咂了咂嘴,有幾分不屑地說,“說白了就是夸鄙人不顯老,不落伍,不遲鈍,不疲軟,活得遊刃有餘,有滋有味罷了。”說畢,貢老又是一臉的壞笑,我們也就跟著他沒正經地笑得死去活來。
記得剛踏進大學校門的時候,貢老就直門直路地開導我們:“有必要對你們這幫乳臭未乾、混沌未開的童男童女進行性愛啟蒙教育。你們知道讀大學第一步需要補的課是什麼?社交?生活?知識?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談戀愛,而且要儘快進入狀態。同學們想一想,大學四年,畢業了卻連戀愛都沒有談上一二盤,留下的絕不僅僅是遺憾,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寒磣。”最後兩句話,振聾發聵,簡直是大聲吼出來的,乃至貢老停止了講話,教室里仍然瀰漫著一種嗡嗡的,叫人心慌心跳的聲音。許久,貢老方一臉嚴肅地認真掃視了每一個同學一遍,又顯得語重心長地說,“同學們,我是把大家當朋友才這么跟你們講的,我這不是高談闊論,也不是譁眾取寵,因為談戀愛也是一個學習、鍛鍊、提高、成熟的過程。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我發現,談戀愛越早,懂得男女之事越早的人,一般智商都比較高,譬如鄙人,國中時就把戀愛談得如火如荼、熱火朝天,現在回想起來,都還有幾分韻味。雖說現在鄙人已過了談戀愛的年齡,但仍然喜歡在大熱天,攜二三美女在翠湖邊喝茶,要的就是那份清涼,那份舒心,那份愜意。”貢老確實是一個既懂得生活,也會享受的人。貢老又說,“看見一個美女,卻視若無睹,這種人要么是偽君子,要么是變態,要么就是陽痿。”貢老說話從不遮遮掩掩,有時甚至直白得讓我們這些當弟子的都替他害臊臉紅。貢老說,“做人關鍵是要有一個良好的、裸露的心態,要把一個本來的我完完全全的向世界敞開,沒必要自我遮蔽,活得鬼鬼祟祟,像別人的翻版似的。”從這點上說,貢老完全活在了他自己的宣言中。這就是“不論做人做狗都要敢於活出個人模狗樣來!”
四
廖老是單身漢,老童男子。年輕時放牛錯過了找對象的機會,現在更沒有找對象的欲望。據貢老說,本校曾有一無人問津的女副教授,因崇拜廖老而對廖老表現出那么一點特別的意思。但廖老說,甘願耍光棍,也不願惹紅顏。氣得那女副教授當面叫了他一聲:“廖公公!”那位女副教授姓張,上過我們的《現代文學》,聲音小,但柔和,樣子也還算過得去,唯一不足的是衣服總是穿得不合體,像是匆忙之中錯穿了別人的衣服似的,多少有些滑稽。有聰明的同學當面誇張老師學者型的教授。張老師卻很敏感,一聽就知道別人在說她的衣服,於是自我解嘲說:“在家裡面,我的這身打扮常讓人誤為保姆。”就這一點來說,和廖老到是有些相當。但兩個都不會過日子湊在一起,也確實有些勉為其難。
貢老說:“廖老之所以不結婚,並不是他要找一個會過日子的,其實完全是因為他的那個東西已經不管用。”
廖老自然是書呆子形的學者,所以在生活方面就很有些糟糕,且不說衣服不合體,就連基本的清潔衛生都無法保證,要么是褲子上有油漬印,要么就是衣裳上有斑痕,或者頭髮凌亂,像幾個星期沒洗的樣子,或者光腳忘記了穿襪子,即便是穿了襪子,也多半情況不配套,有時配套了,又是破舊得慘不忍睹。給我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廖老來上課竟然把“車庫”的門開著,以至裡面內褲上的一根紅帶子還長出一節來在外面恬不知恥地晃悠晃悠的,開始有人想笑——廖老可能也有所察覺,所以上課就比以往更嚴肅,頭也就昂得更高,也就更有幾分凜然之氣,想笑的人也就強忍住不笑。後來我們忙於做筆記,也就暫時忘記了廖老的“車庫”,待到上課告一段落,大家開始注意的時候,“車庫”的門卻意外的關上了,可見廖老也有他擺脫尷尬的一套絕招。
廖老通常和我們一起在學校的餐廳就餐,而且往往忘了帶菜票,只有向我們借。我們借了他菜票,心裡就當報答一次老師,也沒有想過要他還的意思。事實上,也不可能還。因為廖老借菜票,只為了當時打發一下肚子,過後也便忘了借票一事,即便偶然靈機一動想起,他也弄不清是向誰借的,借了多少。為這件頭疼的事,他曾很認真地在班上落實過幾次,但借票的弟子們都友好得不願意承認。那是於老師,於自己都很沒面子的事。雖然廖老有著特殊的記憶功能,但在記人和認路方面,卻顯得有些弱智。這么說吧,上了我們兩門課的廖老基本叫不出學生的名字,有的即便叫出來了卻又往往是驢頭對不了馬嘴,要么是把男女生的名字弄混淆了,要么就是把非本班人員的名字按在了我們班,叫人哭笑不得。想想看,在一座自己呆了十多二十年的城市,廖老獨自一人上街竟然十次有八次要問路或者“打的”才能回到學校。有一個說不清是真實的還是純屬虛構的笑話,說是廖老曾在學校大門口處“打的”到學校,結果師傅以為他是外地人不熟悉情況,把他拉著繞校園外圍轉了一圈又送回來了,下得車來的廖老還暈呼呼地摸著自己的凌亂的頭髮說:“怪哉稀奇!剛才好像就在這裡上的車。”可見他是暈到家了。
毫無疑問,廖老是勤奮而治學嚴謹的教授,而且還有很多有影響的論著發表,屬於本校少有的幾個名教授之一。但廖老的古板固執也是出了名的。
貢老講,廖老曾寫過一部以先秦時代為背景的電視劇本,被香港某家劇組導演看好,原打算要拍片子的,但苦於劇本所涉及的那一百多種稀奇古怪的兵器一時難弄齊全,所以致函聯繫廖老,希望他能變換或者刪去幾種兵器,但廖老卻生硬地說:“現在拍不了,並不等於說以後也拍不了。”所以只得暫時作罷。貢老還講,廖老寫論文,一寫就是洋洋灑灑上萬字,曾有家刊物的編輯看好廖老的某篇文章,但嫌其長,要他刪去三分之二方能刊發,但廖老卻一點也不通容地回絕了編輯:“別說刪,就是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能動。”編輯也不客氣,回敬廖老說,“那我們也只能委屈一下,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能為你刊發了。”結果把個廖老氣得大病了一場似的,幾天過後,臉上還寡綠寡綠的。
貢老說:“其實,廖老師開的分明是垃圾加工廠,還把垃圾當寶貝似的敝帚自珍。”
廖老好像也不大喜歡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貢老講,有次省台要為廖老搞一組特寫,廖老問記者:“我這點鏡頭還能上電視?”
記者說:“關鍵是要看你的學問和氣質。”
廖老再問:“學問和氣質也能在電視上表現出來?”
記者說:“這是表現手段的問題,也是我們處理的問題。”
廖老說:“我總不能比卓別林還卓別林吧?”
記者說:“所謂藝術來源於真實又高於真實,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廖老說:“這個我好像比你們懂得更多一些。”
記者被他噎得夠嗆。結果因為廖老的偏激與執拗錯過了多次露臉的機會。
貢老自然不屑於廖老的清高與固執,貢老向我們說:“你們以後可要充分抓住任何一次展示自己的機會。敢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展示自己,這是一個人綜合素質的大檢閱。廖老師之所以不願意拋頭露面,是因為他的那張死人臉,使他完全對自己失去了信心。”
相比之下,貢老不但喜歡露臉,而且不放過任何一次露臉的機會,特別是喜歡在電視上當特邀嘉賓神聊神侃。貢老自我標榜:“不管在任何場合,我姓貢的都是當然的主角,焦點中的焦點,任何場合只要我一開口講話,便能語驚四座,讓在場的人束然起敬。過後,很多人見了本人,還能回憶起,貢某在什麼場合講過什麼樣話。”無事,貢老還熱衷於辦講座。貢老說:“一個好的講座本身就是一次精神會餐,一次精神充電,一次新潮思想的向外發射。”貢老告訴我們,他辦的講座,常常座無虛席,甚至報告廳的走道上,窗子外面都擠滿了人,讓拍錄像的人都很難擠進去。貢老自己講,很多人評價他的講座,能講,會講,敢講,有深度,有思想,有激情,有煽動性,可洗腦筋,並有敲山震虎,醍醐灌頂之功效。
貢老極儘自我推銷之能事,把自己吹捧得簡直忘記了自己是誰。貢老的講座,我們這幫門生自然每講必聽,並不是說貢老的講座確實有他說的那么奇效,而是因為貢老提前向我們打過招呼的。貢老語重心長向我們講:“你們要站在老師的角度想一想,老師辦的講座,自己的弟子都不去捧場,這老師是不是當得窩囊了點?”所以,貢老又顯得惡狠狠地警告我們,“有必要明白告訴你們這幫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子,誰不去的話將會嚴重影響本門課的學科成績。”非但如此,在私下,貢老還特別交待我們幾個和他混得比較好的弟子,要多鼓動些外班,甚至外校的人去湊熱鬧造氣氛。貢老拍著胸膛向我們表態:“弟兄們,講座結束我請你們吃燒烤。”這是讓我們最興奮不過的事情。我們自然樂意為他效勞。
貢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甘寂寞的人往往很難寫出大部頭的有份量的文章。貢老也說,他最討厭的就是那些長篇大論說教式的文章,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其實枯燥乏味,除了作者和編者兩個當然的讀者外,恐怕再沒有更多的人看。鑒於此,貢老喜歡弄“豆腐小塊”——“跳出形式和內容的束縛,想怎么表現就怎么表現,想怎么談就怎么談,而且三言兩語就把觀點亮出來。”貢老說,“其實讀者要的就是觀點,而不是冗長的論述,沉悶的內容本身。”貢老的文章通常刊登在晨報或晚報上,三五天就亮出一篇,叫人沒法把他忘記。
廖老自然不屑於貢老那些報屁股上的文章,廖老曾不止一次地當作貢老和學生的面評價貢老的文章:“似論文卻沒有論文的縝密,似雜文卻沒有雜文的犀利,似隨筆卻沒有隨筆的恬淡,說是街談巷議,隨地吐痰一類,又似乎貶損了貢老師的價值。”
當作廖老的面,貢老還是滿謙虛的,貢老說:“廖老師的評價既中肯,又切中要害,貢某的那些文章其實就是雜感、雜談,目的是為了給讀者一份輕鬆,一份愉悅而已。”
五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上課和吃飯時間,我們基本上都見不到廖老,廖老也基本上不再接觸學生,更沒有主動找學生勾通一下的雅興,所以大多數的同學除了佩服廖老的治學態度外,基本上對他都敬而遠之,更不會主動去接近他,以免自討沒趣。
貢老則不同。只要高興,貢老就會自掏腰包請我們這幫窮學生吃夜宵,在學校真正意義上和學生打成一片的非貢老莫屬。我們都喜歡貢老,特別是我們這幫男生,只要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都願意向貢老提起,缺錢的時候,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向貢老借,貢老也樂意幫忙。至於女生,對貢老的態度就顯得有些含糊,有些不好說,不便說,或者說,好像她們更喜歡治學嚴謹的廖老一些。
貢老好酒,貪杯,每喝必高,必歡,必醉,必背誦古人的詩,尤其是李白的《將進酒》,而且往往用兩隻筷子擊碗而歌,我們也跟著他擊碗而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需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一個個搖頭晃腦,縱聲高歌,縱情狂笑,醉態可掬,儼然李白再生,又簡直是一群瘋子。
酒醉了的貢老仍忘不了對自己的弟子們諄諄教誨:“你們可要記住了,這個世間有三種人你們可要防著點,一種人是只會說好話的人;一種人是功利心太強的人;一種人是喝酒不會醉的人。”
我們當然知道他的意思,但還是逗他說:“貢老,你說的前兩種人好理解,就是第三種人,我有點不大明白。”
貢老說:“這正說明你道行淺,還正好修煉呢。我告訴你們,酒醉是性情中人,不會醉酒不知道醉酒者,要么是危險的,要么是虛偽的,要么就是冷血動物,這種人是不能處不可處也絕對沒有必要相處的最最最可怕的攻於心計的人。”
他指的當然是廖老了。但我們說:“不知道廖老喝不喝酒?”
貢老把臉一沉說:“最好別在酒場上提老廖,以免敗興。”
事實上,廖老是喝酒的,只不過廖老喜歡獨自一人躲進小樓慢慢品味,品出一篇篇悠長悠長的文章。廖老曾經說過:“喝酒圖的是個滋潤,為的是能夠激發某些方面的靈氣,濺放出思想的火花,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樣以酒亂性,丟人現眼。”我們也明白廖老指的是貢老。
有同學又說:“廖老喝不醉說明廖老酒量高,學問深。”
貢老更不高興了,惡狠狠地瞪了不知趣的弟子一眼,又惡狠狠地喝下一杯酒,然後說:“書蟲,書痴而已。”
顯然貢老認真了,我們就在肚裡偷著樂。
在酒桌上,貢老完全放下了老師的架子,儼然我們的朋友、大哥,既義氣豪爽,又放得開,玩得起。有時喝高了,我們要把他送回家,他卻堅決的不肯回去,說:“有如回去看老婆的嘴臉,不如再感受一下學生生活。”貢老到了學生宿舍就趁著酒興和同學們海闊天空神吹神侃,侃到大半夜,貢老也就在學生宿舍睡了。貢老睡了,我們卻睡不著,因為貢老的鼾聲也就隨之呼嘯而起,攪得整個宿舍不得安寧。
六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班畢業的那個晚會。我們幾個班委去請廖老,廖老說:“心意領了,但我就不去湊這份熱鬧了。我知道貢老師是最會營造氣氛掀起高潮的,這種場合更適合他參加。”
我們說:“貢老也是要請的。”
廖老說:“既然這樣,你們去請貢老師吧,我去了反而妨礙你們。”見我們失望的樣子,廖老有些無奈地嘆口氣說,“我老了,不合時宜了,只有貢老好像永遠走在時代的前列。”
我們又去請貢老,貢老問:“你們請了廖老師?”
我們說:“請了,但廖老說有事恐怕不能去。”
貢老冷冷一笑說:“我就知道你們的廖老是不會去的,廖老面子大,圖清靜,玩清高。只有我,沒面子,好湊熱鬧也清高不了!”貢老說這話時,好像是跟誰賭氣似的。
其實,他們倆人完全犯不著火與冰嘛!
晚會上,本來貢老是要唱一首《好漢歌》的,但主持人提高了嗓門連喊了數聲貢老師都沒有反映,於是主持人點了幾個人去找,找的人把貢老扶回來說,貢老醉了,爬在抽水馬桶上嘔吐,吐著吐著就在馬桶上睡著了。貢老望著大家嘿嘿笑了兩聲,說是身體虛弱,恐怕唱不了《好漢歌》,大家嚷著要他唱一首溫柔的,於是貢老就點了一首《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貢老搖搖晃晃走上台去,別聲別調,扭捏作態唱了起來,唱得不倫不類,完全和他這一米八幾的個子,和他的年齡極不相稱,幾乎笑瘋了整場晚會上的人。待大家緩過氣來,廖老卻意外地出現在了晚會上,頓時全場一下歡呼,掌聲如雷。大家嚷著要廖老來一首,廖老就點了一首《國際歌》,廖老背剪著雙手走上台去,閉著雙眼,雄雞般高昂著頭,一幅目中無人的樣子,完全和他講課的風格一樣,讓人忍不住想笑。出乎意料的是,廖老一開唱便顯出了自身的功力和水平,音質圓潤,聲音雄渾,唱得蒼涼而悲壯,給人一種靈魂上的震動。大家還要廖老唱,廖老又點了一首《畢業歌》,唱得豪情萬丈,熱血沸騰,把大家高亢的激情一下調動起來了。廖老成了中心,冷落在一旁的貢老坐不住了。貢老拉了我的手,悄悄對我說:“我頭暈得利害,你把我送下樓去。”我就把貢老悄悄送下了樓,我要送他回家,貢老不肯,說:“你還是回去同他們湊個熱鬧,同學一場也不容易。”貢老問我身上有沒有零錢,我說有。貢老說他身上都是幾張一百元的票子,要我拿兩張十元的給他好打“的”,我就拿了兩張十元的給他,並告訴他,裝在左邊口袋裡,然後,貢老便坐上了車,我也就回去繼續參加狂歡。待晚會接近尾聲,大家才猛然想起貢老來,我說,早已經走了。廖老笑說:“貢老的中心和主角的位置被鄙人占了,他自然只有知趣得——隱退了。”同學們就跟著笑了起來,廖老其實是冷幽默的,並不是那么古板和難以接近的。
第二天,貢老見面就問我,昨晚是不是拿了錢給他。我說兩張十元的,在左邊的口袋裡,貢老說:“兩張十元的還在口袋裡,可惜幾張一百元的飛了。”我們就笑他,可能是酒多了玩慷慨,掏了幾張百元的給了“的”哥“的”姐,還說“不用找了”。貢老就笑說,“喝酒人長的是豪情與氣概,最不長的是記心。”我們說有的時候花錢買痛快,也值。貢老笑笑,又說,“理解萬歲!只希望你們以後少喝一杯酒,多吃一坨肉,時刻牢記教師的話,永遠跟黨走。”這就是畢業時貢老對我們的贈言,現在想來也挺有意思。
七
有可靠訊息說,廖老在我們畢業兩年後就退了,退了的廖老也不知什麼原因,竟然放棄了他的研究,之後,可能是閒極無聊,廖老竟然結婚了。這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我可以相信任何人結婚,卻怎么也不願意相信廖老結婚。結了婚的廖老也寫文章,但寫的是他當年所不恥的“豆腐小快”,好的是報紙為他專門開闢了一個小專欄。從古代名人的一些小故事發掘一些似乎深刻的大道理。同樣來源的訊息說,貢老離婚了,離婚後的貢老也許是不甘寂寞,在授課之餘開了一家心理諮詢診所,專為都市裡的那些少男少女們進行心理診治。貢老已不再寫文章,但揚言要弄就要弄一部有轟動效應的大型電視劇。貢老的再次離婚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但開辦心理診所卻超越了我的想像範圍。不過,很多事情細細想來,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全文完)
參考資料
[1]小說閱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