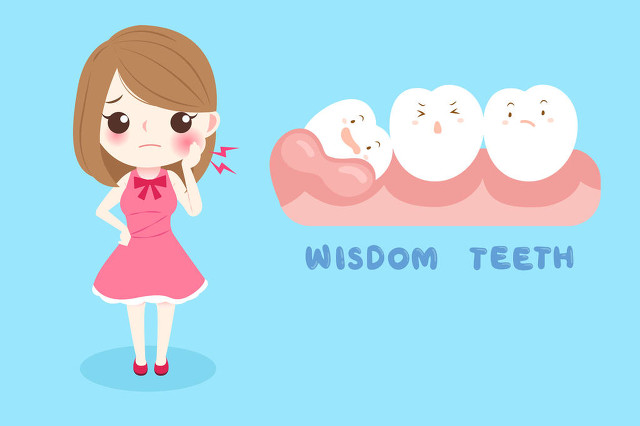在魯中地區,做豆腐一般叫做“出豆腐”,對於生長在魯中鄉村地區的人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回憶。
誰是第一個“出豆腐”的?恐怕無從考證。史書記載,漢代的淮南王劉安喜歡煉丹,周圍聚集了一幫道士。煉丹必用鹽滷,將鹽滷加熱就得到了氯化氫,氯化氫與水結合就得到了鹽酸,以便從礦石中提取金屬元素。一個道士無意中把鹵鹼掉入豆漿里,沒有想到,豆漿竟凝固了。這個道士認為豆漿腐敗了,但其他的道士嘗了嘗,覺得細膩可口,就吃了,事後也沒有不良反應。於是,世界上就出現了一種新的食品——豆腐。漢樂府歌詞《淮南王篇》記載:“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銀綆汲寒漿。”因此說豆腐是西漢的劉安發明的,似無不妥。
 出豆腐
出豆腐煉丹煉出豆腐,這只是豆腐發明的一種版本。在淄博市淄川區還有一種關於豆腐的傳說,比淮南王要早幾百年:戰國時期鬼谷子曾在淄川東北的梓橦山授徒講學,由學生龐涓和孫臏照顧起居,每日輪流給老師製作豆漿。龐涓嫉妒孫臏的才華,偷偷地在孫臏準備的豆漿里放鹵鹽,想讓先生疏遠孫臏。哪知加入鹵鹽的豆漿凝結成糊狀物,味道竟然比豆漿好得多。於是鹽滷點豆腐的技巧流傳開來,散播於民間。歷史上鬼谷子來齊國講學確有其事,孫斌、龐涓也的確是先生的高足,淄川雙楊、寨里周邊也普遍流傳著“孫龐豆腐”的故事,故而此傳說似乎也有幾分可信。
無論是鬼谷子還是煉丹的道士,他們吃到的只是豆腐腦,嚴格說來還不算真正意義上的豆腐,味道估計也不會很美妙,比如道士的感覺僅僅是不難吃而已。任何一項食品工藝的發明絕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經過萬千民眾的不斷嘗試改良才能臻於完善。豆腐的製作發明過程也大抵如是。
豆腐的發明無疑是一項偉大的創舉。人們自從會“出豆腐”,才告別了炒豆子、煮豆子、蒸豆子等單調乏味的吃法,將豆子這種普通平凡的食材吃出了層次與境界,甚至品出了格調與情致。自古以來,詠嘆豆腐的詩歌宛如一道風景優美的長廊,多少文人墨客,藉以豆腐的特別質地來表達他們的美好節操和高雅品格,達到了物我合一的藝術境界。宋代的蘇東坡在《蜜酒歌》里寫道:“炙青莆,爛蒸鵝鴨乃匏壺,煮豆作乳脂為酥,高燒油燭斟蜜酒。”其時,豆腐還只是一道配菜。元代張劭著有《豆腐詩》:“漉珠磨雪濕霏霏,煉作瓊漿起素衣。出匣寧愁方璧碎,憂羹常見白雲飛。蔬盤慣雜同羊酪,象箸難挑比髓肥。卻笑北平思食乳,霜刀不切粉酥歸。”在這裡,豆腐不但已成宴席上的主角,而且被華麗的辭藻裝扮包裹,從磨漿到生成,從品相到口感,張劭均不吝辭彙,賦予了豆腐一份高雅的格調,一絲文化的氣息。
 出豆腐
出豆腐在農村人眼裡,豆腐只是一盤家常菜而已,斷然吃不出以上諸般境界。在魯中地區,豆腐的生產過程也冠以頗為土氣的“出”字。三、四十年前,魯中農村是這樣“出豆腐”的:
第一步:挑豆子
大豆在深秋收成,往往逢上陰雨天,難免會有一些豆粒霉爛。農家做豆腐對原材料很講究,先用簸箕簸去殘留的豆莖、豆葉,再用篩子篩掉細碎的土塊石子,還要把發霉的、秕巴的、有蟲眼兒的精心挑出來。豆腐做來自己吃是這樣,若是賣給別人,那得挑得越發仔細。挑豆子這道工序絕不可省儉,因為發霉的豆子會嚴重影響豆腐的品相和口感,一旦砸了牌子,就沒有人再來買豆腐了。那時的農村,沒有食品衛生之類的監督,也沒有重品牌講信譽之類的表彰,但淳樸的農人卻始終秉承著亘古綿延的傳統,不摻假使孬,不以次充好,也極少會缺斤短兩。偶爾會聽到買豆腐的提醒“給夠稱啊!”賣豆腐的會發誓般地說“短了稱,恁先砸了我的稱,再砸我的人!”
第二步:泡發豆子
泡發豆子一般用溫水,溫度因四季不同而各異,全憑經驗。泡豆子的時間也很有學問:時間短了,豆子沒有吸足水分,很硬,石磨磨不細,影響出漿;泡的時間過長,營養會流失,並且豆體膨脹過度,微微散發出一股霉味,影響豆腐的質量。泡的時間不夠,可以再泡,可一旦泡過了頭,變了味兒,那就麻煩了,做出來的豆腐沒人要,只好自家“內部消化”,曬成豆腐乾,或者做成霉豆腐(農村叫做“si”豆腐),再就是白送人了。一般說來,泡四、五個小時為適宜。有經驗的人往往捏一粒豆子,捻一捻,放在鼻子下聞一聞,就能判斷是否已經泡好。
第三步:磨豆糊子
 磨豆子
磨豆子磨豆糊子一般用石磨。石磨的底座鑿有凹槽,可以接住磨下來的豆糊。底座上面是由一根鋼杵連線的上下兩個磨盤,下面的固定,上面的靠人力或毛驢轉動。磨盤上有一個拳頭般粗細的磨眼兒,豆子就是從磨眼兒里填進去,隨著磨盤的轉動一點點碾進磨盤中,磨成豆糊子。如果一次放入的豆子太多,或者豆子太乾,很容易卡住,不往下走,磨就空轉。於是就在磨眼兒里插上一根筷子或者莛[tíng] 子(高粱秫秸的最後一節,去掉高粱穗的部分),叫做“籌”,能讓糧食順利地通過磨眼兒到達磨盤中間。農村裡面不乏語言大師,有句歇後語“磨眼兒里插竹竿——頂天立地的籌(仇)”說得形象生動又接地氣。
推磨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轉著圈推的,推完一盆豆子要機械重複地轉若干圈。所謂“光著腚推磨——轉著圈兒丟人”,指的就是這種;還有一種是人不走動,全靠兩隻胳膊來回推拉固定在磨盤上的曲木棍,帶動磨盤轉動,叫“推拐磨”,因動作推過來搗過來,因此又稱作“搗磨”。淄博五音戲《王小趕腳》里,男主角伸胳膊蹬腿做的那個動作,就是在推拐磨。儘管省去了走路,但時間久了,胳膊、腿也會累得酸疼,因此農婦們經常抱怨“成天就是搗磨推碾,燒火做飯。”
推磨既枯燥又累人,沒人樂意乾,尤其是小孩子。小時候家裡出豆腐,賣豆腐,放學之後書包一放,撿起磨棍就得推磨。為了磨得細,多出豆漿,還要將磨成的豆糊子再磨一遍。耳聽小夥伴們在街上瘋跑叫喊,就想著快點推完也出去玩。往往是推完了磨,天已黑透了,街上早已沒了人,心裡很失落。那時有個理想:什麼時候能不推磨,放了學就能痛痛快快地玩該多好。記得有一次,很想出去玩,不想推磨,很有情緒,故意使勁不勻和,一股子一股子地,結果把“磨系(連線磨盤和木棍的繩子)”給扽斷了。這樣的把戲顯然瞞不過母親,結果挨了一頓揍。
一個人推磨覺得累,有時就兩個人推,條件好的還會用毛驢。為防止毛驢偷吃,要把靠近磨盤一側的眼給擋住。可毛驢也有智商高的,還是能偷吃到。更有“懶犍”驢,不願出力,一駕上套,連拉帶尿弄得滿地都是。主人怕弄髒了糧食,便解下繩套,打罵著趕到一邊去了。所以,對於那些一到出力之時便玩“尿遁”的奸滑之人,農人也送一句歇後語——“懶驢上磨屎尿多”。
第四步:濾豆汁
磨好的豆糊從磨盤上刮下來,盛在一個直徑大約1米的大盆里,倒進溫水,充分攪拌,豆糊被充分稀釋,呈豆漿狀。不過這可不是真正的豆漿,接下來要濾出豆渣,剩下的才是豆漿,豆漿燒開了,才是我們現在早上喝的豆汁。通常在大鍋上橫放一張籮床,籮床上面放一個紗布做的布袋,用瓢舀來豆糊倒入口袋,用手反覆按壓,豆汁不斷地濾出來,流進鍋里。壓布袋是個力氣活,長期出豆腐的人,老了大多會腰疼、胳膊疼,老百姓叫做“出透了力”,實際上就是筋骨勞損。為了省力氣,有些“講究”人家會在大鍋上方支起一個木架子,吊住紗布的四個角,只管往紗布裡面倒入豆糊,就可以不斷地濾出豆汁了。
第五步:燒“汁子”鍋
豆汁要燒開才能點成豆腐。盛滿生豆汁的大鍋叫做“汁子”鍋,要燒開一鍋“汁子”需要持續不斷的旺火,因此用一般的玉米秸稈等“暄”柴火不行,最好是比較結實的乾樹枝。木器廠鋸木頭產生大量的鋸末,耐燒,煙少,是出豆腐最好的燃料。小時候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要和哥哥到附近煤礦上的木料廠推鋸末,一塊五一車。為了能多裝一些,要站到簍子上使勁踩,簍子邊緣兒插上小木板,一直裝到“垛出尖兒”來。如果運氣好,還能撿到一些樺樹皮,潔白光滑,散發著原木的清香,用火柴就能點燃,發出滋滋啦啦的聲音。鄰居家的小夥伴都來淘換這稀罕物兒,晚上在街上玩兒時點起來照明。
火要燒得旺,需要鼓風助燃。農村幾乎家家有木頭做的鼓風工具——風箱。一推一拉,用力要均勻,灶膛里的活隨著一起一伏,像做廣播操的學生在伸胳膊蜷腿兒,努力地去觸摸鍋底。燒開一鍋豆汁大約需要一個多小時。灶膛空間很大,就在裡面放一些地瓜。鍋還沒有燒開,地瓜早已烤熟,散發著誘人的香氣,掰開一塊,黃燦燦,香噴噴。母親從傍晚一直在幹活兒,還沒吃飯,往往靠這幾塊地瓜充飢。烤地瓜雖然聞著香,但是吃多了容易反酸胃脹。記憶中最深刻的莫過於,出完一包豆腐,母親疲憊地坐在炕沿上,一個勁兒地吐酸水。有時講到這些事情,兒子似乎開玩笑地說:“你們小時候真幸福,天天吃綠色食品”。是啊,地瓜如今身價大增,小區門口的烤地瓜一塊賣七八元呢!吃烤地瓜可算得上高消費了。可是頓頓吃地瓜的日子實在不好過。
第六步:點豆腐腦
“滷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點豆腐腦是技術活,也是出豆腐最關鍵的一步。上一包豆腐濾出的水叫“漿”,發酵後的漿叫做“酸漿”。待燒開的汁子鍋逐漸停止沸騰,舀起一瓢“酸漿”,均勻地、緩緩地澆進去,於是奇妙的變化產生了:豆汁慢慢凝結成塊,聚成團,變成了豆腐腦。期間會因“酸漿”的原因(應該是PH值的高低)、豆汁的溫度、澆注的多少、快慢或者其他原因,導致豆腐腦的數量、質量有差異,當然會影響豆腐的產出。因此,點豆腐腦時,老人們似乎懷著很虔誠乃至神聖的味道:神情嚴肅,動作沉穩,小孩子也不能亂說亂動。村裡有個二流子,心眼兒壞,總是估摸著點豆腐腦的時間在街上說髒話,把老人恨得不行。
酸漿點成的豆腐叫“漿豆腐”,質地細嫩,口感好,但是產量低。於是,從外面傳入另一種點法,石膏點豆腐,先將石膏焙乾,碾碎,溫水泡開,點法同點“酸漿”。石膏點出的豆腐叫做“膏豆腐”,產量高,結實,但因為其中的技術掌握不好,有時口感不好,甚至能感覺到牙磣。書江大哥出了大半輩子豆腐,自然對此有豐富的經驗。他只要嘗一小口,就知道是怎們回事兒,意味深長地笑笑,說:“你這是膏豆腐”,再問,就諱莫如深了。
第七步:出鍋,上模子,壓成型
 上模子
上模子這是最後一步了。模子裡要事先鋪上一層紗布,將豆腐腦舀進模子裡,慮出水分,豆腐就成型了。這個過程不能太慢,太慢了,豆腐腦涼了,不好成型;也不能太快,太快了,慮不乾淨水分,這倒充滿了辯證法。把包袱的四個角依次折向模子的中央,上面蓋上一方形的蓋簾兒,蓋簾兒上面再壓上一塊重物,放置一宿,將水分控乾淨。最後撤去模子,打開包袱,大功告成了。
第二天一早,母親將一包豆腐切成四大塊,小心地將一大塊放進一個小提籃里。姐姐一頭挑著豆腐,另一頭挑著一個空的大提籃,敲著梆子出門賣豆腐了。說是賣豆腐,其實真正用錢買的人很少。家屬還在農村裡的“工人”,有時用錢買。還有就是“出賦”的農民。那時的“出賦”指的是農民冬天義務開山、修水庫,“公家”每天會給幾毛錢的補貼。因此工地上開大力氣的中午多用錢買豆腐。將醃鹹菜的鹽水,加一些韭菜花做成免費的“蘸水”,很受歡迎。花幾毛錢買一塊熱乎乎的豆腐,就著“蘸水”,啃著從家帶來的烙餅,於人群中開著粗俗的玩笑,成為中午工地的一道風景。
絕大多數農村人是用地瓜乾“換豆腐”,豆腐挑子前面的大提籃就是用來盛放地瓜乾的。一般是二、三斤地瓜乾換一斤豆腐,掙的就是其中的差價。不過需要將換來的地瓜乾推到集市上賣掉,才能變成現錢,再去糴豆子,特別辛苦。豆腐賣不了又留不住,就多撒鹽,做成豆腐乾,留著自己吃。夏天氣溫高,上午賣不了,下午就“si腦了”,只能做成“si豆腐”。如果剩下或壞掉的多了,出一包豆腐也就白忙活了,因此出豆腐掙不了多少錢。有一次,母親去趕集,賣地瓜乾攢下來準備糴豆子的幾十塊錢讓小偷偷去了,當時這是一筆“巨款”,母親很受打擊,躺在炕上幾天不吃不喝,至今想起來都覺得難受。因此至今對小偷一直懷有仇恨,最受不了那些“小偷也有人權”的觀點,或者不明就裡替小偷說情的人。
小時候最不願吃的食物“si豆腐”,現如今卻成了美味,單位食堂里有,去得晚了,往往還吃不上呢!真的是“時、位之移人”!
三、四十年前,出豆腐、賣豆腐是一件不得已而為之的餬口營生,辛苦操勞而收入微薄。一句諺語“後晌(晚上)想了千條路,早上起來賣豆腐”,道盡了“出豆腐”的不想乾又不得不乾的酸楚無奈。當然,現在農村里出豆腐都已經“現代化了”,有磨糊機、榨汁機、電動鼓風機,出力少了,豆腐出得多了,更重要的是現在吃豆腐的人多了,基本不用出門去賣了。國小同學現在村里出豆腐,一上午能賣出好幾百斤,下午還耽誤不了乾農活,生活儼然居於村裡的中上游呢。賣豆腐也不再敲棒子了,弄個電聲喇叭,在家喊一遍錄下來,循環播放,省勁兒多了。
不過還是非常懷念小時候的一首兒歌:
“梆梆梆,賣豆腐,
一直賣到山後頭。
山後頭,有間屋,
一個小孩兒在那哭。
哭的啥?
他娘不給他娶媳婦。
娶了媳婦幹啥?
做鞋、做襪,
拉呱、說話。”
打小就會唱,可始終有個疑問:是賣豆腐的看見小孩兒在哭,還是賣豆腐的走至山間僻靜處,想到老大不小卻難以娶妻成家而傷心落淚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如今都過著童年時想都不敢想的生活,“電燈電話,樓上樓下”早已不是事兒了,豪車別墅似乎也指日可期。只是不經意間猛然發現自己已經“奔五、奔六”了。
上了年紀的人容易懷舊。
 出豆腐
出豆腐讓“出豆腐”帶我們回到童年,重溫那些即將消退的記憶。
蘇東坡 魯中 淄博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