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1世紀新生物學
21世紀新生物學比如,奧地利遺傳學家格雷戈爾·孟德爾從對豌豆的研究觀察中發現了遺傳的基本規律;法國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麥蘭從向日葵的朝向發現了晝夜節律;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薩姆納從刀豆中首次獲得了尿素酶的結晶;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芭芭拉·麥克林托克通過對玉米的研究獲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新發現,即玉米中的可移動基因——俗稱“跳躍基因”……
如今,植物在許多令人振奮的新領域中,更是引領著科技新潮流。
植物學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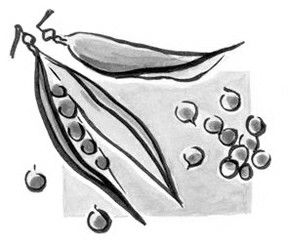 21世紀新生物學
21世紀新生物學“植物結構的複雜性超出了工程師們的想像,”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教授艾略特·邁耶羅維茨和喬治·比德爾說,“如果我們能理解這些機制,將會在工程學領域內開拓新的視界。”
學術價值
獲取這些新知識不僅具有學術上的重要價值,同時還擁有許多實際用途。比如,了解激素的複雜機制,就能用來控制植物的生長;了解植物的生物化學機制,就能讓植物獲得更強的抗病害蟲能力和抗乾旱能力。尤其是目前對於面臨全球多種挑戰的人類來說,這已經是當務之急。而聯合國的一些統計數字發人深省:預計到2050年,全球在目前68億人口的基礎上將再激增30億,其中有近1億的人口正在承受著營養不良的痛苦。同時,世界對能源的需求也在呈持續上升趨勢,長期使用化石燃料產生的後果正日益明顯,土地在需要生長糧食的同時,還要種植生物燃料作物,所有這些都對農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包括氣候變化正在帶來或醞釀一些風險極大的災難性後果,比如,威脅著地球上最重要的小麥主產區的稈鏽菌Ug99的傳播。因此,人類必須考慮如何生產出更多的糧食和用作燃料或能源的植物材料。
“2050年左右將多增加30億人口,但土地資源不會增加,淡水資源也不會增多,同時還要面對地球氣候發生的重大變化,所有這些都將對農業產生重大影響”,美國糧食和農業研究所主任羅傑·比切說,“我們需要改變農業,使作物在氣候真正變暖後仍然可以正常種植,在較少灌溉水和較少使用化肥的情況下仍然能夠高產。我們需要不怕蟲害的植物,我們需要在氣候變暖時不會生病的植物。”
促資研究
2008年9月,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NRC)開始關注一些最為緊迫的社會問題——食品、環境、能源、健康等——並探尋生物學研究可以作出最大貢獻的一些領域。“很明顯,幾乎在所有上述領域內,植物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途徑和主要來源,關鍵是能否及時獲得解決方案。”NRC“21世紀新生物學”委員會副主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赫綜合癌症研究所教授、諾貝爾獎得主菲利普·A·夏普說。而比切認為,有這么多的東西需要去學習和了解,他擔心的是我們的學習速度是否足夠快。在面對如此多的緊迫任務的時候,人們可能會認為植物研究在世界各地都會得到重視和資助。中國近年來比較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在糧食生產不足的印度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但在糧食充裕的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對植物研究卻並不那么重視。在美國,生命科學中的植物學研究是最不為人關注的,聯邦政府每年撥予生命科學研究400億美元的經費預算中,植物學研究所占的比例不足2%,獲大頭的則是生物醫學研究。
解釋原因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只對我們本身感興趣,”喬瑞解釋說,“國會的人往往將著眼點放在疾病和人類健康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農業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在不久前,聯邦政府欲承擔數十億美元的代價在部分地區對種植業做出一些限制。“為什麼要花錢去研究讓農民生產更多作物的方法呢?”比切說,“正是我們的成功在一直阻礙著我們。”
研究經費之間的差距在美國的一些研究型大學中也非常明顯。傑出的植物學家維基·錢德勒說,從事癌症研究的實驗室往往擁有大量的博士後和研究生,而研究植物的科學家所獲得的撥款只夠支持一位博士後研究員和一位技師。如果要支撐一個卓有成效的實驗室則“十分困難”,許多有前途的研究生必須放棄植物學研究才能找到有經費支持的項目。對此,比切認為,“如果僅僅是經費的原因而無法實現目標,這是一種恥辱。”
然而,並非都是壞訊息。儘管支持度相對較低,植物生物學家和遺傳學家在過去的10~15年內,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當喬瑞於1985年從細菌學研究轉向植物生物學研究時,“已發現了一種植物受體,”她回憶說。如今,有了新的研究工具以及阿拉伯芥、擬南芥等植物遺傳、生理和進化生物學研究的模式植物,植物生物學家對這些植物所進行的遺傳基因測序獲得了大量植物遺傳學的知識。科學家們預言,植物基因組裡存在著數百種基因編碼的受體,目前已確定了這些已知植物激素的受體。
例如,光生物學家已經了解到,植物中的某種光受體可感知附近植物的蔭蔽,從非常現實的意義上來說,它能感知到與其爭奪陽光的競爭對手——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植物就會調整生長激素,加快其生長速度。當然,這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在加速生長的同時,植物會降低對病蟲害的防禦能力。即植物群中的某一植物為爭取在植物中長得最高的優勢,即使意味著更容易受到蟲害的侵襲也在所不惜。在研究中,喬瑞與德國圖賓根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德特勒夫·威格爾還了解到,瑞典等受光照較低國家的植物,其感光受體的敏感程度是陽光明媚的西班牙同類植物的10倍以上。
比切認為,“我們對遺傳學的研究工具已經投入了許多,加大對植物學研究的投資時機已經成熟。”夏普補充道,加大投資“很可能會引發最大的知識爆炸,由於之前在該領域內投資嚴重不足,意味著加大投資會有更多回報的機會。”
發展前景
機會在哪裡?“下一個挑戰除了產量,還是產量,”喬瑞說。這意味著要繪製出成百上千種植物的基因圖表及其細節,然後再學會如何操縱這些基因。NRC在“21世紀新生物學”報告中指出:“我們目前擁有的只是植物零件的清單,而不是彙編指令。”
如果我們能夠對玉米基因的彙編指令進行調整,是否能使其根系發展與土壤中的固氮微生物的關係更為密切,並以此減少其對肥料的需求?“確實有一些植物知道它們該怎么做,”錢德勒說,“甘蔗就和土壤擁有這種密切的關係,所以對氮肥的要求遠遠低於玉米。”
我們可以發揮充分的想像力,想像如何通過植物生長出大量的生物質原料,包括是否有可能對草原上的牧草進行一些生物學上的改變,即通過“生物學精煉”途徑,將牧草細胞壁上的纖維素改造成乙醇或其他燃料等化學物質呢?對此,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的傑拉爾德·芬克、懷特黑德生物醫學研究所的瑪格麗特·索科爾教授認為,“儘管目前這些還都只是科幻小說般的想像,但它有可能會成為現實。”
通過生物化學途徑實現的看似微小的變化會產生巨大的差異。以植物最基本的功能為例,通過光合作用,將陽光的能量轉換成為植物的莖、葉、種子和果實,這一過程的核心是一種稱為Rubisco的酶——它吸收二氧化碳,並將其結合進生物質中。喬瑞說,Rubisco酶可能是地球上最豐富的蛋白質,約占植物葉片總蛋白的30%,同時它也是一種非常低效的酶。比切表示,儘管植物只能捕獲陽光照射中大約2.5%的能量,但若能進行基因調整以提高Rubisco酶對陽光能量的吸收率,比方說達到3%,我們就可以解決世界糧食問題了。
即使無法提高酶的效率,通過對整個光合作用過程進行基因工程的重新設計,也能提高效率。約3%的植物(包括玉米和甘蔗在內)採用的是C4光合固碳途徑,固碳產生四個碳原子,而不是更為普遍的C3途徑那樣產生三個碳原子——C4途徑不僅吸碳效率更有效,對水分的要求也更少。因此,若將C4途徑加入到C3植物中,可大大提高其生長速度,同時也更為耐旱。據劍橋大學的朱利安·希伯德估計,加入C4途徑基因工程改造的水稻產量可提高50%。
研究主線
所有這些新發現對科學家來說十分誘人,但錢德勒指出,“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比切和其他一些人認為,如果研究植物的科學家團隊與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合作,採取更廣泛更系統的研究方法,這一領域內將會有更多的發現。例如,為什麼某些植物會形成共生植物群?這種生態系統是如何形成的?喬瑞說:“要了解某種生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緊迫形勢下,植物研究的另一條主線是,隨著環境變化壓力的加重,如何面對植物病害可能加劇的問題。對此,美國植物生物學學會執行理事克里斯平·泰勒說:“一個系統的生物學方法可以觀察到植物某種病原體分子結構的詳細情況,以及給植物帶來的種種壓力所產生的變化。”
加州理工學院的邁耶羅維茨說:“通過數學與工程學的結合,以了解植物的生長機制,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研究前沿。”例如,一棵樹的分支結構,是基因和機械應力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因這種互動以及細胞的實際物理結構而形成的樹木的分叉結構,可用數學方法建立起某種模型。
然而,大多數的實際套用還有待於未來的研究。目前正在進行中的項目有提高高粱的營養成分、提高植物根系對氮的吸收能力、給木薯等作物補充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等營養物質,以及更好地了解我們從植物中獲得的營養與人類健康之間的聯繫等。孟山都公司的科學家已經承諾,到2030年他們能夠將玉米、大豆和棉花的產量提高一倍。對此,夏普認為,到目前為止“對於所有這些可能性,我們只是做了一些粗淺的嘗試而已。”
總而言之,植物研究的成果不僅在神經科學、癌症生物學領域內令人興奮,同時還提供了一個拯救世界的機會。科學家指出,推動植物研究的發展將有賴於各方面的支持。夏普說:“種種機會就在我們眼前,但植物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面臨著資金不足的困境。”而比切擔心的則是基礎科學的研發和公司開發能力之間的巨大差距,眼前的重點應放在能夠獲得快速經濟回報的產品之上。他說:“目前尚未有足夠的資源與途徑來填補這一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