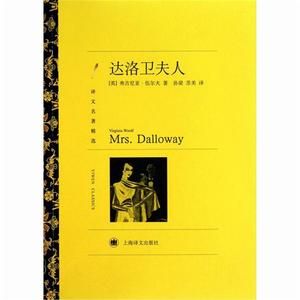二、內容簡介
英國著名意識流作家伍爾夫的意識流作品,強調了女權主義.
維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衛夫人》情節非常簡單,就是寫了一天的事情。從達洛衛夫人早上買花、籌備晚會寫起,一直寫到子夜晚會結束、賓客離去為止。
就是這一天里,達洛衛夫人時時刻刻在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懷疑。表面上的上層社會華麗舒適的生活方式,與內心的空虛交織在一起,使達洛衛夫人有一種難以言說的絕望。
請看下面這一段。早上,她看到鏡子中的自己,突然百感交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感受。
她將胸針放在桌上,心中突然一征,仿佛在她沉思的時候,一隻冰冷的魔爪趁機抓住了她。她還不老,剛剛跨進了人生第52個年頭。還有許多的歲月等著她去過。六月,七月,八月!每一個還幾乎都是完整的。就好像想抓住天上落下的雨滴一樣,達洛衛夫人(走到梳妝檯旁)一下子縱身進入了這個時刻的核心,將它刺穿。這個時刻,這個六月的清晨,所有其他清晨的壓力都湧來了。她再一次看著鏡子,看著梳妝桌,看著那些小瓶子。(當她凝視鏡子的時候,)在這一瞬間,她看到了整個的她自己,她看到了一個女人精緻的粉紅色的面孔,這個女人今天晚上就要舉辦一場晚會。這張面孔就是克萊麗莎·達洛衛夫人的面孔,也就是她自己的面孔。
Laying herbroochon the table, she had a sudden spasm, as if, while she mused, the icy claws had had the chance to fix in her. She was not old yet. She had just broken into her fifty-second year. Months and months of it were stilluntouched. June, July, August! Each still remained almost whole, and, as if to catch the falling drop, Clarissa (crossing to the dressing-table) plunged into the very heart of the moment, transfixed it, there—the moment of this June morning on which was the pressure of all the other mornings, seeing the glass, the dressing-table, and all the bottlesafresh, collecting the whole of her at one point (as she looked into the glass), seeing the delicate pink face of the woman who was that very night to give a party; of Clarissa Dalloway; of herself.
三、作者簡介
維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英國意識流文學的代有性作家之一。是20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女性作家、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又是西方女權主義的先驅者之一。著作有:《到燈塔去》、《海浪》、《黛洛維夫人》、《奧爾蘭多》《一間自己的房間》、《三個基尼》以及散文《時常上街去走》。
四、圖書文摘
書摘
然而,她心中有一個兇殘的怪物在騷動!這令她焦躁不安。她的心靈宛如枝葉繁茂的森林,而在這密林深處,她仿佛聽到樹枝的嘩剝聲,感到馬蹄在踐踏,她再也不會覺得心滿意足,或心安理得,因為那怪物——內心的仇恨——隨時都會攪亂她的心,特別從她大病以來,這種仇恨的心情會使她感到皮膚破損、脊背挫傷,使她蒙受肉體的痛楚,並且使一切對於美、友誼、健康、愛情和建立幸福家庭的樂趣都象臨風的小樹那樣搖晃,顫抖,垂倒,似乎確有一個怪物在刨根挖地,似乎她的心滿意足只不過是孤芳自賞!仇恨之心多可怕呵!
要不得!要不得!她在心中喊叫,一面推開馬爾伯里花店的鏇門。
她挺直頎長的身子,邁著輕快的步伐向前走去,皮姆小姐立刻上前招呼。這位女士天生一張鈕扣形的臉,雙手老是通紅,好象曾經捧了鮮花浸在冷水裡似的。
這兒是鮮花的世界:翠雀、香豌豆、一束束紫丁香,還有香石竹,一大堆香石竹,更有玫瑰、三尾鳶,啊,多可愛——她就站著與皮姆小姐交談,一面吮吸這洋溢著泥土氣息的花園的清香。皮姆小姐曾得到她的恩惠,因而覺得她心腸好;確實,好多年以前,她就是個好心人,非常和善,可是今年她見老了。她在三尾鳶、玫瑰和一簇簇搖曳的紫丁香叢中,眯著眼睛兩邊觀望,貪婪地聞著那令人心醉的芳香,領略著沁人心脾的涼爽,驅散了剛才街頭的喧鬧。過了一會,她睜開雙目:玫瑰花兒,多么清新,恰似剛在洗衣房裡熨洗乾淨、整齊地放在柳條盤中的花邊亞麻織物,紅色的香石竹濃郁端莊,花朵挺秀,紫羅蘭色、白色和淡色的香豌豆花簇擁在幾隻碗中——仿佛已是薄暮,穿薄紗衣的少女在美妙的夏日過後,來到戶外,採擷香豌豆和玫瑰,天色幾乎一片湛藍,四處盛開著翠雀、香石竹和百合花;正是傍晚六七點鐘,在那一刻,每一種花朵——玫瑰、香石竹、三昆鳶、紫丁香——都閃耀著:白色、紫色、紅色和深橙交織在一起,每一種花似乎各自在朦朧的花床中柔和地、純潔地燃燒;喔,她多喜愛那灰白色的小飛蛾,在香水草四周,在暮色中的報春花四周飛進飛出。
就象修女退隱,又象孩子在寶塔上探險,她走上樓去,在窗前停留片刻,走進浴室。室內鋪著綠色地氈,有一個水龍頭在滴水。生命的核心一片空虛,宛如空蕩蕩的小閣樓。女人必須摘下漂亮的衣飾。她們必須在中午卸裝。她把發針插入針插,把綴著羽毛的黃帽子放在床上。寬大的白床單十分潔淨,兩邊拉得筆挺。她的床會越來越窄。半支蠟燭已燃盡。她曾經入迷地
讀馬伯特貝爵的回憶錄,在深夜裡念著關於從莫斯科撤退的記載。閃為議院會議很長,理察回來得晚,所以他堅持,必須讓她在病後獨自安睡。然而,實際上她寧願讀有關從莫斯科撤退的記載。這一點他也知道。於是她便獨自睡在斗室中,在一張窄床上,由於睡不好,就躺著看書,心裡總感到,自己雖然生過孩子,卻依然保持童貞,這一想法恰如裹在身上的床單,無法
消除。她在少女時期多么可愛,而忽然,有那么一刻——譬如那一回在克利夫登樹林下的河岸邊——當時,就由於那種冷漠的性情,她讓他失望了。另一回是在康斯川丁堡,以後一再發生同樣的情況。她知道自己的缺陷。說到底,既不是美貌,也不是理智,而是一種內在的核心,滲透全身,一種熱烈的情感衝破表層,使男女或女性之間冷淡的接觸變得波動。她能隱約地覺察到這點。她厭惡它,對它懷有莫名其妙的戒心,她覺得,或許是天生的,乃是(一貫明智的)大自然所賜;可她有時卻不禁被一個女人的魅力吸引,並非被一個少女,而是被一個訴說自己的困窘或愚蠢行為的女人所吸引,她們經常來向她傾訴。不管是出於憐憫,還是迷戀她們的美貌,或者因為自己年長,或者完全由於偶然的巧合——譬如,聞到一縷幽香,聽到鄰家的小提琴聲(在某種時刻,聲音的力量如此奇異)——她在那時確實感受到人們均有的感覺。這一感覺瞬息即逝,但已足夠。那是一種驟然的啟示,恰如一絲紅暈,仿佛一個人在臉紅時,想遏制,卻越漲越紅,也就任其自然,急忙跑到最遠的角落,在那裡微微顫抖,感到外界逼近、膨脹,孕育著某種驚人的意蘊、某種壓不住的狂喜,它衝破稀薄的表層,噴涌而出,帶著無窮的慰藉,去填補裂痕和創痛。然後,就在那一瞬間,她看見了光明:一根火柴在一朵藏紅花中燃燒,一種內涵的奧妙幾乎得到詮釋了。然而,近景消失,堅硬的物質軟化了。那一瞬間——消逝了。同這些時刻(包括跟女人在一起的時刻)相比(她放下帽子),眼前只有一張床、馬伯特男爵的書、燒剩的半支蠟燭。她躺在床上,無法入眠,聽見地板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燈光照亮的屋子驀地暗下來:要是她抬起頭,便能隱約聽到理察非常輕地轉動門把時發出微微的咔嗒聲,他只穿著襪子,躡手躡腳地上樓,卻經常失手把熱水袋掉在地上,於是他狠狠地罵自己!當下,她笑得多歡呵!
可是(她把外套撂在一邊,思索著),關於愛情這一問題,同女人的相愛,又是怎么回事呢?就說薩利·賽頓吧,自己過去和薩利·賽頓的關係,難道不是愛情嗎?
奇怪的是,在他熟識的人中間,她是最徹底的無神論者,也許(她在某些方面令人一眼見底,在另一些方面卻十分難以捉摸,以前他慣於用這種想法去解釋她的為人)她對自己這么說:既然我們的民族被鎖在即將沉沒的船上,注定要滅亡(她少女時代最愛讀赫克斯利和廷德爾的著作,兩人都愛用海上生涯的比喻),既然這一切只不過是可怕的笑話,就讓我們至少盡一份力吧,減輕我們同室囚徒的痛苦(又是赫克斯利的語言),用鮮花和氣墊裝飾地牢,儘可能保持體面吧。那些凶神惡煞,不能讓他們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她認為,神始終在利用每一個社會去傷害、妨礙、摧毀人的生命,但是只要你舉止端莊,不失大家閨秀的風範,那么神的威力就會大受挫折。她那種心情完全是受了西爾維亞之死——那件可怕的事——的影響。克拉麗
莎老是說,目睹自己的親姐妹被一棵倒下的樹壓死(那全是賈斯廷·帕里的過錯——全怪他不小心),足以使你憤世嫉俗,當時西爾維亞也正當豆蔻年華,又絕頂聰敏,在姊妹中最為出色。或許,後來克拉麗莎不那么憤慨了,她認為沒有什麼神,也不是任何人的過錯,這樣她就形成了一套無神論者的宗教——為善而善。
誠然,她生活得很幸福。她天生就喜愛生活的樂趣(雖然,天曉得,她也善於掩飾內心,儘管與她相處多年,他仍經常感到,自己對她的了解還相當膚淺)。不管怎樣,她並不怨天尤人,也沒有賢妻良母那種令人反感的美德。她幾乎什麼都喜歡。倘若你和她在海德公園散步,她會醉心於一叢鬱金香,一會兒對童車裡的一個小孩發生興趣,過一會兒又心血來潮,臨時編造什麼荒唐的戲劇場面。(假如她認為有些戀人不幸福,她很可能去安慰他們呢。)她有一種了不起的喜劇感,而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她把時間都消磨殆盡,午宴、晚宴,舉辦她那些永無休止的宴會,說些莫名其妙的話,或者言不由衷,從而使腦子僵化,喪失分辨能力。她會坐在餐桌的首席,煞費心機應酬一個可能對達洛衛有用的傢伙——他們對歐洲最無聊的瑣事都了如指掌——或者,伊莉莎白走了進來,一切又得圍繞她轉。伊麗莎自在中學念書。上一次彼得到她家去的時候,伊莉莎白還處在不善於辭令的階段。她是個臉色蒼白、眼睛圓圓的姑娘,生性緘默、遲鈍,壓根兒不象她的母親。她認為一切都理所當然,任憑母親小題大做一番,然後問道:“我可以走了嗎?”好象她只是個四歲的孩子呢。克拉麗莎解釋道,伊莉莎白是去打曲棍球的,聲調中混合著愉悅和自豪,這種感情看來是達洛衛本人在她心中激起的。現在伊莉莎白可能已經“進入社交界”,因而把他看作思想守舊的老頭,嘲笑她母親的朋友。唉,這也沒什麼。彼得·沃爾什一手執著帽子,走出攝政公園,心裡想,老年的補償只有一點:雖然內心的熱情依然象往昔一般強烈,但是獲得了——終於獲得了——給生命增添最可貴的情趣的力量——掌握生活經驗的力量,在陽光下慢慢地使生活重現的力量。
這是可怕的自白(他又戴上帽子),可他如今已五十三歲了,幾乎不需要伴侶。生活本身,生活的每一刻,每一滴,此時此地,這一瞬間,在陽光下,在攝政公園內,夠滿意了。實際上,過於滿足了。既然一個人已獲得這種力量,就會可惜人生太短促,難以領略所有的情趣,難以汲取每一滴歡樂、每一層細微的意蘊:兩者都比以往更為充實,更不帶個人情調。他再也不會經受克拉麗莎給他的那種痛苦了。因為,在一段時間裡,連續好幾個小時,(上帝保佑,他可以這樣說而不致被人竊聽!)連續好幾個小時、好幾天,他絲毫沒有想念過戴西吶。
難道這是因為他依然戀著克拉麗莎?他回想起昔日的痛楚、折磨和滿腔的激情。這一回可截然不同,比以前愉快得多。當然,事實上,現在是戴西愛上了他。興許,這一點可以說明,為什麼他在輪船啟航後,竟會覺得一陣奇異的安慰,只想獨自清靜一下,其他什麼也不要,而且,在船艙里看見戴西費心給他準備的小禮物——雪茄菸、筆記本、航海用的小氈毯——他竟會感到厭煩。任何老實人都會說,五十出頭的人不需要伴侶了,他再也不想討好女人,說她們很美了,年過半百的人,只要他們是誠實的,大多會這么說,彼得·沃爾什思量著。
然而,這些令人震驚的感情流露——今天早上猝然流淚,那是什麼緣故呢?克拉麗莎會怎么想呢?敢情認為他是個傻瓜吧,並且不是第一次這么想。這一切歸根結底是由於嫉妒,這種
心理比人類任何一種情感都持久,彼得·沃爾什思忖,手裡握著小刀,手臂伸得筆直。戴西在最近來信中說,她曾去看過奧德少校,他知道她是故意寫上這一筆的,為了要他妒忌,他想像得出她蹙眉寫信時的模樣,她心中捉摸著怎樣才能刺傷他的心。然而,這一切都是枉費心機,他感到怒不可遏!他跑回英國來找律師調停,這一番鬧哄哄的忙亂並非為了娶她,而是為了不讓她嫁給別人。這正是由於妒忌之心在折磨他。當他看到克拉麗莎那么鎮靜、冷淡,那么專心地縫裙子之類的衣服時,也正是妒忌心觸動了他,他意識到,她原來可以讓他不受痛苦,但恰恰是她,使他變成一個哭哭啼啼的老傢伙。不過,他兀自尋思,女人不懂得什麼是激情,想到這裡,他闔上了折刀!女人不理解激情對男人意味著什麼。克拉麗莎委實冷若冰霜。她會坐在沙發上,在他身邊,讓他握著她的手,甚至主動吻一下他的面頰——他走到了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