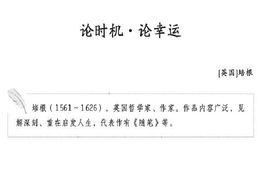內容
幸運之機好比市場,只要錯過機會,價格就將變化,有時它又像那位出賣預言書的西比拉,如果你能買時不及時買,那么當你得知此書重要而想買時,書卻已經不全了。所以古諺說得好,機會老人先給你送上它的頭髮,當你抓不住而再抓時,就只能摸到它的禿頭了。或者說它光給你一個可以抓的瓶頸,你不及時抓住,再得到的就是抓不住的圓瓶身了。
善於在做一件事的開端識別時機,這是一種極難得的智慧。例如在一些危險關頭,總是看來嚇人的危險比真正壓倒人的危險要多許多。只要能挺過最難熬的時機,再來的危險就不那么可怕了。因此,當危險逼近時,善於抓往時機迎頭痛擊它要比猶豫躲閃更有利。因為猶豫的結果恰恰是錯過了克服它的機會。但也要注意警惕那種幻覺,不要以為敵人真像它在日光下陰影那樣高大,因而在時機不到時過早出擊,結果反而失掉了獲勝的機會。
總而言之,善於識別與把握時機是極為重要的。特別對於政治家來說,秘密的策劃與果斷的實行更是保護他的隱身盔甲。因為果斷與迅速乃是最好的保密方法---要像疾掠空中的於彈一樣,當秘密傳開的時候,事情卻已經做成了。
作者介紹
弗蘭西斯·培根(Erancis Bacon)是近代歸納法的創始人,又是給科學研究程式進行邏輯組織化的先驅,所以儘管他的哲學有許多地方欠圓滿,他仍舊占有永久不倒的重要地位。
他是國璽大臣尼可拉斯·培根爵士的兒子,他的姨母就是威廉·西塞爾爵士(SirWilliamCecil)(即後來的柏立勳爵)的夫人;因而他是在國事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培根二十三歲作了下院議員,並且當上艾塞克斯(Essex)的顧問。然而等到艾塞克斯一失寵,他就幫助對艾塞克斯進行起訴。為這件事他一向受人嚴厲非難。例如,里頓·斯揣奇(Lytton Strachey)在他寫的《伊莉莎白與艾塞克斯》(Elizabethand Essex)里,把培根描繪成一個忘恩背義的大惡怪。這十分不公正。他在艾塞克斯忠君期間與他共事,但是在繼續對他忠誠就會構成叛逆的時候拋棄了他;在這點上,並沒有絲毫甚至讓當時
最嚴峻的道德家可以指責的地方。
儘管他背棄了艾塞克斯,當伊莉莎白女王在世期間他總沒有得到十分寵信。不過詹姆士一即位,他的前程便開展了。
1617年培根獲得父親曾任的國璽大臣職位,1618年作了大法官。但是他據有這個顯職僅僅兩年後,就被按接受訴訟人的賄賂起訴。培根承認告發是實,但只聲辯說贈禮絲毫不影響他的判決。關於這點,誰都可以有他個人的意見,因為在另一種情況下他本來要作出什麼判決,不會有證據。他被判處罰金四萬鎊;監禁倫敦塔中,期限隨國王的旨意;終生逐出朝廷,不能任官職。這判決不過執行了極小一部分。並沒有強令他繳付罰款,他在倫敦塔里也只關禁了四天。但是他被迫放棄了官場生活,而以撰寫重要的著作度他的餘年。
在那年代,法律界的道德有些廢弛墮落。幾乎每一個法官都接受饋贈,而且通常雙方的都收。如今我們認為法官受賄是駭人聽聞的事,但是受賄以後再作出對行賄人不利的判決,這更駭人聽聞。然而在那個時代,饋贈是當然的慣例,作法官的憑不受贈禮影響這一點表現“美德”。培根遭罪本是一場黨派爭哄中的風波,並不是因為他格外有罪。他雖不是像他的前輩托馬斯·莫爾爵士那樣一個德操出眾的人,但是他也不特別奸惡。在道德方面,他是一個中常人,和同時代大多數人比起來不優不劣。
培根過了五年退隱生活後,有一次把一隻雞肚裡塞滿雪作冷凍實驗時受了寒,因此死去。
培根的最重要的著作《崇學論》(TheAdvancemento?e Learn-ing)在許多點上帶顯著的近代色彩。一般認為他是“知識就是力量”這句格言的創造者;雖然以前講過同樣話的也許還有人在,他卻從新的著重點來講這格言。培根哲學的全部基礎是實用性的,就是藉助科學發現與發明使人類能制馭自然力量。他主張哲學應當和神學分離,不可像經院哲學那樣與神學緊密糅雜在一起。培根信正統宗教;他並非在此種問題上跟政府鬧爭執的那樣人。但是,他雖然以為理性能夠證明神存在,他把神學中其它一切都看作僅憑啟示認識的。
的確,他倒主張如果在沒有啟示協助的理性看來,某個教理顯得極荒謬,這時候信仰勝利最偉大。然而哲學應當只依靠理性。所以他是理性真理與啟示真理“二重真理”論的擁護者。這種理論在十三世紀時有一些阿威羅伊派人曾經倡說過,但是受到了教會譴責。“信仰勝利”對正統信徒講來是一句危險的箴言。十七世紀晚期,貝勒(Bayle)曾以諷刺口吻使用這箴言,他詳細縷述了理性對某個正統信仰所能講的一切反對話,然後作結論說:“儘管如此仍舊信仰,這信仰勝利越發偉大。”至於培根的正統信仰真誠到什麼程度,那就無從知道了。
歷來有多少哲學家強調演繹的相反一面即歸納的重要性,在這類稟有科學氣質的哲學家漫長的世系中,培根是第一人。培根也如同大多數的後繼者,力圖找出優於所謂“單純枚舉歸納”的某種歸納。單純枚舉歸納可以借一個寓言作實例來說明。昔日有一位戶籍官須記錄下威爾斯某個村莊裡全體戶主的姓名。他詢問的第一個戶主叫威廉·威廉斯;第二個戶主、第三個、第四個……也叫這名字;最後他自己說:
“這可膩了!他們顯然都叫威廉·威廉斯。我來把他們照這登上,休個假。”可是他錯了;單單有一位名字叫約翰·瓊斯的。
這表示假如過於無條件地信賴單純枚舉歸納,可能走上岔路。
培根相信他有方法,能夠把歸納作成一種比這要高明的東西。例如,他希圖發現熱的本質,據他構想(這想法正確)熱是由物體的各個微小部分的快速不規則運動構成的。他的方法是作出各種熱物體的一覽表、各種冷物體的表、以及熱度不定的物體的表。他希望這些表會顯示出某種特性,在熱物體總有,在冷物體總無,而在熱度不定的物體有不定程度的出現。憑這方法,他指望得到初步先具有最低級普遍性的一般法則。由許多這種法則,他希望求出有二級普遍性的法則,等等依此類推。如此提出的法則必須用到新情況下加以檢驗;假如在新情況下也管用,在這個範圍內便得到證實。
某些事例讓我們能夠判定按以前的觀察來講均可能對的兩個理論,所以特別有價值,這種事例稱作“特權”事例。
培根不僅瞧不起演繹推理,也輕視數學,大概以為數學的實驗性差。他對亞里士多德懷著惡毒的敵意,但是給德滿克里特非常高的評價。他雖然不否認自然萬物的歷程顯示出神的意旨,卻反對在實地研究各種現象當中摻雜絲毫目的論解釋。他主張一切事情都必須解釋成由致效因必然產生的結果。
培根對自己的方法的評價是,它告訴我們如何整理科學必須依據的觀察資料。他說,我們既不應該像蜘蛛,從自己肚裡抽絲結網,也不可像螞蟻,單只採集,而必須像蜜蜂一樣,又採集又整理。這話對螞蟻未免欠公平,但是也足以說明培根的意思。
培根哲學中一個最出名的部分就是他列舉出他所謂的“幻象”。他用“幻象”來指讓人陷於謬誤的種種壞心理習慣。
他舉出四種幻象。“種族幻象”是人性當中固有的幻象;他特別提到指望自然現象中有超乎實際可尋的秩序這種習慣。“洞窟幻象”是個別研究者所特有的私人成見。“市場幻象”是關乎語言虐制人心、心意難擺除話語影響的幻象。“劇場幻象”是與公認的思想體系有關係的幻象;在這些思想體系當中,不待說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家的思想體系就成了他的最值得注意的實例。這些都是學者們的錯誤:就是以為某個現成死套(例如三段論法)在研究當中能代替判斷。
儘管培根感興趣的正是科學,儘管他的一般見解也是科學的,他卻忽略了當時科學中大部分正進行的事情。他否定哥白尼學說;只就哥白尼本人講,這還情有可原,因為哥白尼並沒提出多么牢靠的議論。但是克卜勒的《新天文學》(New Astronomy)發表在1609年,克卜勒總該讓培根信服才對。吉爾伯特對磁性的研究是歸納法的光輝範例,培根對他倒讚賞;
然而他似乎根本不知道近代解剖學的先驅維薩留斯(VesalA ius)的成績。出人意料的是,哈維是他的私人醫生,而他對哈維的工作好像也茫然不知。固然哈維在培根死後才公布他的血液循環發現,但是人們總以為培根會知道他的研究活動的。哈維不很高看培根,說“他像個大法官似的寫哲學”。假使培根原來對功名利祿不那么關切,他當然會寫得好一些。
培根的歸納法由於對假說不夠重視,以致帶有缺點。培根希望僅只把觀察資料加以系統整理,正確假說就會顯明畢露,但事實很難如此。一般講,設假說是科學工作中最難的部分,也正是少不得大本領的部分。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出方法,能夠按定規創造假說。通常,有某種的假說是收集事實的必要先決條件,因為在對事實的選擇上,要求有某種方法確定事實是否與題有關。離了這種東西,單只一大堆事實就讓人束手無策。
演繹在科學中起的作用,比培根想的要大。當一個假說必須驗證時,從這假說到某個能由觀察來驗證的結論,往往有一段漫長的演繹程式。這種演繹通常是數理推演,所以在這點上培根低估了數學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單純枚舉歸納問題到今天依舊是懸案。涉及科學研究的細節,培根排斥單純枚舉歸納,這完全正確。因為在處理細節的時候,我們可以假定一般法則,只要認為這種法則妥善,就能夠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多少還比較有力的方法。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設出歸納法四條規範,只要假定因果律成立,四條規範都能用來有效。但是穆勒也得承認,因果律本身又完全在單純枚舉歸納的基礎上才信得過。科學的理論組織化所做到的事情就是把一切下級的歸納歸攏成少數很概括的歸納——也許只有一個。這樣的概括的歸納因為被許多的事例所證實,便認為就它們來講,合當承認單純枚舉歸納。這種事態真不如意到極點,但是無論培根或他的任何後繼者,都沒從這局面中找到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