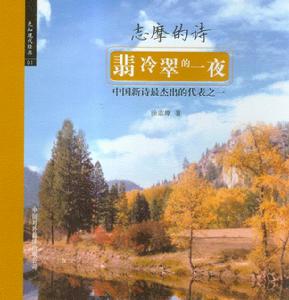作品原文
 徐志摩像
徐志摩像翡冷翠的一夜①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著我,就記著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著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憐憐的在風前抖擻,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乾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著寒傖,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臉,燒得多焦,虧這夜黑
看不見;愛,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別親我了;我受不住這烈火似的活,
這陣子我的靈魂就象是火磚上的
熟鐵,在愛的槌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飛灑……我暈了,抱著我,
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
閉著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頭頂白樹上的風聲,沙沙的,
算是我的喪歌,這一陣清風,
橄欖林里吹來的,帶著石榴花香,
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螢火,
多情的殷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
我到了那三環洞的橋上再停步,
聽你在這兒抱著我半暖的身體,
悲聲的叫我,親我,搖我,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著清風走,
隨他領著我,天堂,地獄,哪兒都成,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
在愛里,這愛中心的死,不強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著……你伴著我死?
什麼,不成雙就不是完全的“愛死”,
要飛升也得兩對翅膀兒打伙,
進了天堂還不一樣的要照顧,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沒有我;
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說地獄不定比這世界文明
(雖則我不信,)象我這嬌嫩的花朵,
難保不再遭風暴,不叫雨打,
那時候我喊你,你也聽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脫反投進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運,笑你懦怯的粗心?
這話也有理,那叫我怎么辦呢?
活著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願你為我犧牲你的前程……
唉!你說還是活著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嗎?——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丟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這是命;
但這花,沒陽光曬,沒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兒焦萎,多可憐!
你不能忘我,愛,除了在你的心裡,
我再沒有命;是,我聽你的話,我等,
等鐵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
愛,你永遠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變一個螢火,
在這園裡,挨著草根,暗沉沉的飛,
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
只願天空不生雲,我望得見天
天上那顆不變的大星,那是你,
但願你為我多放光明,隔著夜,
隔著天,通著戀愛的靈犀一點……
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年翡冷翠山中
作品注釋
①翡冷翠(Firenze,義大利文),現通譯佛羅倫斯,義大利一個城市的名字。
作品鑑賞
詩人或藝術家總是儘量隱蔽情感和思想,不讓它們站出來“直接”說話,而是讓它們隱寓在詩人為其創造的種種意象和設定的層層矛盾中,拐彎抹角、迂迴曲折地“間接”表現出來。在《翡冷翠的一夜》這首詩里,讀者將看到詩人是怎樣“間接地”而不是“直接地”表現抒情主人公——一弱女子錯綜複雜、變幻不定的情感思緒的。
詩一開始就切入抒情主人公的心理活動:“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愛人的行期應該是早已決定了的,對這本沒有什麼可疑問的,但這女子心裡並不願意愛人離她而去,也不相信愛人真的忍心離她而去。這樣,外在的既定事實同女子的內心愿望形成“錯位”,產生了對不是猝然而至的行期卻感到突然的心理反應。“那我,那我,……”這是一句未說完的話,它的意思應是“你走了,那我怎么辦?”但如果這樣說,就缺乏一種詩意,也欠缺含蓄,不能揭示這一弱女子複雜的心理活動。這裡用重複和省略號,很好地傳達出女子喃喃自語、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狀態。“你願意記著我,就記著我,/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有我”這是因留不住愛人而說的“賭氣”話,女子心裡仍在嗔怪愛人,她明知愛人是不可能忘記她的,卻偏這么說,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愛人記住她。但不管怎樣,愛人的即將離別在她心裡投下了沉重的陰影,對“殘紅”這一意象的聯想,反映了她的精神負擔和心理壓力,她對愛人走後自己將獨自面對現實處境而感到焦慮和害怕。她隨即把苦楚的因由轉嫁給愛人:“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愛情讓人幸福,愛情也會讓人苦惱,特別是相愛的人不為社會所理解、不為親朋好友所支持時,更會有苦惱的感受。女子責怪愛人帶給她愛情的苦惱。對愛的表現,詩從開頭到這裡,切入的是愛的“反題”,它不是正面表現愛,而是從愛人的即將遠離在女子心中引起的難過、嗔怒、責怪等情緒反應,反襯出愛人在她生活中的重要以及她對愛人的摯愛和依戀。有了這層鋪墊後,詩便從“反題”轉入“正題”的表現,指出這愛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愛:“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你教給我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愛,/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沒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愛情因溶進了生命、溶進了人的自然情感、溶進了智性和靈性而閃耀著其獨特的光彩。這種愛是讓人難以忘懷的。能夠擁有這種愛是值得自豪、叫人羨慕的。女子的苦惱與自憐被她所擁有的愛的幸福和愛的自豪湮沒了,她再一次沉浸在烈火般的愛情體驗中:“這陣子我的靈魂就象是火磚上的/熟鐵,在愛的槌子下,砸,砸,火花/四散的飛灑……”寫到列這,詩人沒有讓愛的昂奮、情感的高潮繼續持續下去,而是筆鋒一轉,描繪了一幅非常優美的、令人陶醉的“死”的幻象。生與死是具有強烈對照意味的範疇,生意味著“動”,意味著生命;死則意味著“靜”,意味著生命的結束。但生的含義和死的含義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一定的價值坐標上,沒有意義的生不如有意義的死,沒有愛情的生不如為愛情而死,正如這女子所說,在愛中心的死強如五百次的投生。為愛而死,這“死”,實際上是另一層次的“生”,愛情因死而獲得自由、獲得永恆。詩人讓抒情主人公從對愛情的幸福體驗中轉入對死的嚮往,這似乎來得有點突兀,其實並不矛盾,正是對愛情有著深刻的體驗,才萌生了要實現愛情自由和愛情幸福的美好願望,而這種願望既然在現實世界中不能實現,也只能通過死來實現了。然而,如果詩就以弱女子為愛而死、進入到天堂或地獄的冥冥之界中而結束,這在藝術表現上並不能充分展開抒情主人公豐富複雜的內心情感,抒情主人公的精神境界也不能真正得以升華。實際上,詩人為抒情主人公設定了另一層矛盾。這矛盾來自現實世界與非現實世界(天堂或地獄)並不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也許天堂一如人們想像的是個幸福的世界,而“地獄不定比這世界文明”。在現實世界裡,這弱女子有如“殘紅”般“叫人踩,變泥”不被人憐惜反遭摧殘的命運,進了地獄,她也“難保不再遭風暴,不叫雨打”,“那不是求解脫反投進了泥坑”。這就不能不感嘆“活著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的生存處境了。這種矛盾痛苦只有愛才能夠撫平。這個弱女子可以捨棄現實世界,可以捨棄天堂或地獄,但不能沒有愛——人間至真至美的愛情。有的人把生存的精神力量、精神支柱寄托在一個虛幻的世界裡,比如天堂;或寄託給一個虛幻的偶像,比如上帝。但徐志摩筆下的這個弱女子既不把希望寄托在天堂,也不寄託給上帝;如果她心中也有天堂或上帝的話,那么這天堂是有著至真至美的愛的天堂,愛人便是是的上帝。“——你在,就是我的信心”,“愛,除了在你的心裡,我再沒有命”,“愛,你永遠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愛,愛人,是她生活的一切;愛,成為她人生的信仰。因此,即使她不幸死了,也不是飛到天堂或下到地獄,而是要變一個螢火,“在這園裡,挨著草根,暗沉沉的飛”,從“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只因天上有她的愛人——那顆不變的明星。“但願你為我多放光明,隔著夜,/隔著天,通著戀愛的靈犀一點……”抒情主人公錯綜複雜的情感思緒、愛怨交織的心理矛盾,終於在愛的執著與愛的信仰中得到了舒緩和統一,並萌發出美好的願望,閃爍著愛情浪漫而又動人的光彩。徐志摩的這篇《翡冷翠的一夜》是摹擬一個弱女子的口吻寫成的,他用細膩的筆調,寫出依戀、哀怨、感激、自憐、幸福、痛苦、無奈、溫柔、摯愛、執著等種種情致,層層婉轉,層層遞深,真實而感人地傳達出一弱女子在同愛人別離前夕複雜變幻的情感思緒。抒情主人公這種複雜的思緒,也正是詩人當時真實心境的反映。寫作這首詩時,詩人正身處異國他鄉(義大利佛羅倫斯),客居異地的孤寂、對遠方戀人的思念、愛情不為社會所容的痛苦等等,形成他抑鬱的情懷,這種抑鬱的情懷同他一貫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信仰結合起來,便構成了這首詩獨特的意蘊。這首詩不象徐志摩的許多抒情短詩那樣,以高度的藝術凝聚力和藝術表現力顯示其魅力;它是以細膩的筆調,對一種複雜情感思緒的鋪敘,對一種自由流動的心理活動的鋪展,有許多細緻的細節描繪,這在藝術表現上也許會顯得比較錯雜凌亂、紛繁來碎,然而這正吻合了抒情主人公複雜變幻的思緒。
在語言上,這首詩通篇用一種平白的、近乎喃喃自語的口語寫成。口語表達不僅親切真實如在目前,它比書面語更適宜表現“獨語”;當一個人獨自抒遣情懷、傾訴情感時,用口語表達方式(說話間的重複、停頓、省略、感嘆等等)更適宜表現內心情感的變化和自由變幻的心理活動。口語表達自然、生動、貼切、靈活多變,是這首詩的成功所在。
作者簡介
徐志摩(1897~1931)詩人、散文家。名章垿,筆名南湖、雲中鶴等。浙江海寧硤石人。1915年畢業於杭州一中,先後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薰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1921年開始創作新詩。1922年返國徐志摩像後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1923年,參與發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學研究會。1924年與胡適、陳西瀅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任翻譯。1925年赴歐洲、遊歷蘇、德、意、法等國。1926年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詩鐫》,與聞一多、朱湘等人開展新詩格律化運動,影響到新詩藝術的發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教授。1927年參加創辦新月書店。次年《新月》月刊創刊後任主編。並出國遊歷英、美、日、印諸國。1930年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被選為英國詩社社員。同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1931年初,與陳夢家、方瑋德創辦《詩刊》季刊,被推選為筆會中國分會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飛機到北平,因遇霧在濟南附近觸山,機墜身亡。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小說散文集《輪盤》,戲劇《卞崑岡》(與陸小曼合寫),日記《愛眉小札》、《志摩日記》,譯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他的作品已編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像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於變化,並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
創作背景
寫作這首詩時,詩人正身處異國他鄉(義大利佛羅倫斯),客居異地的孤寂、對遠方戀人的思念、愛情不為社會所容的痛苦等等,形成他抑鬱的情懷,這種抑鬱的情懷同他一貫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信仰結合起來,便構成了這首詩獨特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