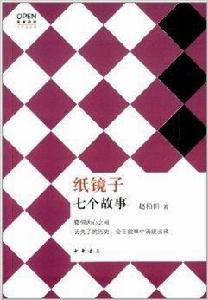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紙鏡子:七個故事》作者趙柏田把這些年陸續寫下的七個歷史短篇小說匯成此書,收入“風度閱讀”出版,重讀這些文字,忽然想起李商隱的一句詩:“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歷史之鏡,它反映著,結束了又開始,而它最為晦暗、堅硬的部分,最強大的理性也無法穿透。在那裡,古老而又日常的生活的每一處肌理,都像是一個精心製造的、虛幻而又深刻的鏡中世界。
作者簡介
趙柏田,小說和隨筆作家。1969年8月出生於浙江餘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作協簽約作家。在各大期刊發表作品200餘萬字,入選多種選刊、選本及年度排行榜,部分作品譯介到國外。曾獲“十月”散文獎、2000年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全國大紅鷹文學獎等。主要作品有《我們居住的年代》、《站在屋頂上吹風》、《歷史碎影:日常視野中的現代知識分子》等。近年致力于思想史及近現代知識分子研究。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趙柏田的寫作呈現出了多元的格局,在他筆下,歷史與當下常有天涯比鄰之感。而且,他創試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把日常化、民間性提上來,以此與大歷史構成對話。
——文學評論家毛尖
趙柏田寫作的特點在於溝通了古今,溝通了文史。我個人感覺是氣息醇正,用心良苦,因為正好與當代知識分子的狀況構成了對照,有一種潛在的對話關係。
——同濟大學教授王鴻生
我感興趣的是趙柏田的敘述姿態。存在著三種敘述姿態,一種是仰視的,是注釋性的;一種是俯視的,肢解性的。趙柏田採用了一種平視的目光穿透歷史,讓作者、人物、讀者在一個平面上互動,形成一個“場”。……以往我們的關注點總落在人物與時代關係上。趙柏田的書寫顛覆了這種觀念。
——浙江文學院院長盛子潮
名人推薦
趙柏田的寫作呈現出了多元的格局,在他筆下,歷史與當下常有天涯比鄰之感。而且,他創試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把日常化、民間性提上來,以此與大歷史構成對話。
——文學評論家 毛尖
趙柏田寫作的特點在於溝通了古今,溝通了文史。我個人感覺是氣息醇正,用心良苦,因為正好與當代知識分子的狀況構成了對照,有一種潛在的對話關係。
——同濟大學教授 王鴻生
我感興趣的是趙柏田的敘述姿態。存在著三種敘述姿態,一種是仰視的,是注釋性的;一種是俯視的,肢解性的。趙柏田採用了一種平視的目光穿透歷史,讓作者、人物、讀者在一個平面上互動,形成一個“場”。……以往我們的關注點總落在人物與時代關係上。趙柏田的書寫顛覆了這種觀念。
——浙江文學院院長 盛子潮
圖書目錄
自序:“鏡子窺伺著我們”
明朝故事
萬鏡樓
三生花草
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
一個雪夜的遭遇
秘密處決
紙鏡子
台灣繁
後記
寒夜,等待著雪的訊息,開窗關窗不知凡幾。雪未至,卻等來了台北的一紙電郵。鄭伊庭先生在郵件中告訴我,“以當代口吻還原歷史現場”的小說《萬鏡樓》已評估完成,年初將由秀威出版。
有一剎那的出神,我還以為這世上另有一個趙柏田,他和我一樣以煮字為生,泅渡著一個個有雪或無雪的夜晚。也或許,我是一個時光旅行者,提前接獲了這封發自未來的信函?
感謝出版人薛原先生和海峽對岸的著名學人蔡登山先生,讓這本小書走到了公眾面前。
即將過去的辛卯年歲末,因網路上流傳的一張造型兇悍的龍年郵票,我正困擾於“歷史性偏頭痛”(羅蘭·巴特語)。倒不是糾結於這幅透出騷動不安氣息的“壬辰龍”外形酷似一八七八年的大清龍票,而是悚然心驚於一百多年過去了,歷史的列車還是在環形車道里打著轉。那病蟲般張牙舞爪的模樣,如同遊蕩不去的民族主義幽魂,還真把我嚇著了。這哪是雍容、自信的“龍”,分明是千百年來一直壓在我們自己身上的那條吸血蟲。
對於以歷史寫作為職志的我和我的同道們來說,把歷史當作一道食糧也罷,一副神聖的毒藥也罷,都意味著,我們是歷史的啖食者,也是見證者和祭獻者。
這些文字,即是前行途中一次小小的獻祭:先是吞噬歷史,然後反芻歷史。
三十年前,當我還是一個懵懂少年穿行在家鄉餘姚城——那是王陽明出生並度過人生初年的小城——的石板弄堂間,我就想著,總有一天我要為陽明先生寫一部書。歷史,過早地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個原核。
過了四十歲,我部分地償還了這個願望。在二○○七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拙著《岩中花樹》中,我這樣說道:“歷史小說——如果有這樣一種文學樣式的話——並不只是小說家用他那個時代的方法去詮釋過去年代的人和事,它更重要的責任,乃在於把握、甚至創造一個內部的世界。”
這種向內的把握和重建,在我還沒有以歷史寫作為職志之前——那時我是正趨向沒落的先鋒小說的一個附驥尾者——就已經在中短篇小說寫作中先驗地坐實,後來的研究和寫作不過是這初聲的一個迴響。
收入本集的七篇小說,七則故事,主人公們從歷史的底部浮上這個喧囂的時代說話:一個追慕畫道的青年在對大師徐渭的尋找中遁形於一幅畫中;一個在夢境和香料中營造精緻生活的明朝作家;一個年代莫辨的復仇故事;一個對《世說新語》經典故事的後現代嘲諷;一場綿延了一個女人一生的秘密處決;一個詩人的前世今生;講故事的人與故事中人在時空的某一個交叉點上邂逅相遇又合二為一……
循著草蛇灰線,其本事或可一一追溯、考據到徐渭、陳獨秀、蘇曼殊、董若雨、王子猷……但讀小說的自由或在於用不著一一拘泥,羚羊掛角,象由心生,他們不過是心靈世界的一個幻象。也正因為此,歷史呈現出了第二個維度,一個由智力活動構成的全景式維度,歷史寫作也從勞役一躍而成為了一場歡慶。
感謝鄭伊庭編輯為此書出版付出的辛勤勞動。感謝最初發表這些作品的編輯同仁們。
趙柏田
2012年1月6日,初雪之日午時於寧波
序言
有一個人終生迷戀著鏡子又害怕鏡子,他說,“鏡子窺伺著我們”——我們打量著它,同時顯現的卻是一張瞧著它又被瞧著的臉。很多年裡,我一直把這個叫博爾赫斯的南美洲作家當作我寫作的導師。歷史之鏡,它反映著,結束了又開始,而它最為晦暗、堅硬的部分,最強大的理性也無法穿透。在那裡,古老而又日常的生活的每一處肌理,都像是一個精心製造的、虛幻而又深刻的鏡中世界。它對我的魅惑有多大,我就和博爾赫斯一樣有多少的怕。
承蒙中華書局徐衛東先生厚愛,把這些年陸續寫下的七個歷史短篇小說匯成《紙鏡子》,收入“風度閱讀”出版,重讀這些文字,忽然想起李商隱的一句詩:“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
星何以沉?原來是夜空幽藍,深邃一如大海。能看作星沉海底,說起來還是心外無物的從容。雨聲如鈸,如鼓,卻是岸上置座,隔著安全的距離靜觀。歷史的天空星沉雨過,那些紛繁的人和事進入眼裡,其搖曳多姿,全在這一“當”、一“隔”的虛與實間了。
紀實與虛構,正是歷史寫作的“任督二脈”,其悠然相會處,正是李義山嚮往中那個叫“碧城”的自由世界:那裡,名和物各歸其位,一塵不染,人和事都有開端,有高潮,也有終結。
然而,歷史經常會丟三落四,會人為塗飾,會虎頭蛇尾,那個“碧城”,如同一場只留下苦澀回憶的晚唐愛情,怎么也找不見的。好在丟失了的歷史,會在小說的織體細節里湧現出來。
——所以虛構就是再現往事,它是我們的第二次機會。
我需要做的,就是始終沉住氣,調整好手中望遠鏡的準確焦距,這樣才能把遠處的東西拉近觀察。
是為序。
趙柏田
2013年3月1日,於浙江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