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猶太文學
美國猶太文學猶太人文學是美國文學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美國猶太作家,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發表小說的美國猶太作家,他們的成就令人矚目,成為讀者和文學批評者關注的一個焦點。他們相繼獲得重要的全國乃至國際大獎。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僅是為某個民族的人民寫作,而是為所有現代人寫作。他們描述了現代狀況下普通人的受難、邊緣狀態、受害、異化和救贖。
文學時期
 《聖經》
《聖經》猶太人文學大致可以分為3個時期。第1期是古代希伯來語時期,大約從公元前12至公元前2世紀,約1,000年間的文學,曾經編訂為猶太教的《聖經》,後來基督教稱為《舊約全書》。在這一時期所用的語言是巴勒斯坦口頭語言,起初稱為“聖經希伯來語”,後來演變為“彌希拿希伯來語”。前者的意思是創作《聖經》作品時期的活希伯來語;後者的意思是解釋《聖經》時期的希伯來語或希伯來法典的語言──書面語言。
第2期是公元200至1880年間的文學。這一時期希伯來語發展成為書面文字或文言文。作者也用其他語種寫作。這時期的希伯來文學中心在地中海地區,繼而轉至西北歐、中歐與東歐,19世紀中葉以後移至美洲。
第3期是1880年以後。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希伯來語恢復為口頭語言,其文學中心逐漸移到巴勒斯坦。
“猶太人文學”和“希伯來文學”不同。希伯來文學是指用希伯來語文寫作的文學,有的出於猶太人之手,有的出於撒馬利亞人的手筆,17世紀時還有基督教徒的作者。猶太人文學不一定用希伯來語文寫作。有些猶太人作家用希臘文、亞蘭文、阿拉伯文、猶太西班牙文和意第緒語(猶太德意志語)以及英、法、德、俄等國語文寫作。
重要地位
 《聖經》
《聖經》美國當代作家中,猶太裔作家占相當大的比重,猶太人文學幾乎可以視為一種“次文化”或“文化支流”。猶太人文學作品一般都具有古老的歐洲文化與現代的美國文化的雙重色彩,兩種文化的衝突與歸併使猶太人文學增加了複雜性。宗教思想與同胞遭到屠殺使猶太作家產生犯罪感與負疚感,歷史的命運又使他們有流浪感與漂泊感,美國的異化社會也使他們感到找不到歸宿。因此,尋找“自我本質”便成為他們的作品中一個突出的主題。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貝洛的《奧吉·瑪琪歷險記》。實際上,這是猶太民族確立自己的民族地位與民族尊嚴的一種表現。70年代後期,代表西方較新思想體系的貝洛與屬於意第緒文化傳統的辛格(1904- )相繼得到諾貝爾獎金,說明猶太人文學在美國文學中的重要性。其他重要的猶太作家還有馬拉默德(1914- )、羅斯(1933- )等。
猶太情結
 凱爾泰斯·伊姆雷
凱爾泰斯·伊姆雷200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以下簡稱諾獎)塵埃落定,73歲的匈牙利老人凱爾泰斯·伊姆雷意外當選,成為又一個以猶太人的身份躋身諾獎行列的作家。這位游離於世界文壇主流視野之外的凱爾泰斯,此前可謂藉藉無名,不僅在各類東歐當代文學史中難覓其跡,甚至在獲獎之後各國媒體對於他的稱呼都存在差異,譬如中文媒體中就有克特斯、凱爾泰斯、凱爾泰茲、凱爾特斯等多種譯法。當文學界人士著力為這位無名小卒何以在與米蘭·昆德拉、托馬斯·品欽、略薩等文壇大腕的競爭中勝出尋找理由時,也許注意到了作者的猶太人身份。
第十一位猶太人獲獎者
猶太人的標籤不比諾獎的桂冠般能夠帶來美金和聲望,更多的時候,它與苦難、流浪、屠殺聯繫在一起。凱爾泰斯·伊姆雷的遭遇便是最好的註腳。1929年他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猶太家庭,少年時即因為猶太出身而被關入奧森維辛集中營,直至二戰結束。1950年起,他長住布達佩斯,從事寫作和翻譯,少年時集中營的悲慘生活是其小說創作的主題。
獲獎後的凱爾泰斯寧願反覆強調這是世界對匈牙利文學的肯定,並不願太多提及自己的猶太裔身份。2001年,他在接受西班牙一家日報採訪時,有過對自己猶太身份的矛盾心態的表述:“我生活在一個有著強烈反猶思想的社會裡,我常常覺得,我是被迫成為猶太人的。我是猶太人,我接受這一點,但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這一身份的確是強加在我身上的。”
然而諾獎似乎對猶太裔作者厚愛有加。自1901年始,諾貝爾文學獎已走過百餘年的歷史,其間因為戰爭緣故,有7年停發,又曾經有4年將獎項同時頒給兩位作家。截止2002年,共有99位作家榜上有名,而猶太裔作家就有11位。1966年更是諾獎歷史上的“猶太年”,竟然破天荒地將獎項同時頒給了兩位猶太裔作家約瑟夫·阿格農和奈莉·薩克斯。
考慮到猶太民族最高峰時也僅占世界總人口四百分之一的1600萬人口數,以及西方世界從政治到文化領域內根深蒂固的排猶主義情緒,這10%的比例足以令人吃驚和深思。可以說,百餘年的諾獎歷史已不自覺地培育出了一種“猶太情結”,也儼然成為了一種內涵豐富、機理複雜的文化現象。
究竟猶太裔作家有著什麼樣的精神特質和文化底蘊,使得諾獎如此垂青?這是在回顧諾獎歷史時無法迴避的問題。
流浪者對於西方文化的認同
諾貝爾文學獎的初衷是“獎給那些在文學領域裡創作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優秀的作品的人”,但不能否認的是,諾獎在民族土壤、評選標準、文化價值取向上具有明顯的西方文化色彩。在業已獲獎的99位作家中,80%強來自西方國家,而即便是為數甚少的幾位東方獲獎者,也不是以特有的東方文化色彩取勝,相反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吸取了西方的文化營養。最典型的是1913年獲獎的印度作家泰戈爾,幼時即在英國接受西方教育,諾獎授獎辭稱他“運用完美的技巧,運用自己的英語辭彙,使他詩意盎然的思想成為西方文學的組成部分。”這可以視作諾獎評審們對於東方文學的絕妙諷刺。其他諸如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還有非洲奈及利亞的索因卡,均在自己本土特色的創作中吸取了大量的西方文學價值觀和寫作技巧。可以這么說,百年的諾獎歷史中,完全不具西方文學背景的作家作品,幾無獲獎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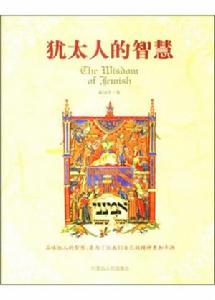 猶太人的智慧
猶太人的智慧因此,在探討猶太作家為何屢屢問鼎諾貝爾文學獎時,幾乎可以斷言他們必定對異質的西方文化進行了特殊的溝通,從而獲得認同。業已獲獎的11位猶太作家,就出身和教育背景看,均屬於猶太第二代或第三代,在西方文化氛圍中長大,受西方文明耳濡目染。即便後來回歸以色列故土的阿格農,也是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波蘭出生並長大,他的作品譬如《婚禮的華蓋》、《阿古諾》等公認為具有鮮明的德語文化特色。
歐洲文明的兩個源頭,一為希伯萊文化,一為希臘文化。希伯萊文化便是猶太作家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傳統,這意味著西方文明在本質核心上存在著猶太作家介入和吸收的可能,而兩千多年來猶太民族坎坷多舛的異地生存境遇更是把這種可能性推向了作家主體的自覺需要。
猶太人視自己為“上帝的特選子民”,但特選子民獲得的卻是特別的苦難。從公元前6世紀的“巴比倫之囚”一直到奧森維辛的屠殺,歷經兩千多年的顛沛流離,猶太人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尤以歐美為甚,單現在的紐約一處,就聚集達800萬之眾。生活在異邦的猶太人在文化取向上被迫面臨著“上樹和下地”的兩種抉擇:一部分猶太人潛移默化地被居住地文明所同化,既而淪為“沒有猶太性的猶太人”;而另外一部分則在吸收異質文化的同時頑強地保持著猶太文明的特性,學會了“在猶太性中解放自己”,成為所謂的“沒有國籍的猶太人”。
1981年獲獎的卡奈第,其祖父是西班牙猶太人,他本人更是在保加利亞、奧地利輾轉,二戰期間逃亡法國,最後才定居英國倫敦,外界稱其為“英國作家”、“奧地利作家”、“德語作家”,但他自己清醒地稱自己為一個猶太人。而2002年獲獎的凱爾泰斯,卻擺出一副極不情願的姿態,聲稱猶太身份是強加於自己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反映了猶太裔作家在認同西方文化過程中對於自身多重身份的困惑和焦慮。
這種身份和文化上的多重性和模糊性,使得其與西方文明之間達成了特定的溝通和契合機制,他們在作品中廣泛借鑑來自於西方的文學敘述與技巧、甚至包括生活內容和思想觀念,為入選諾獎掃除了文化差異上的障礙。這種對於西方文化的認同最直接、最典型的體現當是他們創作語言的選擇。11獲獎位作家中,戈迪墨用英語寫作,伯格森用法語,帕斯捷爾納克用俄語,薩克斯用德語,僅有的兩位:辛格和阿格意欲使用本土語言,但最終所用的意第緒語也還是一種特殊的希伯來語、德語、斯拉夫語的雜交體,遠非純粹的猶太民族語言了。創作語言與西方的同質化不但奠定了他們為西方所接受的形式基礎,更重要的是在潛移默化的西方語言使用中培養了多重的思想方法,當然多半還是符合西方的思維邏輯。
猶太式命題的標本意義
為西方文化所認同,僅為猶太作家進入諾獎視野提供了可能性,但不足以解釋他們緣何在與眾多西方本土作家的競爭中勝出。這牽涉到猶太民族的族性問題。猶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不擅長遺忘和執著的民族,幾千年來身處異質文化的衝突中卻還能保持猶太族性,實屬不易。他們相信只會被認同,但不會被同化。
綜觀各位猶太獲獎作家,不難發現,他們無不在認同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各種方式對悠遠獨特的猶太文化資源進行整合或消解,從而賦予個人創作或鮮明或隱晦的猶太文化色彩,使得諾獎評審感到了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品性。這種窘異的新鮮感使得他們的作品別有風味。他們懂得專注於挖掘猶太文化中獨有的資源,將其與人類的恆定普遍的命題相結合,從而獲得超越猶太文化自身而放之世界皆宜的參照意義。
這其中包含兩種具體的操作方式:“一顯一隱”,或“一明一暗”。
或在作品中暗含猶太因素,使其符號化、意象化,消解為文學作品中的內在構因。譬如1969年的獲獎者貝克特,其代表作《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漢無助而絕望的等待正寓意著幾千年來猶太民族對於救世主彌賽亞的等待狀態;1981年的獲獎者卡內蒂喜好以冷峻的態度表現精神與現實的衝突中無足輕重的“邊緣人物”,如異鄉客、怪人以及精神反常的各種小人物,而兩千年來猶太人正是扮演著這種尷尬的“邊緣人”角色。
或直接以猶太生活為描述中心,從中進行反思,體現對於全人類的哲學關懷,譬如1978年獲獎的辛格,其長篇小說《莫斯卡特一家》、《莊園》等就是描述在現代文明和排猶主義雙重壓力下,波蘭猶太社會的解體過程;更具代表性的則是作家們對於猶太大屠殺和集中營題材的偏愛:1966年同時獲獎的薩克斯和阿格農,前者致力於對殺戮和被殺戮、追逐和逃亡、暴力和死亡的關係的探討,後者更因為善於從猶太民族生命中吸取主題而被瑞典學院譽為“現代希伯來文學的首要作家”2002年獲獎的凱爾泰斯亦不例外,他自己常說“一提起文學創作,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悲慘生活。”
 猶太名人
猶太名人難能可貴的是,猶太作家在將猶太命題標本化的同時,並沒有囿於民族情緒的表達,而是上升為對於人類命運的關注,正如諾獎在對辛格授獎辭中所講的“將人類普遍的處境逼真地反映出來了。”綜上所述,猶太裔作家以其特殊的文化優勢,創造了百年諾獎歷史上的“猶太現象”:流浪者的角色和現實的困境,使得他們以實用為原則,有目的、有過濾地整合或揚棄西方的異質文明;同時亦清醒地堅守著自我的猶太民族特性,保留著鮮活的猶太記憶,並以西化的方式將其消融進文本中,從而使得作品既具有世界性,又不失民族性,最終在二者的互相滲透中征服諾獎評審。民族的苦難,在幾千年後以另類的方式被後人所傳承。而所有這些貌似平常的經驗也好,教訓也好,都應當為屢被諾獎排斥的中國作家記取。
獲獎的11位猶太作家分別是:1927年的亨利·伯格森(法國)、1966年的阿格農(以色列)、1958年的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蘇聯)、1966年的奈莉·薩克斯(德國)、1969年的薩繆爾·貝克特(法國)、1976年的索爾·貝婁(美國)、1978年的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美國)、1981年的埃利亞斯·卡內蒂(英國)、1987年的約瑟夫·布羅茨基(美國)、1991年的內丁·戈迪默(南非)、2002年的凱爾泰斯·伊姆雷(匈牙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