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結構
 朗香教堂的彎曲造型
朗香教堂的彎曲造型在朗香教堂的設計中,勒·柯布西耶把重點放在建築造型上和建築形體給人的感受上。他摒棄了傳統教堂的模式和現代建築的一般手法,把它當作一件混凝土雕塑作品加以塑造。
教堂造型奇異,平面不規則;牆體幾乎全是彎曲的,有的還傾斜;塔樓式的祈禱室的外形像座糧倉;沉重的屋頂向上翻卷著,它與牆體之間留有一條40厘米高的帶形空隙;粗糙的白色牆面上開著大大小小的方形或矩形的窗洞,上面嵌著彩色玻璃;入口在捲曲牆面與塔樓的交接的夾縫處;室內主要空間也不規則,牆面呈弧線形,光線透過屋頂與牆面之間的縫隙和鑲著彩色玻璃的大大小小的窗洞投射下來,使室內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氣氛。
設計構思
 朗香教堂奇特設計
朗香教堂奇特設計勒氏生前曾說了不少和寫了不少關於朗香教堂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是還不夠。應該承認,有時候創作者本人也不一定能把自己的創作過程講得十分清楚。有一次,那是朗香建成好幾年以後的事,勒柯布西耶自己又去到那裡,他還很感嘆地問自己:“可是,我是從哪兒想出這一切來的呢?”勒氏大概不是故弄虛玄,也不是賣關子。藝術創作至今仍是難以說清的問題。需要深入細緻的科學研究。勒氏死後,留下大量的筆記本、速寫本、草圖、隨意勾畫和注寫的紙片,他平素收集的剪報、來往信函,等等。這些東西由幾個學術機構保管起來,勒柯布西耶基金會收藏最集中。一些學者在那些地方進行多年的整理、發掘和細緻的研究,陸續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報告。一些曾經為勒氏工作的人也寫了不少回憶文章。各種材料加在一起,使我們今天對於朗香教堂的構思過程有了稍為清楚一點的了解。勒·柯布西耶關於自己的一般創作方法有下面一段敘述:“一項任務定下來,我的習慣是把它存在腦子裡,幾個月一筆也不畫。人的大腦有獨立性,那是一個匣子,盡可往裡面大量存入同問題有關的資料信息,讓其在裡面遊動,煨煮、發酵。然後,到某一天,喀噠一下,內在的自然創造過程完成。你抓過一隻鉛筆,一根炭條,一些色筆(顏色很關鍵),在紙上畫來畫去,想法出來了。” 這段話講的是動筆之前,要作許多準備工作,要在腦子中醞釀。
設計過程
創作思想和立意的形成
在創作朗香時,在動筆之前勒氏同教會人員談過話,深入了解天主教的儀式和活動,了解信徒到該地朝山進香的歷史傳統,探討關於宗教藝術的方方面面。勒氏專門找來介紹朗香地方的書籍,仔細閱讀,並且作了摘記。大量的信息輸進腦海。
 朗香教堂
朗香教堂過了一段時間,勒氏第一次去到布勒芒山(Hill of Bourlemont)現場時,他已經形成某種想法了。勒氏說他要把朗香教堂搞成一個“視覺領域的聽覺器件”(acoustic component in the domain of form),它應該像(人的)聽覺器官一樣的柔軟、微妙、精確和不容改變”(《勒柯布西耶全集1946—52》P.88)第一次到現場時,勒氏也在山頭上畫了些極簡單的速寫,記下他對那個場所的認識。他寫下了這樣的詞句:“朗香與場所連成一氣,置身於場所之中。對場所的修辭,對場所說話。”
在另一場合,他解釋說:“在小山頭上,我仔細畫下四個方向的天際線,……用建築激發音響效果——形式領域的聲學”。把教堂建築視作聲學器件,使之與所在場所溝通。進一步說,信徒來教堂是為了與上帝溝通,聲學器件也象徵人與上帝聲息相通的渠道。這可以說是勒氏設計朗香教堂的建築立意,一個別開生面的巧妙的立意。
方案的設計和改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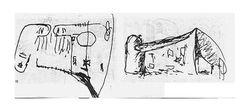 朗香教堂設計草圖
朗香教堂設計草圖從1950年5月到11月是形成具體方案的第一階段。現在發現的最早的一張草圖作於1950年6月6日,畫有兩條向外張開凹曲線,一條朝南像是接納信徒,教堂大門即在這一面,另一條朝東,面對在空場上參加露天儀式的信眾。北面和西面兩條直線,與曲線圍合成教堂的內部空間。
另一幅畫在速寫本上的草圖顯示兩樣東西。一是東立面。上面有鼓鼓地挑出的屋檐,檐下是露天儀式中唱詩班的位置,右面有一根柱子,柱子上有神父的講經台。這個東立面布置得如同露天劇場的台口。朗香教堂最重大的宗教活動是一年兩次信徒進山朝拜聖母像的傳統活動,人數過萬,宗教儀式和中世紀傳下來的宗教劇演出就在東面露天進行。草圖只有寥寥數筆,但已給出了教堂東立面的基本形象。這一幅草圖上另畫著一個上圓下方的窗子形象,大概是想到教堂塔頂可能的窗形。此後,其他一些草圖進一步明確教堂的平面形狀,北、西兩道直牆的端頭分別向內卷進,形成三個半分隔的小禱告室,它們的上部突出屋頂,成為朗香教堂的三個高塔。有一張草圖勾出教堂東、南兩面的透視效果。整個教堂的體形漸漸周全了。然後把初步方案圖送給天主教宗教藝術事務委員會審查。
委員會只提了些有關細節的意見。1951年1月開始,進入推敲和確定方案的階段,工作在勒氏事務所人員協助下進行。這時做了模型——為推敲設計而做的模型,一個是石膏模型,另一個用鐵絲和紙紮成。對教堂規模尺寸做了壓縮調整。勒氏說要把建築上的線條做得具有張力感,“像琴弦一樣!”整個體形空間愈加緊湊有勁。把建成的實物同早先的草圖相比,確實越改越好了。
設計解讀
有關靈感
 朗香教堂
朗香教堂讓我們回到勒氏自己提的問題:他是從哪兒想出這一切來的呢?這個問題也正是我們極為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夢裡所見的嗎是靈機一動,無中生有出現的嗎?在世界建築史上,基督教教堂何止千萬,著名傑作也不在少數,何以這個山中的小小教堂竟如此引人注目,令許多人讚賞不迭,連與基督教絲毫沾不上邊的人都為之心折,這是什麼原故呢? 再說,勒柯布西耶是大家知道的現代主義建築的旗手,當年他大聲號召建築師向工程師學習,要從汽車、輪船、飛機的設計製造中獲取啟示。他的名言:“房屋是居住的機器”言猶在耳,人們記得他是很主張理性的。那么,這么一位建築師怎么又創作出朗香這樣怪裡怪氣的建築來了呢?
難道我們可以說朗香教堂還是理性的產物么?如果不是,那又是什麼呢?是什麼樣的背景和思想促成了那個朗香教堂?大家都說建築創作要有靈感,勒柯布西耶創作朗香時從那兒來的靈感呢? D·保利先生經過多年的研究,認為勒氏是有靈感的建築師,但靈感不是憑空而來,它們也有來源,朗香教堂形像的源泉就是勒氏畢生不懈、廣泛收集、儲存在腦海中的巨量資料信息。
但畢竟朗香教堂誕生至今已經過去了37年,37年在建築通史書上不算長,在當代建築史上又不算太短。許多建築物和世間許多事物一樣,距離太近不容易看得清楚,不容易評論恰當。間隔一段時間倒好一點。朗香落成37年,勒氏過世27年。現在更多的資料、文獻、手跡、檔案被收集,被整理、被研究了;研究者們發表了許多研究報告,幫助我們了解得多一些,使我們可以再作一番思考。看法自然仍是此時此地的一孔之見。
有關形像和觀感
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不管你信教還是不信教,也不論你見到了實物還是只看到照片或影片,朗香教堂的形象都會令你產生強烈的、深刻的、從而是難忘的印象。在這裡,教堂的規模、技術和經濟問題,以及作為一個宗教設施它合用到什麼程度等等都不重要,也與我們無關。在這裡,重要的是建築造型的視覺效果和審美價值。
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平日我們看到許多建築物,有的眼睛一掃而過,留不下什麼印象,有的眼睛會多停留一會兒,留下多一點的印象。差別就在於有的建築能“抓人”,有的“抓不住”人。朗香教堂屬於能抓人的建築,而且特別能抓。為什麼呢?
這首先是由於它讓人感到陌生,有陌生感或陌生性。我們從日常生活中都形成了一定的關於房屋是什麼樣子的概念。如果直接或間接見到過一些基督教堂的人,心目中又形成基督教堂大致是什麼樣子的概念。我們觀看一座建築物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將眼前所見同已有的概念作比較。如果一致,就一帶而過,不再注意,如果發現有差異,就要檢驗、鑑別,注意力被調動起來了。與以往習見的同類事物有差異,就引起陌生感。
朗香教堂像人們習見的房屋嗎?不像。像人們見過的那些基督教堂嗎?也不像。它太“離譜”了,因此反倒引人注意。
本世紀初,俄國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學派”對文學作品中的“陌生化”做過專門研究。他們說,文學的語言、詩的語言同普通語言相比,不僅製造陌生感,而且本身就是陌生的。詩歌的目的就是要顛倒習慣化的過程,使我們已經習慣的東西“陌生化”,“創造性地損壞”習以為常的東西、標準的東西,以便“把一種新的、童稚的、生氣盎然的前景灌輸給我們”。又說陌生化的文學語言“把我們從語言對我們的感覺產生的效力中解脫出來”,詩歌就是對普通語言的破壞,是“對普通語言‘有組織”的侵害”。(見特·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P61,70)
從文學中觀察到的這些原理,我想在建築和其他造型藝術門類中也大體適用。陌生化是對約定俗成的突破或超越。當然,陌生化是相對的。百分之百的陌生化,全然擺脫人們熟知的形象,會使作品完全變成另外一種東西,也就達不到預期的效果。陌生化有一個程度適當的問題。
勒氏在朗香教堂的形象處理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陌生化”的效果。它同建築史書上著名的宗教建築都不一樣,人們的眼光不能對之漠然。同時,朗香的形象也還有熟悉的地方。那屋頂仍在通常放屋頂的地方;門和窗儘管不一般,但仍然叫人大體猜得出是門和窗。它們是陌生化的屋頂和門窗。正在所謂的似與不似之間。最大限度然而又是適當的陌生化的處理,是朗香教堂一下子把人吸引住的第一關鍵。
 朗香教堂四面
朗香教堂四面朗香教堂的引人之處又在於它有一個非常複雜的形象結構。本世紀初期,勒柯布西耶和他的現代主義同道們提倡建築形象的簡化、淨化。勒氏本人在建築圈內與美術界的立體主義派呼應,大聲讚美方塊、圓形、矩形、圓錐體、球體等簡單幾何形體的審美價值。20年代和稍後一段時期,勒氏設計的房屋即使內部相當複雜,其外形也總是處理得光光淨淨、簡簡單單。薩伏伊別墅即是一例,人們很難找出一個比它更簡單光溜的建築名作了。然而,在朗香,勒氏放棄了往日的追求,走向簡化的反面——複雜。試看朗香教堂的立面處理,那么一點的小教堂,四個立面竟然那樣各個不同,你初次看它如果單看一面,絕想不出其他三面是什麼模樣,看了兩面 ,也還是想像不出第三面第四面的長相,四個立面,各有千秋,真是極盡變化之能事,與薩伏伊別墅幾乎不可同日而語。再看那些窗洞形式,也是不怕變化,只怕單一。再看教堂的平面,那些曲里拐彎的牆線,和由它們組成的室內空間,也都複雜多變到家了。當年勒氏很重視設計中的控制線和法線的妙用,現在都甩開了,平面構圖上找不出什麼規律,立面上也看不出什麼章法。如果一定說有規律,那也是太複雜的規律。薩伏伊別墅讓人想到古典力學,想到歐幾里得幾何學,朗香教堂則使人想到近代力學,非歐幾何。總之,就複雜性而言,昔非今比。
然而有一點要指出的,也是朗香的好處:它的複雜性與中世紀哥德式教堂不同。哥德式的複雜在細部,那細部處理達到了繁瑣的程度,而總體布局結構倒是簡單的,類同的,容易查清的。朗香的複雜性相反,是結構性的複雜,而其細部,無論是牆面還是屋檐,外觀還是內里,其實仍然相當簡潔。
社會審美心理
 朗香教堂
朗香教堂朗香教堂有一個複雜結構,而複雜結構比之簡單結構更符合現在人們的審美心理。如果說薩伏依別墅當初是新穎的,有人喝彩的,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當年也是新穎的,有人叫好的,那么,今天再拿出類似的貨色,絕對不會受到廣泛的歡迎。簡單整齊的東西,舉一可以反三,容易讓人明白的東西,現在被看成白開水一杯,失去了吸引力。簡單和少聯繫在一起,密斯堅持到底,也就栽在這裡。不是嗎,文丘里一句“少不是多”,又一句“少是枯燥”,就把密斯給否了。語云“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代人喜歡複雜的東西,揆之時下的服裝潮流,即可證明。這是就社會審美心態的變遷而言。格式塔心理學家在學理上也有解釋。他們研究證明,格式塔即圖形有簡單和複雜之分。人對簡單格式塔的知覺和組織比較容易,從而不費力地得到輕鬆、舒適之感,但這種感覺也就比較淺淡。視知覺對複雜的格式塔的感知和組織比較困難,它們喚起一種緊張感,需要進行積極的知覺活動。可是一旦完成之後,緊張感消失,人會得到更多的審美滿足。所以簡單格式塔平淡如水,複雜格式塔濃釅如茶如酒。付出的多,收穫也大。朗香教堂的複雜形象就有這樣的效果。
對於朗香教堂的形象,人們觀感不一。概括起來,認為它優美、秀雅、高貴、典雅、崇高的人很少,說它怪誕的最多。晚近的美學家認為怪誕也是美學的範疇之一。朗香教堂可以歸入怪誕這一範疇。上面說了陌生感和複雜性,似乎就包含了怪誕,不必再單說。可是三者既有聯繫,又互相區別。譬如看人,陌生者和性格經歷複雜之人並不一定怪誕,怪誕另有一功。
怪誕就是反常、超越常規、超越常理,以至超越理性。對於朗香教堂,用建築的常理常規,無論是結構學、構造學、功能需要、經濟道理、建築藝術的一般規律等等,都說不清楚。我們面對那造型、那模樣,一種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感想立即油然而生。為什麼?就是面前那個建築形象太怪誕了。
朗香教堂的怪誕同它那原始風貌有關。它興建於1950—55年間,正值20世紀的半中間,可是除了那個金屬門扇外,幾乎再沒有什麼現代文明的痕跡了。那粗糲敦實的體塊、混沌的形象,岩石般穩重地屹立在群山間的一個小山包上。“水令人遠,石令人古”,它不但超越現代建築史、近代建築史,而且超越文藝復興和中世紀建築史,似乎比古羅馬和古希臘建築還早,……它很像原始社會巨石建築的一種,“白雲千載空悠悠”。朗香教堂不僅是“凝固的音樂”,甚且是“凝固的時間”永恆的符號時間。時間都被它打亂了,這個怪誕的建築物!
由此又生出神秘性。朗香教堂那沉重的體塊的複雜組合裡面似乎蘊藏著一些奇怪的力。它們互相拉扯,互相頂撐,互相叫勁。力要進發,又沒有迸發出來,正在掙扎,正在扭曲,正在痙攣。引而不發,讓人揪心。
這些都不易理解,甚至不可理解。誰造出來這樣的建築?明明是勒柯布西耶,可是又不像人造的,完全不像20世紀文明昌盛國度里的人造的。他是不是超人?或者他是按超人的啟示造出來的吧?超人是誰?當然是上帝了。在這樣的教堂里向上帝祈禱,多么好啊! 這都是猜測、是揣摸、是冥想,無法確定。許多建築物,也許是大多數建築物,即使單從外觀上看,也能大體上看出它們的性質和大致的用途,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大廈、各處的飯店、商場、車站、住宅……,都比較清楚。另外一些建築物就不那么清楚了,如巴黎蓬皮杜中心,悉尼歌劇院等等,需要揣測,可以有多種聯想。因為它們在我們心中引出的意象是不明確的,有多義性,不同的觀看者可以有不同的聯想。同一個觀看者也會產生多個聯想,覺得它既像這,又像那,有多義性、多義性帶來不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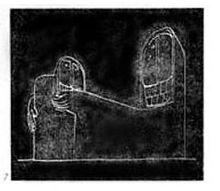 五種聯想
五種聯想朗香教堂的形象就是這樣的,有位先生曾用簡圖顯示朗香教堂可能引起的五種聯想,或者稱作五種隱喻,它們是合攏的雙手、浮水的鴨子、一艘航空母艦、一種修女的帽子,最後是攀肩並立的兩個修士。 (見Jencks,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1977,Rizzoli,P49)。V·斯卡里教授又說朗香教堂能讓人聯想起一隻大鐘、一架起飛中的飛機、義大利撤丁島上某個聖所、一個飛機機翼覆蓋的洞穴,它插在地里,指向天空,實體在崩裂、在飛升……(Le Corbusier,1987,Princeton,NJ,P.53)。一座小教堂的形象能引出這么多(或更多)的聯想,太妙了。而這些聯想、意象、隱喻沒有一個是清楚肯定的,它們在人的腦海中模模糊糊,閃爍不定,還會合併、疊加、轉化。所以我們在審視朗香教堂時,會覺得它難於分析,無從追究,沒法用清晰的語言表達我們心中的複雜體驗。“剪不斷、理還亂”,真的“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而這不是缺點,不是缺陷。朗香教堂與別的一看就明白的建築物的區別正如詩與陳述文的區別一樣。寫陳述文用邏輯性推理的語言,每個詞都有確切的含義,語法結構嚴謹規範。而詩的語法結構是不嚴謹的,不規範的,語義是模糊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秋水清無力,寒山暮多思。”能用邏輯推理去分析嗎,能在腦海中固定出一個確定的意象嗎?相對於日常理性的模糊不定、多義含混更符合某些時候某些情景下人心理上的複雜體驗,更能觸動許多人的內心世界。詩無達詁,正因為這樣反倒有更大的感染力。
兩千多年前傳下來的中國古籍《老子》(第二十一章)中有這樣的話: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朗香教堂一角
朗香教堂一角這些話不是專門針對美學問題,然而接觸到藝術世界和人的審美經驗中的特殊體驗。在藝術和審美活動中,人們能夠在介乎實在與非實在、具象與非具象、確定與非確定的形象中得到超越日常感知活動的“恍惚”,並且感受到“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可以說朗香教堂作為一個藝術形象,正是一種恍惚之象,它體現的是一種恍惚之美。20世紀中期的一個建築作品越出歐洲古典美學的軌道而同中國古老的美學精神合拍,真是值得探討的有意思的現象。總之,陌生、驚奇感、突兀感、困惑感、複雜、怪誕、奇崛、神秘、朦朧、恍惚、剪不亂、理還亂、變化多端、起伏跨度很大的藝術形象,其中也包括建築形象,在今天更能引人駐目,令人思索,耐人尋味,予人刺激和觸發人的複雜心理體驗。因為當代有更多的、愈來愈多的人具有這樣的審美心境和審美要求。朗香教堂滿足這樣的審美期望,於是在這一部分人中就被視為有深度、有力度、有廣度,有烈度,從而被看作最有深意,最有魅力的少數建築藝術作品之一。
朗香教堂屬於建築中的詩品,而且屬於朦朧詩派。
設計者簡介
 設計者勒·柯布西耶
設計者勒·柯布西耶出生於瑞士的勒·柯布西耶是現代建築里程碑式的人物,其設計作品顯示了同時代的繪畫與雕塑到建築的概念轉換,在其努力變革並逃離歷史風格束縛的過程中,建築和其他視覺藝術共享了進入抽像的旅程。朗香教堂是勒·柯布西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要作品,代表了勒·柯布西耶創作風格的轉變,在朗香教堂的設計中,勒·柯布西耶脫離了理性主義,轉到了浪漫主義和神秘主義。
![朗香教堂[法國索恩地區宗教教堂] 朗香教堂[法國索恩地區宗教教堂]](/img/2/f2a/nBnauM3XzEDN0cDM3MT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zUzL0g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