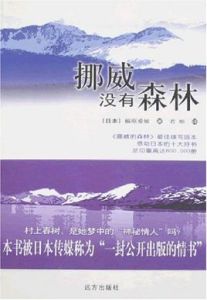本書簡介
在日本,這本書被評論界稱為“一封公開發表的情書”,是福原愛姬寫給比她年長很多的村上春樹的一封情書。在作者的個人網站,她將村上春樹稱為自己的“神秘情人”。她說,《挪威沒有森林》寫的是自己的內心獨白和真實體驗。沒有人知道她和村上春樹到底是怎樣的愛戀故事,也許讀過這本書的人會知道,這是一場淒絕的愛情悲劇。
早在1999年,日本網路上就流傳這本書,並創下當時3000000的點擊率,為什麼有如此的熱潮,我們想一是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有著四百萬冊銷量的影響力,二是本書在寫作上延續了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的故事情節,輕描淡寫的日常生活:憂傷、纏綿、感傷、彷徨、恐懼、迷惑,像古老的咒語一樣纏繞,一群深陷森林的年輕人看到黝黑茂密的森林裡荊棘密布,藤蔓橫生懸掛,濃霧瀰漫,陽光在頭頂若有若無忽隱忽現,渡邊在這樣的生活里遊蕩和行走,他對直子的死耿耿於懷,而綠子在一次與大海搏浪中消失,紀香的表弟小野因同性戀自殺,玲子再次住進精神醫院……使他看到了自己遠去的身影在他們中間,陌生而又熟悉,那不知所措,仍在掙扎著……
本書以一種對話方式進行敘述,看似渡邊自言自語,其實是渡邊在追憶自己當年的青春歲月,它的鋪排和簡練,舒緩和節制,讓人在一種奇妙的絮叨之中,看到冷靜和隨意,這完全由內心意識流動而展開的內心獨語,它造成的距離並沒有讓讀者疏遠,反而讓節奏變得舒緩和沉穩,帶著讀者的靈魂慢慢下沉,並完全被渡邊的情緒和故事所淹沒。在日本,這本書被評論界稱為“一封公開發表的情書”,是福原愛姬寫給比她年長很多的村上春樹的一封情書。在作者的個人網站,她將村上春樹稱為自己的“神秘情人”。她說,《挪威沒有森林》寫的是自己的內心獨白和真實體驗。沒有人知道她和村上春樹到底是怎樣的愛戀故事,也許讀過這本書的人會知道,這是一場淒絕的愛情悲劇。
早在1999年,日本網路上就流傳這本書,並創下當時3000000的點擊率,為什麼有如此的熱潮,我們想一是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有著四百萬冊銷量的影響力,二是本書在寫作上延續了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的故事情節,輕描淡寫的日常生活:憂傷、纏綿、感傷、彷徨、恐懼、迷惑,像古老的咒語一樣纏繞,一群深陷森林的年輕人看到黝黑茂密的森林裡荊棘密布,藤蔓橫生懸掛,濃霧瀰漫,陽光在頭頂若有若無忽隱忽現,渡邊在這樣的生活里遊蕩和行走,他對直子的死耿耿於懷,而綠子在一次與大海搏浪中消失,紀香的表弟小野因同性戀自殺,玲子再次住進精神醫院……使他看到了自己遠去的身影在他們中間,陌生而又熟悉,那不知所措,仍在掙扎著……
本書以一種對話方式進行敘述,看似渡邊自言自語,其實是渡邊在追憶自己當年的青春歲月,它的鋪排和簡練,舒緩和節制,讓人在一種奇妙的絮叨之中,看到冷靜和隨意,這完全由內心意識流動而展開的內心獨語,它造成的距離並沒有讓讀者疏遠,反而讓節奏變得舒緩和沉穩,帶著讀者的靈魂慢慢下沉,並完全被渡邊的情緒和故事所淹沒。
外界評論
林少華:——《挪威沒有森林》,再包裝也瞞不過我等知情者。其實事情非常簡單:去年夏天在東京時,上海譯文出版社沈維藩先生(拙譯村上作品責任編輯)用E-mail發來一部長篇小說的若干章節,說有人模仿村上或“林先生譯筆”續寫《挪威的森林》,囑我 “奇文共賞析”。我粗粗看了一遍,回覆說“品位不高”。此後再未提起。不料,今年五月赫然冒出一本《挪威沒有森林》。於是奇蹟和魔術一同發生了:未出國門的這部中文小說成了 “總印量高達600,000冊感動日本的十大好書”之一,原來的男作者成了日本女作家福原愛姬兼譯者“若彤”並宣稱村上春樹“是她夢中的神秘情人”及“靈魂導師”,“本書被日本傳媒稱為‘一封公開出版的情書’”云云。各路媒體亦聞風而動,報紙上網頁上一時裡應外合烽火連天好不熱鬧。
最先揭穿這鬼把戲的,自然是沈維藩先生。他打開來稿電子存檔,去年夏天那部發給我看過的所謂《挪》之續篇及其作者姓氏聯繫電話即刻一目了然,文稿毫無二致。日本村上代理人方面也一再聲明日本從未有這個女作家從未有其個人網站從未有什麼《挪》的續篇,村上亦從未就此授權從未見過這個“情人”,明確表示此乃 “無稽之談”。於是,“森林”果真沒有了,“村上情人”原來是姓沈的中國大老爺們!順便說一句,此書作者姓沈,策劃人姓沈,仗義執言者亦姓沈。以致沈維藩苦笑“我們沈家的不肖子”。
我作為譯者和教書匠,當然無意捲入這樣的是非。無奈日本方面一會兒叫我介紹“續篇”梗概一會兒叫我說說讀後感。我能說什麼呢?再不肖也是自己的同胞,況且萬一惹得千呼萬喚不出來的村上君風風火火跑來中國打官司,誰臉上都夠尷尬的。於是我只好違心地說“續篇”續得沒有那么糟,沒有歪曲原著,且作者對村上先生的致敬之情溢於言裡行間……。得得!
可關起門來思之,心裡好不氣惱。氣惱什麼呢?氣惱咱們同胞真是不爭氣。彼國出了本《挪威的森林》,盜版滿天飛還覺不過癮,又挖空心思開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國際玩笑”。說穿了,純屬利令智昏,想錢想瘋了。錢人人都想,問題是別想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堂堂的中國文化人,為什麼就不能爭一口氣老老實實寫一本咱們自己的暢銷書,而偏偏在挪威的森林挪威沒有森林挪威有沒有森林上面耍小聰明想歪點子?想當年李白杜甫白樂天三國水滸登入東瀛列島,春風化雨,澤被萬方,朝野仰慕。仿作因之盛行,尤以仿三國仿水滸者蔚為大觀。但日本人畢竟還算老實,沒好意思說是三國水滸的續篇,更沒死皮賴臉自稱是羅貫中施耐庵的“神秘情人”。而當今部分國人竟落到全然不要自尊的可悲地步,好端端一個中國鬚眉男兒偏要當哪家子外國男人的“神秘情人”!依我看,豈止“沈家的不肖子”,更是炎黃的不肖子。焉能不令人氣惱!當然,我們的管理也有問題,以為假書不同於假奶粉,反正吃不出“大頭娃娃”,結果不了了之。這個不氣惱也罷。
上海譯文社正式函告媒體,澄清《挪威沒有森林》事件。
關於《挪威沒有森林》一書(被宣傳為“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神秘情人福原愛姬所著”)的真實性問題,策劃人沈浩波昨日再次表示,還未能與翻譯者若彤取得聯繫,他也非常焦急地等待著郵件。如果繼續得不到回復,他將考慮訴諸法律解決問題。他說:“我看到了作者的直接授權書,就沒有想到再看看原著,也沒有對譯者提供的資料進行核實。”他表示這是自己的疏忽。
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葉路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們不能理解出版人“不了解真實情況”這種說法。他說:“簽訂著作權契約時審核原作者身份,同時驗看原版書是引進著作權的必要程式。”他用“有意為之”來形容了這種行為。他介紹說,按照著作權書的編輯程式,編輯需要將譯者的翻譯跟原文進行審核,進行修訂和加工才能出版。
而且,上海譯文社確實曾收到部分章節相同的投稿。
著作權引進的陷阱據記者了解,近年來出版界不少號稱為翻譯作品的圖書其實作者根本就不存在。《沒有任何藉口》等書都是銷售不錯的著作權書,但被不少出版界人士疑為“偽書”。昨天,記者採訪了相關出版人。《沒有任何藉口》的出版人李臻治對記者表示,英文“沒有藉口”的書有好幾種,他們出版的這本的確不存在。但美國一位叫凱普的作者確實寫過幾篇文章,他們對這些文章進行了翻譯,並翻譯了部分關於西點軍校的相關資料,加入該書,重新編輯了一本中國版的《沒有任何藉口》。
李臻治表示,他認為出版物的宣傳有誇張之詞是一種正常的商業現象,在國內國外都是如此。在商品化的社會,圖書作為一種商品出現,必然和其他商品一樣,在做廣告的時候“自賣自誇”。
他說,實際上,如果這種略帶誇張的宣傳能夠吸引讀者的眼球,讓讀者能夠把目光從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中投向圖書,讓讀者接觸到一本好書,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李臻治認為,實際上隨著讀者素質的提高,讀者對書籍好壞的判斷力也會提高。廣告宣傳做得好,宣傳、包裝當然會對銷售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最終影響一本書銷售數量的還是書本身的質量。“廣告上說國外如何暢銷,國內讀者不買賬的書也有很多。書是一種特殊商品,讀者還是會根據實際的內容去選擇。”
對於《挪威沒有森林》真實性的爭議,相關出版人都表示,他們不了解情況不便發表評論。有人表示,在著作權引進的問題上什麼是規範,什麼是不規範,沒有什麼標準。即使找了著作權代理公司,有些公司也是不規範的,甚至有公司同時把一本書的著作權賣給幾家。
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葉路表示,很多出版單位敢對著作權書進行肆意炒作,是認為國內國外信息交流不暢通,不容易被原作者發現,實際上現在網路和通訊都如此發達,有很多專家學者在從事出版翻譯的研究,造假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他說:“一個出版社、一個出版人的謊言被戳穿,因此在讀者中、在業界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針對有些書並不是真正的引進書,而是在國內編輯而成,然後,以引進著作權書的面貌出現,比如故意將作者的名字改為英文譯名等等。
他介紹說,讀者可以通過著作權頁是否有引進著作權的登記號判斷它是否是引進著作權。
另外,他再次強調了作為出版單位應有的職業操守。他說:“實際上,這些辦法都很不高明,有很多成功的出版單位做原創書照樣可以有很好的經濟效益。”
據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沈維藩先生介紹,《挪威沒有森林》一書出版後,上海譯文出版社專門與村上春樹作品的著作權代理人酒井先生取得了聯繫,根據酒井先生傳回的資料,在日本沒有福原愛姬這名作家,也不存在《挪威沒有森林》這本書,同時,著名翻譯家、村上春樹作品的譯者林少華先生也證實日本不存在福原愛姬這位作家。
譯者若彤至今未現身針對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質疑,《挪威沒有森林》一書的策劃人沈浩波表示,出版方與福原愛姬本人簽訂了出版契約,並持有福原愛姬本人的授權書,當記者提出希望看到這份授權書時,沈浩波表示授權書現在出版社,暫時還不能提供。對於福原愛姬這位作家是否存在的質疑,沈浩波表示,出版方與福原愛姬的聯繫完全通過《挪威沒有森林》中文版譯者若彤進行,他本人並沒有見過這位作家,也沒有見過《挪威沒有森林》的日文原版。對於《挪威沒有森林》這本書是否屬於編造的偽書,目前他本人還不能作出判斷。沈浩波稱,他正在設法與若彤取得聯繫,要求若彤出示《挪威沒有森林》的日文原版資料,如果若彤不能提供相關資料,出版方將做出停止支付版稅等相應處理。另據沈浩波介紹,他雖然曾經與譯者若彤見面,並支付若彤翻譯費,但除了電子郵件,他並沒有若彤的其他聯繫方式,截至記者發稿時止,若彤尚未就此事作出回應,這位譯者本人也沒有出現。
《挪威沒有森林》前身記者注意到,沈浩波曾說《挪威沒有森林》的日文原名應該叫做《渡邊的叢林》,並承認《挪威沒有森林》的書名是出版方確定的,目的是為了吸引媒體與讀者的注意。但不論是《挪威沒有森林》還是《渡邊的叢林》,目前都找不到該書日文版確實存在的可靠證據。而沈維藩先生則表示他曾經於去年8月收到一份《挪威的森林》續集的投稿,向他投稿的是北京一位姓沈的人,投稿人聲明是此書的作者,並給他發來第五章的全文。沈維藩先生通過與網上連載的《挪威沒有森林》對比,發現《挪威沒有森林》第五章與他去年收到的稿件是一樣的。
在談到《挪威沒有森林》以村上春樹秘密情人為賣點的時候,該書策劃人沈浩波也承認這是出版方的運作手段,以便獲得市場成功。據記者了解,近年來出版界不少號稱為翻譯作品的圖書其實作者根本就不存在。
書摘
我與綠子在四谷車站相遇的時候,東京街頭已經是華燈初上。看著綠子從遠處走來,我覺得仿佛從陰界一下子回到了現實中。的確,算起來我與綠子已經一個多月沒見面了。
送玲子上火車後,給綠子打電話的時候,我的確覺得有滿肚子的話要對她說。可現在,坐了好久的車趕過來,在人群里找到對方,看著綠子嬌俏的臉,我竟不知從何說起。綠子也仿佛理解似的,只是與我並肩走著。秋風一陣陣吹過來,我不禁有點冷。
“對不起,”我說,“現在想說什麼也表達不好。”
“沒關係,”綠子頑皮地笑著說,“不過,渡邊君,在冷風裡走路可填不飽肚子喔。”
我這才想起來,從早上到現在,我還一直沒有吃飯呢。
“姐姐今天不在家,去我那裡吧,給你做滿滿一桌菜。看你瘦的,”綠子嘿嘿一笑,“把你折騰得夠戧,那個有夫之婦?”
“來不及了吧,這么晚?隨便吃一點算了。嘗你的手藝,以後有的是機會。”
“悉聽尊便。”
我們來到一家餐館,我要了煎蛋和沙拉,綠子要了一份義大利通心粉。我實在餓壞了,自顧風捲殘雲狼吞虎咽一番,吃罷,才覺得有了點精神,長出了一口氣。綠子吃著空心粉,不時抬起頭看我。
“胃口不錯嘛,渡邊君。”
“實在太餓了。”我一邊回答,一邊叫來一杯咖啡,“喝點什麼?”
“可樂吧,謝謝。”
侍應生端來可樂和咖啡,我喝了一口咖啡,將身子放低,完全躺在椅子裡,這才發現綠子模樣變了。她的頭髮已經長到肩膀,頭微微一動,便在臉頰飄來飄去,與以前相比,另有一番風韻。
“新形象如何?”
“你留短髮的時候,我想像你長發的樣子,當時覺得短髮好;如今,看著你留起長發,覺得長發似乎更適合你。”
綠子展顏,“你誇起人來蠻動腦筋的。”
“也不是動腦筋,只是想什麼說什麼罷了,可總讓人有這種刻意的感覺。”
“我么,喜歡你這一點。”綠子說,“渡邊君,問你一件事,可要如實回答。”
“我向來不會撒謊。”
“那好,”綠子趴在桌子上,下巴抵在手掌上,“沒認識之前,你一個人走在路上,一般想什麼?”
我嘆了口氣,原來就問這個!
“不過想一些瑣事罷了。”我回答說。
“真的?”綠子一臉的不相信。
“我不過是一個凡人,想的也只是一些人人會想的事。”
“我可不這樣認為,”綠子眼睛望著天花板,“以前的時候,看見你一個人來來去去,天馬行空,走在人群里,仿佛與周圍有一個截然的界限。我常常想走入你的生活,覺得那裡一定是一個我渴望的世界。我想鑽進你的腦袋裡,了解你,研究你,當時差一點就衝上去問你在想什麼,那種感覺非常強烈。”
“為什麼沒有衝上去呢?”
“肯定是不好意思嘛,那么多人。”綠子噘起嘴來說。
“所以就選擇在餐館主動搭話?”
“是不是讓你覺得唐突了?傻乎乎的。”
“那倒沒有。”我說,“我現在的回答是不是讓你覺得特別失望,有沒有想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沒有,現在已經不重要了,只是那個時刻特彆強烈罷了。”綠子將雙眼焦點定在我身上,“渡邊君,從來沒有對別人好奇過?”
“為什麼要對別人產生好奇心?”
“夠冷酷,”綠子手托下巴,“想不想聽聽我當時這方面對你的猜測?”
“倒不是冷酷不冷酷的問題,只是不想打擾別人,也不想太多人打擾自己而已。”我說,“不妨說說,你想的東西都很有趣。”
“我當時覺得,這傢伙一定永遠也不會對別人產生好奇心,看起來總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得其樂。”綠子說,“別人因此對你有好奇心,這一切你漠不關心,對你毫無影響。你就像一隻螞蟻,下雨搬家,秋天儲存糧食,冬天冬眠,一切按部就班。”
“我倒真想做一隻螞蟻,無憂無慮安安穩穩過一輩子。”
“英雄所見略同,”綠子打了個響指,“渡邊君,去酒吧。喝一杯?”
“正合我意。”
“還是不加奶油、砂糖?”綠子起身,看著我喝完的咖啡問。
我們來到一家迪斯科酒吧,綠子提議先跳一會兒。
“當為喝酒熱身嘛。”她說。
“你跳吧,我坐著等你。”我轉身在旁邊找了個座位坐下。一會兒,綠子滿頭大汗地走過來。
“好痛快,渡邊君,不想跳會兒嗎?”
我示意她坐下,叫了兩杯威士忌,兩人一飲而盡。
“乾杯,為我們的劫後餘生!”
“劫後餘生,什麼意思,渡邊君?”
我沒有回答,扭頭看舞池裡那些男男女女。少年時的兩個夥伴,木月和直子,都沒有躲過青春浩劫,被奪去了生命。只有我留了下來,不知是該慶幸還是悲哀。
“綠子,我想我們不會再分開了。”我輕聲地說。
“什麼?”綠子湊近我問,這時,新一段舞曲正好響起來。
“為久別重逢乾杯!”我舉起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