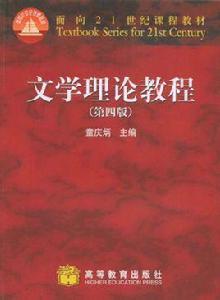中國古代的“實用說”
興觀群怨說
 孔子像
孔子像興觀群怨,來自孔子對詩社會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對詩的美學作用和社會教育作用的深刻認識,開創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源頭。出自《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說明了詩歌欣賞的心理特徵與詩歌藝術的社會作用。
文以載道說
 周敦頤像
周敦頤像“文以載道”的藝術命題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頤提出來的。他在《周子通書·文辭》中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塗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這裡所說的“道”,是指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周敦頤認為,寫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為封建統治的政治教化服務;評價文章好壞的首要標準是其內容的賢與不賢,如果僅僅是文辭漂亮,卻沒有道德內容,這樣的文章是不會廣為流傳的。
 曹丕像
曹丕像三國時期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載道”。其實“文以載道”的思想,早在戰國時《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
 韓愈像
韓愈像後來唐代文學家韓愈又提出的“文以貫道”之說,他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序》中說:“文者,貫道之器也。”。
西方的“實用說”
寓教於樂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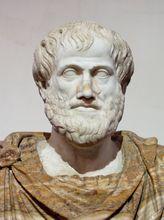 亞里士多德像
亞里士多德像對文藝的特點與社會功能之間關係所進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強調文藝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必須通過藝術的審美方式,即美的形象來達到。古希臘著名美學家亞里士多德在所著的《詩學》中已蘊含了這一思想,以後由古羅馬詩人、文藝理論家賀拉斯明確地表達出來。賀拉斯在《詩藝》中提出,詩應帶給人樂趣和益處,也應對讀者有所勸諭、有所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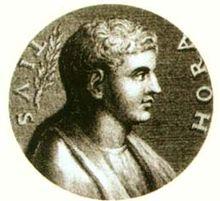 賀拉斯像
賀拉斯像賀拉斯提出“一首詩僅僅具有美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魅力”,這樣才能發揮藝術的教化作用。“教”,既指社會道德教育,又指文化開發,詩的“教”的功效應是崇尚美德、簡樸、正義、秩序和法律,應促使人接受文明,為人神劃界,為夫婦立定禮法。教是目的,教必須通過樂的手段才能實現,教化功能在詩和藝術作品中不應脫離使人獲得愉悅的具體形象,欣賞者總是在審美體驗和審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
“寓教於樂”說同時也揭示了藝術的本質特徵:藝術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須通過明晰的個性化,轉化為個體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藝術作品必須是形式與內容的美的融合、統一。
詩人如果想做到“寓教於樂”,要加強自身的人格修養和心靈淨化,同時應嚴肅對待藝術創作,遵循特定規範,既順應讀者習慣,又左右讀者的心靈和審美情感,引導讀者趨善避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