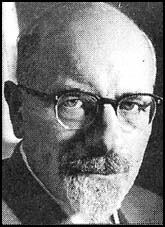
生平簡介
生於波蘭切爾扎諾夫一個猶太家庭,生長在波蘭傳統的文學實踐和政治解放的環境中。可他的家庭並不屬於愛國的貴族階層,而是屬於猶太中等階層,父親是印刷商。他年輕時期的政治信仰是社會主義。在其祖輩中,羅莎·盧森堡就生長在相鄰的盧布林省,她的父親是木材商。 和她一樣,多伊徹在十幾歲就參加波蘭革命運動,1927年初就加入當時屬於非法的波蘭共產黨。當然,在這兩者當中,波蘭的獨立徹底改變了多伊徹的世界觀。然而,多伊徹在《波蘭共產黨的悲劇》中這樣解釋道,使他成為勇士的主要政治環境仍是盧森堡。削弱傳統、妥協乃至最終消滅的方法,實際上形成了他不斷呼籲的主題——既尖銳又敏感——即波蘭戰前共產主義的命運。可是,多伊徹自己思想的形成卻是盧森堡遺產的延續。他從中學到了道德獨立、自發的國際主義、不妥協的革命精神——一個古典與歷史唯物論並存的馬克思主義者(盧森堡是第一個批評《資本論》中再生產綱要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它同工人運動的現實生活有密切聯繫。1932年,他組織了小股的反對勢力,攻擊德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史達林領導下趨向納粹主義興起的宗派消極狀態,還批評了“第三時期”路線的結果以及波蘭黨內的官僚統治。這些立場與托洛茨基流放時期的立場(他警告說希特勒發起的運動對歐洲勞工的威脅已達到頂峰)一致,結果被波蘭共產黨開除。
1936年10月完成的關於第一次莫斯科大審判的一個小冊子。其內容展示了他的未來生活和研究範圍。多伊徹對審判義憤填膺,他寫作時——如塔瑪拉·多伊徹(Tamara Deutscher)所說——“氣得手直發抖” 。多伊徹作品中義正詞嚴的抗議展現出他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顯著特點。在審判中,他並不滿足於僅僅披露史達林主義所謂“事實”的荒謬,他更具總結性地詳細論述了所謂“恐怖主義”在其譴責者面前謙卑心理的不可能性,冒險的“同謀”不可能頹然變成一種可憐的自責,並據此推測出迫使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餘黨認罪的途徑──格伯烏。私下許諾,只要他們在受審過程中出於道德目的而自殺,審判後便給予原諒,還可免除現在的體罰。多伊徹在這裡所表現出的深刻的觀察力——與他同時期人們過分的猜測相比——被後來得到的有關審判的事實所證實。對一位要重構歷史的天才而言,這無疑是一曲美妙的頌歌。他用一句熱烈的話語結束了這本小冊子:“歷史仍給社會主義留有時間拯救燃燒的大廈。我們不要失去理想的信念。”
1939年離開華沙到達倫敦。波蘭小股共產主義反對勢力已孤立並瓦解。他反對成立由托洛茨基領導的新共產國際,認為在一個“強烈的反應和失望的時期”對冒險是“完全不利的”;隨著第三帝國野心的擴張,一場新的歐洲戰爭一觸即發。多伊徹開始學習英語併到國外開始新聞記者的生涯。數月後,德國侵略波蘭,戰爭爆發。納粹在西方勝利後,緊接著就是蘇聯占領波蘭東部,相伴而來的是《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如此劃分,使多伊徹家鄉再次從歐洲地圖上銷聲匿跡。兩年後,希特勒大軍直撲蘇聯,數月內就逼近了莫斯科的大門。多伊徹在蘇格蘭的波蘭軍隊里停留一段時間後,成為倫敦《經濟學家》報社記者。之後寫下了大量著作,包括對文化大革命做出深刻分析和驚人預測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直至1967年在倫敦逝世。
在眾多品質當中,最突出的要數多伊徹堅毅的政治立場了。他在自己生活的時代偶然發現了它——從此忠實於他青年時期的政治理想,即便經歷了諸多的災難、左翼大廈一個接一個地被摧毀或者不得不加以重建,他都始終矢志不移。這種矢志不移是他在思想上完全獨立的結果:他在左派知識分子左右搖擺時、在流派分呈令人眼花繚亂之時——先是史達林主義或毛主義,又是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接著又鼓吹新工人階級或新社會運動,然後又是歐洲共產主義或歐洲社會主義——始終保持了個性和世界觀的獨立不羈。但這種獨立決不是宗派性或偽善者的孤立所能同日而語的。恰恰相反,與同時代使用英語的其他社會主義作者相比,多伊徹與讀者的交流更多更廣泛。其著作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翻譯,其文章被人們廣泛閱讀。這樣的廣泛性源於他作品強有力的文學魅力。但他的天分絕不僅僅表現在藝術上: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真真正正把握了古典馬克思主義在歐洲文化及其啟蒙這樣大背景下的根源,它無需特殊的辭彙——根本不需要技術性的辭彙——來尋找自己的言辭。採用傳記文學的方式寫作歷史與此有類似的意義——這種類型在抒寫過去的不同文學種類中最具有廣泛的感染力。就多伊徹而言,傳記形式有特殊的、深層含義。在傳主的個人生活中,他可以把道德話語和必然性話語加入進去,而馬克思主義總是很難做到這一點。他筆下的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在(他們表達過的或是拒絕過的)決定論這樣更廣泛的社會力量的前提條件下,都可以稱得上是卓越的歷史人物:可他們同時又是道德代理人,為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及其後果承擔責任。倫理傳統上指個人;因果動力指集體。多伊徹特殊的心理把握是個媒介,兩者——因果關係和責任——可以在他作品中起到綜合作用。今天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們需要用同樣的尺度看待雙方。換一種說法就是,回憶一下所作的真實的比較,就可以明白多伊徹的意義。多伊徹挑選了拿破崙時期反抗尊奉的三個人:歌德、雪萊、傑斐遜來加以比較——一個是平靜的奧林匹亞人、一個是空幻的反崇拜偶像者、一個是世故的政客。多伊徹的性格中包含了上述每一個人的一點成分。他們對左翼文化來說都需要。
主要著作
伊薩克・多伊徹一生著述甚豐,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先知三部曲》與《史達林政治評傳》。而前者迄今仍是舉世公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權威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分為《武裝的先知》、《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流亡的先知》。本書出版後,在學術界和讀書界引起廣泛影響。英國《每日電訊報》將其譽為本世紀重要的政治傳記之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格拉漢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觀察家》上說:
對我來說,伊薩克·多伊徹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這一年最激動人心的讀物。毫無疑問,這部傳記肯定會敖用英語寫成的最優秀的傳記之列。
另一位學者A.J.P.泰勒(A.J.P.Taylor)在權威刊物《新政治家》上評論道:
他(多伊徹)比以往任何一本書都更準確、更詳盡地講述了這個故事。他的這部傳記對任何一個對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歷史感興趣的人都是必讀。
在出版後的三四十年中,本書一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蘇聯史和托洛茨基研究領域重要的參考書。
托洛茨基的幽靈顯然一直在困擾著史達林的繼承者。托洛茨基曾揭露工人國家裡的“官僚主義墮落”,還指出史達林領導下所謂“堅如磬石”、“一貫正確”的黨正面臨著言論自由、爭論自由、批評自由等迫切要求的挑戰,並相信真正自願遵守共產黨的紀律只能也只應該建立在這些要求的基礎上。迄今為止,托洛茨基提出來的問題充其量也不過解決了一半,該事實足以說明,托洛茨基反史達林主義的鬥爭歷史現在具有了更多而非更少的原則意義。本書大部分敘述集中在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與以史達林為代表的後期布爾什維主義的孤立自保政策之間的衝突上。甚至還在史達林時代結束之前,這個衝突就已重新出現並變得愈加尖銳;而自此之後,天平的一端就開始向國際主義一側傾斜。這是喚起了人們對與20年代爭論的新興趣有關的另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