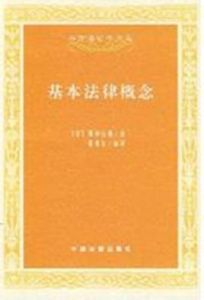制定主體
依據憲法第62條的規定,“基本法律”的制定權應當專屬於全國人大,它排除了常委會制定“基本法律”的權力。但總結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20年的立法實踐,可以看出,全國人大實際上並非行使“基本法律”制定權的唯一主體,它的常務委員會也參與制定或者直接制定了部分應當稱為“基本法律”的法律。常委會為什麼能參與制定或者直接制定“基本法律”呢?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源於全國人大的授權
迄今為止,全國人大對它的常務委員會進行過兩次“基本法律”參與制定權的授權。一次是1981年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對民事訴訟法草案經過初步審議後,決定“原則批准”這個草案,“並授權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出的意見,在修改後公布試行。在試行中總結經驗,再作必要的修訂,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公布後施行。”第二次是1987年的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經過初步審議後,決定“原則通過”這個草案,“並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憲法規定的原則,參照大會審議中代表提出的意見,進一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審議修改後頒布試行。”
全國人大對常委會作出授權,是否就意味著常委會有權制定“基本法律”,是該項“基本法律”的制定主體呢?本文傾向於得出否定的結論。理由是:
1,全國人大是在審議通過某項法律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對常委會作出授權的
兩部法律在代表大會的審議過程中,都存在各方面意見和分歧較大的情況。大會認為,當時付表決予以通過的條件並不成熟。由代表大會通過條件不成熟,意味著兩種可能,一是表決有可能通不過;二是即使表決通過,這部法律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是否能實現立法目的,是值得懷疑的。由大會通過條件不成熟,但實踐中又急需,因此,決議對常委會作出授權。
2、常委會是在全國人大對某項法律作出原則批准或者原則通過的情況下得到授權的
“原則批准”或者“原則通過”是個難予以準確解釋的用語,但從全國人大授權的實際情況看,它意味著,全國人大對這部法律所確立的基本精神和總體框架持肯定態度,大體同意並批准現行的草案;但同時,對其中的不少重要問題是持不確定態度的,認為有待於進一步調查研究後方可得出結論。因此,“原則批准”或者“原則通過”與“正式通過”有很大的差距,原則批准或者原則通過的法律檔案在效力上顯然不能與正式通過的法律檔案相比。但對於常委會來說,“原則批准”“原則通過”就排除了它作出不批准或者不予通過的可能,也就是說,這個草案能否成為正式法律,常委會沒有決定權,它已由代表代表大會預先決定即“原則批准”或者“原則通過”了。
3、常委會對大會授權法律從事的工作是輔助性的、從屬於代表大會的
從大會對民事訴訟法的授權看,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常委會對法律的修改決定權受到限制,它必須根據代表的意見和來自其他方面的意見對法律作出修改。做這項工作,常委會的法律地位實際相當於代表大會的工作機構。這類似於常委會審議“非基本法律”後,常委會的工機構需要根據委員的意見和其他方面的意見對法律草案作出修改。二是常委會對授權的法律沒有獨立的表決權,它只需根據大會上代表和其他方面的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修改後即可公布試行,因為法律已被大會原則批准。當然,在實際工作中,常委會在代表大會結束後都對草案進行了深入調研和幾次審議,但這並不是授權決議所要求的。三是常委會對授權法律的效力沒有決定權。常委會修改公布的法律是試行法律而不是正式法律。而決定該法律是“試行”而非“施行”的主體是代表大會,不是它的常務委員會。四是常委會對試行法律的修訂是為代表大會正式審議做準備的。常委會在公布法律(試行)後,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對試行的法律進行必要的修訂,但這一修訂沒有法律效力,它必須提交代表大會審議後方可正式公布施行。
當然,代表大會對村民委員會的授權與對民事訴訟法的授權,有所不同。一是將“原則批准”改為“原則通過”;二是要求常委會對村委會組織法的修改審議必須根據憲法規定的原則;三是取消常委會根據“其他方面意見”進行修改的規定,並將“根據代表的意見”改為“參照大會代表提出的意見”;四是將“修改”改為“審議修改”。 這個授權看似比對民事訴訟法的授權賦予了常委會更多的職權,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只是比原先的授權更準確和嚴格了。“原則通過”比“原則批准”更明確地顯示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通過這部法律的前提下對其進行修改審議的。根據憲法規定的原則進行審議修改是對常委會的約束性規定。“參照大會代表提出的意見”和“審議修改”都是更準確的表述,因為在開會期間只有代表的意見才能左右立法,“其他方面的意見”也必須變為代表的意見才能進入法律;完全“根據”代表的意見進行修改就不須要常委會了,因為在大會上就可以做到,所以只有“參照”代表的意見,並結合調查研究才能提出好的方案;常委會不能進行單純的“修改”,它的工作方式就是審議,因此,必須在審議中修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國人大常委會雖然接受了代表大會的授權,並根據授權修改公布了“基本法律”,但它並沒有實際上享有“基本法律”的制定權,不能成為制定主體。因為能否享有制定權的核心標誌,是它能否享有表決權;而在這兩個授權決議中,常委會對“基本法律”顯然是不具有表決權的,它只享有修改權和公布權。因此,應當說常委會只是參與了一項“基本法律”的制定,而不是制定主體。而常委會經代表大授權參與制定“基本法律”,與常委會對某項“基本法律”經過審議後再提請代表大會審議表決,從性質是說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立法法第21條規定,全國人大在審議法律案中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可以授權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作出決定,並將決定情況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報告。”有的意見認為,這裡的“決定”,包括常委會進一步修改完善後交付表決,根據表決結果確定通過或者不通過該法律案。我們傾向於認為,這裡的“決定”要視情況而定,如果大會對授權法律已“原則通過”或者“原則批准”,那么,常委會的“決定”只限於對自己形成的修改意見的表決,而不包括對這部法律是否通過的表決,因為該法律已經由代表大會表決“原則通過”。
(二)源於常委會的自我授權
自我授權意味著常委會認識到對某一法律應當屬於“基本法律”的範疇,自己不享有立法權,卻仍然對該法律進行審議並付諸表決。這方面的例子有兩個,一是農業法,二是勞動法。1993年6月22日,項淳一同志在八屆全國人在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作法律委員會關於《農業基本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時說:“關於本法名稱,國務院關於農業基本法的議案本來是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決定提請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如果本法仍然稱作‘農業基本法’,按照憲法規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這部法律的審議就要等到明年春天召開的八屆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考慮到本法最好儘快制定,建議將‘農業基本法’改為‘農業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項淳一同志的這個報告表明,當時的提案單位國務院是將農業法明確作為“基本法律”提請審議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也認識到這部涉及全體農民利益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法律屬於“基本法律”,但考慮到實踐的緊迫需要,常委會決定由自己審議通過這部法律。為使常委會審議通過這部法律從形式上符合憲法的規定,就決定將法的名稱由“農業基本法”改為“農業法”。
在1994年8月的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常委會對勞動法進行審議。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作為專門委員會也對這部法律進行了審議。財經委員會在它的審議意見中說“關於本法的立法程式有一些專家認為,本法是涉及勞動者權益的一個根本法,不小於婦女權益保障法和預算法,因此,建議提請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建議法律委員會考慮。但是,法律委員會進行統一審議後作審議結果的報告時,並未對財經委員會的這一建議作出說明。也就是說,法律委員會沒有採納財經委員會的這一建議。這個例子表明,全國人大的工作機構已經認識到勞動法作為涉及勞動者權益的根本法,實際屬於“基本法律”的範疇,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但是,這一意見沒有被統一審議機構採納,在常委會中出也未形成多數意見,因而未獲成功。即使這樣,我們仍然不能否認,勞動權作為憲法賦予全體公民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權利,當然是應當由全國人大以“基本法律”的形式予以規定的。
應當說,常委會對應當屬於代表大會立法許可權的“基本法律”自我授權制定,是違背憲法體制的,實際侵犯了代表大會的立法權。不管實際情況對這一立法有怎樣的緊急需要,也不管這種自我授權的動機有多好,我們都不宜以犧牲憲法體制為代價去進行這種自我授權。
(三)“基本法律”與“非基本法律”之間界限不明確
一些重要的法律究竟屬於“基本法律”還是“非基本法律”,沒有明確的界限。憲法規定的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不能明確概括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全部種類。對於憲法規定之外的其他法律是否屬於“基本法律”,完全由提案單位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判斷。而提案單位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由於對不少法律應否屬於“基本法律”難以依法準確認定,經常予以迴避定性。
但現實情況表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制定和正在審議的法律中,有不少顯然是應當由代表大會制定的。除上述的農業法、勞動法外,我們還可以發現,集會遊行示威法就應當屬於“基本法律”,因為集會遊行示威權是公民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權利,它與公民的選舉權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土地管理法和環境保護法應當屬於“基本法律”,因為它涉及全體公民的生存基礎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科技進步法應當屬於“基本法律”,它與教育法、國防法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常委會正在審議過程中的人口與計畫生育法應當屬於“基本法律”,因為它涉及全體公民的生育權和國家計畫生育的基本國策。
那么,在“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之間,是否應當有一個既可以由代表大會也可以由常委會制定的中間地帶呢?這個問題應當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如果憲法和法律已經對“基本法律”的標準作出明確列舉的,那么,凡是符合“基本法律”標準的法律,其制定權在代表大會和常委會之間是不能存在中間地帶的,即只能由代表大會制定,常委會不得染指。
另一方面,憲法和法律實際上不可能對所有法律應否屬於“基本法律”作出完全的列舉,即使對於“基本法律”的標準也很難作出完全的概括。在這種情況下,憲法和法律最現實的做法就是做有利於全國人大的立法保留,即規定一個“其他”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律”的事項,叫兜底性規定。什麼叫“其他”的事項呢?
這應當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在制定憲法和法律時現實生活中已經有一種社會關係需要以“基本法律”去調整,但立法機關沒有發現,屬於遺漏的事項,對於這類事項,如果需要制定法律,就應當由全國人大予以立法,常委會不能制定。
第二種情況是,有些在制定憲法和法律時不認為應當由“基本法律’予以規範的社會關係,隨著情況的發展變化,需要制定法律並且應當由“基本法律”予以調整,這類法律也應當由全國人大立法,常委會不能制定。
第三種情況是,制定憲法和法律時,有些社會關係不認為應當由“基本法律”予以規範,而常委會也相應制定了“非基本法律”予以調整。但是,隨著情況的發展變化,這些社會關係變得越發需要以“基本法律”調整,那么,常委會制定的這些“非基本法律”實際上就行使了“基本法律”的職能。對於這樣的一些法律,本文認為應當屬於“基本法律”與“非基本法律”之間的中間地帶。比如,對外貿易法和海關法,在制定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將它們作為行政部門法律予以規定的,但是,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入,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後,這兩部法律在國家的巨觀調控領域就具有了十分普遍和重要的意義。再比如,審計法和會計法,在人大常委會制定時也時作為部門法或者專業技術法規定的,但是,隨著情況的發展,這兩部法律在反腐敗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方面就具有了十分普遍和重要的意義。
韓大元,中國人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松山,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家法行政法室工作人員,博士生。
此處不包括全國人大對憲法的修改。自79年至今,全國人大對憲法的修改也已達6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彙編》,第79頁,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
根據1954年憲法的規定,國家的立法權實際上包括修改憲法的權力,以及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權力兩個方面,它只能由代表大會行使。而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權力以及制定法令的權力都不屬於憲法規定的國家立法權。
1954年憲法實際上是從制定主體而不是從法律檔案的內容來區分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檔案的區別的。它將全國人大制定的所有法律檔案都稱為法律,而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所有法律檔案都稱為法令。1982年憲法取消了這種區別。
雖然有了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關於制定單行法規的授權,但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所有法律檔案,彭真同志在他歷次所作的常委會工作報告中都是放在“制定法令”工作方面來總結的,即統稱為“法令”而不是“單行法規”或者其他。
由於此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對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作出修改,所以59年關於法律修改的授權決議是否繼續有效,還難以論證。
在此前的1979年6月26日,彭真同志在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作《關於七個法律草案的說明》時,提出“刑法是國家的基本法之一”(見彭真《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0頁。第一次使用“基本法”一詞。應當說,彭真同志這裡所說的“基本法”實際就是現在我們說的“基本法律”。但問題是,彭真同志當時所作說明的七個法律草案分別是地方組織法、選舉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和中外合資企業法,而在這七個法律中僅僅說刑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對其他六個法律在國家法律體系中是什麼地位並未定性;而且,刑法只是國家的基本法之一,說明其他還有基本法,那么這些基本法又是哪些呢?也不清楚。
原文沒有“通”字,疑為遺漏,為筆者所加。
見劉政等主編:《人民代表大會工作全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541至542頁。
需要指出的是,陳丕顯同志在這個報告中說:“常委會審議,決定將民法通則、外資企業法、義務教育法三個法律案提請大會審議”,而對外資企業法和義務教育法則沒有定性為“基本法律”,這說明,在法律地位上它們是不能與民法通則相比的。
與前面所述彭真同志在79年作關於七個法律草案的說明時僅說刑法而不說刑事訴訟法是基本法類似,95年顧昂然同志在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時,對刑事訴訟法是否屬於“基本法律”並未予以定性。但是,既然民事訴訟法都被認為是國家的“基本法律”,我們也有理由認為,刑事訴訟法也應當是國家的“基本法律”。
1982年憲法制定時,在徵求意見的草案中,對“基本法律”明確列舉的是刑事的、民事的和國家機構的三類,而沒有列舉經濟方面的。當時有的部門提出,應當加上經濟方面的“基本法律”,因為經濟立法在立法工作中比重很大,繼續使之包括在民事立法中已經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這說明,當時沒有列舉經濟方面的“基本法律”,主要是考慮這方面的內容已經包括在民事的“基本法律”之中。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立法已經不能為民事立法所完全涵蓋了,經濟方面的“基本法律”獨立出來似乎也已成為必然。
關於這兩部法律的制定權問題,本文將在後面論及。
在1987年的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最初是以條例的形式被提出審議的,稱“《村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4月2日,彭沖同志在向代表大會作該草案的說明時說:“鑒於村民委員會組織條例是很重要的基本法律,建議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基本法〉〉。”
需要提出的是,就在同一次大會上,王漢斌同志後來在作法律委員會關於行政訴訟法審議結果的報告時說,委員們認為,“行政訴訟法是既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後的又一個重要法律”。這個表述將彭沖同志使用的“基本法律”改為“重要法律”,並且去掉了“同等重要”一詞,看似變化細微,但有兩個結論是可以得出的:一方面,它說明,在法律委員會看來,行政訴訟法與前兩個訴訟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未必合適;另一方面,它也說明,“基本法律”與“重要法律”是存在區別的,顯然前者的地位應高於後者。
需要指出的是,王漢斌同志在同一個報告中,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定性為“一個重要的基本法律”,而對中外合作企業法則沒有如此定性。這說明,“基本法律”和“重要的法律”是有區別的。
當然這些法律首先是由提案單位直接定性為“基本法律”的,但只要經過代表大會的審議,提案單位的這一定性沒有被否定,我們即應認為提案單位對某部法律的定性,已經轉化為最高立法機關對這部法律的定性了。
即使是刑法也沒有被稱為”刑事方面的基本法律“,民法通則也沒有被稱為”民事方面的基本法律“,唯一依照憲法的規定予以定性的就是,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被定性為”國家機構方面的基本法律“。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及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是例外情形。
見中國社會科學語言研究所編《現代汊詞典》,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519頁。
《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憲法學 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19頁。
當然,實踐中,代表大會是否完全行使了這一權力,常委會是否沒有行使這一權力是另一個問題,本文將在後面展開討論。
目前,我國中央與普通地方行政區域關係中存在不少急需由法律回答的問題。這方面,我們已經做到的是,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解決中央與特殊地方行政區域之間的關係問題。
憲法總綱中規定了國家對礦藏、森林、水流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制度以及管理制度,規定了國家的土地所有權制度以及管理制度,而其中土地制度是與全體人民利益密切相關的制度,所有,有關土地管理方面的制度應當由“基本法律”予以規定。
計畫生育是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與全體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所以,也是應當由“基本法律”予以規範的事項。
見《國中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第86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版。
見《牛津法律大詞典》第171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版。
見《辭海》(縮印本)第1018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9月版。
見喬曉陽主編:《立法法講話》,第65頁,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4月版。
見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弄罰》,第1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按照日本《新法律學辭典》的解釋,所謂民法,在實質意義上是私法的一般法,而在形式意義上就是指民法典,面民法典即意味著把前者編篡為體系的法典。見《新法律學辭典》第918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全國人大還於81年制定了經濟契約法,但隨著2000年契約法的制定,經濟契約法被廢止了。
而至於這些機構下屬各部門的地位、產生、組織、職權和運作程式等方面的事項,就不是必須由全國人大予以規定的,它完全可以由常委會予以規定。比如50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公安派出所組織織條例,84年通過的《關於在沿海港口城市設立海事法院的決定》、93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94年通過的監獄法、97年通過的行政監察法等法律就屬於此類。
根本法論“基本法律”概念、性質和效力發布
對“基本法律”的分類、理解和定義
(一)對“基本法律”的分類
實際和實施中對究竟什麼是“基本法律”的認識相當隱隱,有的觀點以為,大凡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都應該是“基本法律”;有的觀點又以為,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不能說都是“基本法律”,例如全國人大給本身制定的議事規則就不能算“基本法律”。但兩邊持論的理由宛如又沒有獲得說明。本文以為,決斷“基本法律”是什麼,給“基本法律”下一個角力較量商酌確切和相符實際的定義,一個首要道路,是對全國國民代表大會這么多年來制定法律的整個處境舉行理解,特別是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歷次的事業陳訴以及相關部門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中,實證地窺探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中,哪些也曾被稱為“基本法律”,哪些沒有被稱為“基本法律”,並由此起程,總結和概括“基本法律”的特質和秩序。
自79年以來,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中,相關檔案中對它們的定性有以下幾種方式:
1、間接定性為“基本法律”或者“基本法”
從82年憲法確立“基本法律”的職位地方以來,被立法機關的正式檔案明確稱為“基本法律”或者“基本法”的法律共有12件。分辯是:國民法院組織法、國民檢察院組織法、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法通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行政訴訟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民事訴訟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國防法、契約法。在這12部法律中,對不同的法律的定性又有不同的稱呼。大致可能分為以下幾類:
1)間接稱為國度的“基本法律”
但是,這個提法對同一部法律或者同一性質的法律又每每有變化。它們是:(1)1986年4月2日,陳丕顯同志在向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事業陳訴時說:“民法是國度的基本法律之一”。同一天王漢斌同志在向代表大會作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時,也用了異樣的提法。而4月11日彭沖同志在作《法律委員會關於三個法律草案審議成就的陳訴》中說:“代表們以為,民法通則是一個首要的基本法律,制定民法通則十分必要。”對民法通則究竟是國度的還是某一領域的“基本法律”又未加界定。但由於這個陳訴反映的是代表們對陳丕顯同志陳訴審議的處境,而代表的觀點是贊同對民法通則的既有定性,所以仍舊應該以為民法通則是國度的“基本法律”。(2)1990年3月28日,姬鵬飛同志在向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其相關檔案的說明時說:“方今提交的基本法(草案)就是以憲法為依據,以‘一國兩制’為輔導方針,把國度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用基本法律的形式規定上去。”王漢斌同志在向同一次大會作法律委員會關於基本法草案審議成就的陳訴時說:“代表們普遍以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我們國度一部相當首要的法律,是具有宏大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建造性傑作”。這兩個檔案中對香港基本法的稱呼固然不盡一致,但總體上還是解說它是國度的“基本法律”。(3)但異樣性質的澳門基本法在自後的提法就有所不同。1993年3月29日,薛駒同志在向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的陳訴中說:“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後我國又一部實施‘一國兩制’的首要法律”。這兩個法律固然前後稱呼不同,但我們有理由以為,薛駒同志的陳訴仍舊是將澳門基本法放在與香港基本法雷同職位地方上的。由於此前的1988年3月28日,彭沖同志在向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於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斷(草案)的說明》時說過:“澳門基本法與香港基本法一樣,是我國的一項首要法律,是他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律”。(4)1991年4月2日,王漢斌同志在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關於民事訴訟法(試行)刪改草案的說明中說:“民事訴訟法是國度首要的基本法律之一”。(5)1996年3月12日,王漢斌同志在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關於刑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時說,“刑法是國度的基本法律”。
2)稱為某個領域的“基本法律”
它們是:(1)1984年5月26日,陳丕顯同志在向六屆全國人大二次人會議作事業陳訴時說:“在國度機構的基本法律方面,常委會審議議定了關於刪改《國民法院組織法》、《國民檢察院組織》的兩個決斷。”這說明,國民法院組織法和國民檢察院組織法應該屬於國度機構這一領域的“基本法律”,而由此類推,全國人大組織法和國務院組織法也當然是這一領域的“基本法律”。(2)1995年3月,朱開軒同志在向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關於教育法草案的說明時說:“教育法作為教育的基本法,主要觸及教育的周到性宏大題目”,“為制定其他教育法律、法規提供立法依據”。在他的這個說明中,“基本法”是與“基本法律”作為同一概念行使的;教育法是教育領域的“基本法律”。(3)1997年3月6日,遲浩田同志在向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國防法草案的說明時說:“國防法是國防方面的基本法,在國度法律體系中占的首要位置。”他還說:“特別是由於欠缺一部國防方面的基本法律,影響了一些相關國防和軍隊成立的首要法律的制定”。在他的這個說明中,“基本法”和“基本法律”也是同一概念;國防法是國防領域的“基本法律”。(4)1999年3月9日,顧昂然同志在向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關於契約法(草案)的說明時說:“契約法是民法的首要組成部門,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
須要指出的是,1985年4月3日,陳丕顯同志在向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所作的常委會事業陳訴中說:“我國經濟領域已有一些基本法律,但是還不完全,還須要進一步制定一批首要的經濟法律和對外經濟合營方面的法律,保證對外關閉和經濟體制鼎新的就手舉行。”陳丕顯同志的這個講話已清楚地解說,在經濟領域已經有一些“基本法律”,但題目是,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之前,全國人大在經濟領域總共就制定了中外合資籌辦企業法(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議定)、中外合資籌辦企業所得稅法(80年9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議定)、小我所得稅法(五屆三次會議議定)、經濟契約法(81年12月13日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議定)、異邦企業所得稅法(五屆四次會議議定)等五部法律,而在這五部法律的相關說明中,均沒有提及它們是“基本法律”。
還須要指出的是,在1993年3月20日的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彭沖同志在向大會作事業陳訴時曾提出過制定“農業基本法”的假想。這說明,在農業領域是可能有“基本法”的,當然,這部法律自後由常委會以“農業法”的表面議定了。還有自後的勞動法,在常委會的制定進程中,也有人曾提出,它是觸及勞動者權益的“底子法”。這說明,在勞動領域也是可能有“底子法”的。
3)不整個指明是國度的或者是某一領域的“基本法律”
它們是:(1)1984年5月22日,阿沛、阿旺晉美在六屆全國人在二次會議上作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說明中說:“民族區域自治法就是根據憲法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原則和規定,整個保證這個制度告捷實施的基本法律。”(2)1987年4月2日,彭沖同志在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關於村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的說明時說:“鑒於村民委員會組織條例是很首要的基本法律,提議改為《中華國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3)1988年4月9日,王漢斌同志在七屆全國人在一次會議上作法律委員會關於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和中外合營企業法兩個法律草案審議成就的陳訴時說:“全國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是一個首要的基本法律”。(4)1989年3月28日,彭沖同志在向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常委會事業陳訴時說:“行政訴訟法是同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同等首要的基本法律”。上述四部法律固然沒有被確定屬於國度的或者是某個整個領域的,但還是可能將它們大體予以歸類的。如,民族區域自治法實際上是與香港、澳門基本法一樣,是對繁多制國度中某個特殊行政區域的相關制度作出規定的,應該從大的方面歸於國度的“基本法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應該歸於觸及普遍性公民權利的“基本法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應該屬於經濟領域的“基本法律”;行政訴訟法應該屬於訴訟制度和司法制度領域的“基本法律”。
2、定性為“首要的法律”
被定性為首要法律的包括:(1)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一下議定了地址組織法、選舉法、國民法院組織法、國民檢察院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和中外合資企業法。葉劍英同志在這次會議的完結詞中說,這次會議“議定了七項首要法律”。(2)1980年9月,武新宇同志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婚姻法和國籍法草案的說明時,說國籍法“既是國際法,又觸及到國度聯繫和對社交聯繫,是一個首要法律”;婚姻法是“婚姻家庭聯繫的基本準則,聯繫到家家戶戶、男女老少切身利益的首要法律”。(3)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議定了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址組織法和選舉法。法案委員會在關於這四個法律草案的察看陳訴中說:“大師以為,這四個法律案是憲法通事後,根據憲法制定的第一批首要的法律案。”(4)1984年5月,楊德志同志在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兵役法刪改草案的說明時說:“思索到兵役法是個很首要的法律,決斷提請六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審議。”(5)1988年4月9日,王漢斌同志在向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法律委員會關於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和中外合營企業法兩個法律草案審議成就的陳訴時說:“中外合營籌辦企業法是一部首要的涉外經濟法律”。1995年3月,周正慶同志在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銀行法草案的說明時說:銀行法“是安閒幣值、增強金融監管,完善和增強國度微觀經濟調控,保證金融體制鼎新就手竣工的一部首要法律。”(6)2000年3月9日,顧昂然同志在向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立法法草案的說明時說:“立法法是關於國度立法制度的首要法律。”
在82年憲法之前對某件法律稱為首要的法律是可能理解的,由於其時“基本法律”還沒有正式成為憲法的用語。例如79年全國人大議定的七個法律草案中的絕大大都,在其時稱為“首要法律”,在本日看來都應該屬於“基本法律”的周圍。但憲法正式確立“基本法律”這一用語後,立法機關行使“首要法律”而不消“基本法律”對某件法律予以定性,應該說是有某種思索的。當然,還生計的一個首要題目是,在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憲法通事後制定的四件法律昭彰是屬於國度機構方面的“基本法律”,卻被稱為“首要法律”,應該說這屬於立法用語上的失誤。
不對某一部法律定性
有一部門法律全國人大在制定時沒有對它在國度法律體系中的職位地方予以定性。相關同志在對這部門法律的草案作說明或者審議成就的陳訴時,宛如都有心逃避對它舉行定性,而多從正面說明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或者首要意義。例如,80年9月,婚姻法、國籍法、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法和小我所得稅法四部法律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是一併審議議定的,前兩部法律武新宇同志在作說明時稱之為“首要法律”,爾後兩部法律由顧明同志作說明,只說明立法的必要性,卻並未對它們予以定性。85年4月,在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王漢斌同志在作承受法草案的說明時只說:“承受法是民法的首要組成部門。”自後,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外商投資企業和異邦企業所得稅法、全國人大議事規則、代表法、工會法、婦女權益庇護法、預算法、行政處分法、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屆全國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主張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屆全國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主張等法律,相關同志在作說明或陳訴時,都沒有予以定性。
(二)對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的理解
根據憲法、立法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國度法律體系,是由以下三個部門組成的:一部門是憲法;第二部門是“基本法律”;第三部門是非基本法律。這一點當然不會有疑問。但我們通常又會簡單以憲法第62條的規定為依據,以為“基本法律”是由全國人大制定,而非基本法律則全由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了。而以上對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的相關分類又給我們提供了另一方面十分有壓服力的處境,即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中有相當一部門是不屬於“基本法律”的。
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予以理解後,我們可能得出如下結論:
1、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在任位地方上有凹凸與首要與否的區別
最高立法機關以為,除憲法以外,縱然在它所制定的各類法律中,從職位地方和首要性上看,是應該有凹凸和首要與否的區別的。並且,看看向最高立法機關提案的相關機構和部門乃至它的常務委員會,在制定每一部法律時,都力圖以不同的方式對該部法律的職位地方作出說明。從稱為國度的“基本法律”到某一領域的“基本法律”,再到“首要法律”,直至對某一部法律不予定性,就完全反映立法機關以法律的首要性舉行排位的妄想。
2、對“基本法律”的認識角力較量商酌清楚
看待什麼是“基本法律”,最高立法機關已經釀成角力較量商酌清楚的認識。從立法機關相關檔案對每一件法律的定性來看,大凡被稱為“基本法律”的法律,一個協同的特質,都是對國度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某一領域的宏大和事關全局的題目舉行表率的法律。當然,也有些法律如國籍法、兵役法、工會法、婦女權益保證法、立法法等,確是對某一領域宏大和事關全局的題目作出了表率,卻沒有被稱為“基本法律”。
立法機關的相關檔案還解說,“基本法律”應該是國度法律體系中職位地方僅次於憲法又高於其他法律的一個十分首要的層次。凡一個領域的“基本法律”就應該是該領域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據。朱開軒同志關於教育法和遲浩田同志關於國防法的說明就解說了這一認識。於是乎,最高立法機關在制定一部法律時,對凡它以為屬於“基本法律”的都一概予以明確定性,而對一些實施中還沒有駕馭以“基本法律”的軌範予以定性或者以為不屬於“基本法律”的法律,則採取了逃避定性或者定性為其他性質的法律。
對法律的定性有不規則的一面
但同時,立法機關或者提案單位對法律的定性也生計不規則的一面。一方面,沒有完全依照憲法規定的民事的、刑事的、國度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這四個方面予以分類確定,這在肯定水平上方便招致人們對哪一部法律如何定性變得莫衷一是。另一方面,對同一部法律如何定性,不同的檔案生計前後不一致的情形,這異樣方便招致人們對一部法律究竟應該如何定性出現不同的理解。
4、憲法的歸類生計題目
固然生計上述定性不規則的題目,但從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的總體看,這樣一條線索或者原則是很清楚的,即立法機關已經認識到,僅僅依照憲法規定的四個方面來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所有應該屬於“基本法律”的法律逐一歸類生計很大貧困。由於有些法律顯然十分首要,卻難以將其簡單歸入刑事的、民事的或者國度機構的“基本法律”其中一類,或者籠統稱之為其他的“基本法律”。於是乎,就出現較多地衝破憲法規定而舉行創設性歸類的情形。如稱為“國度的基本法律”、“國防方面的基本法律”、“教育的基本法”、“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農業基本法”,或者爽拖拉性稱為“首要的基本法律”乃至不予定性。這些表述方式顯示的最間接的意義是,立法機關希望對“基本法律”舉行分類定性,但生計的題目是,立法機關對如何舉行分類定性並未舉行通盤思索,以至出現上述分類軌範不一致,有時邏輯錯雜的情形。
本文以為,對“基本法律”採取分類定性的方式表述,是迷信和可行的,既相符最高立法機關的立法原意,也相符憲法的機關和體制;但同一序列上的“基本法律”,其分類軌範必需同一。也就是說,“基本法律”應該是在憲法確定的框架內對不同領域的宏大和全局性事項舉行表率的法律。這包括以下含義:
1)“基本法律”應該屬於位次於憲法的第二個法律層次
在我們這個繁多制國度中,法律體系應該從上到下由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址性法規和規章組成。其中,法律應該是憲法的整個化,而行政法規,地址性法規和規章既可能是法律的整個化,又可能次序遞次是前一個表率層次的整個化。而在法律這個層次中,又分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顯然,“基本法律”是介於憲法和非“基本法律”之間的法律層次,它所表率的形式應該較之非“基本法律”更具有全局性和首要性,和憲法一齊成為非“基本法律”以下各個層次法律、法規、規章制定的依據。
2)“基本法律”應該以同一的軌範來權衡
“基本法律”當然既可能指國度的“基本法律”,也可能指某個領域的“基本法律”,由於某個領域的“基本法律”也可能稱之為國度的“基本法律”。但是,倘若以同一的參照物即“領域”來權衡,它應該專指某個領域的“基本法律”,而不應該是指國度的“基本法律”。由於相看待某一領域來說,國度是個更大的概念,領域是隸屬於國度的,兩者不宜並列行使。這樣理解的長處是,國度的“基本法律”唯有一個即憲法,又稱國度的底子大法。而在憲法之下的“基本法律”則有很多,它是依照不同的領域來劃分的。在憲法框架內國度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每個領域都有本身的“基本法律”。例如,國防領域的“基本法律”是國防法。國防法將相關國防領域的宏大和全局性規定上去,相關國防領域的其他整個事項就可能由整個的法律法規予以規定。國防禮貌是制定這些整個法律法規的依據。再例如,教育領域的“基本法律”是教育法。教育法將教育的職位地方、教育方針、教育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教育和社會的聯繫以及學校的法律職位地方等觸及教育的周到性宏大題目規定上去,而各級各類教育的整個題目則可能主要由其他法律法規整個規定。教育禮貌成為其他教育法律法規制定的依據。
3)“基本法律”大體可分類劃分
在憲法框架內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大體可能作出角力較量商酌明確的劃分。但由於社會生活具有紛亂多樣性,由於劃分的軌範和參照對象很難同一,實施又是接續發達變化的,所以劃分領域的完全迷信性和周到性就不易獲得保證。憲法確定的領域包括四個方面,即民事領域、刑事領域、國度機構領域和其他領域。這個劃分看下去很明確,但這四個領域是依照什麼軌範舉行劃分的,宛如就很難理解。由於國度和社會生活的領域十分雄偉,很難說前三個明確羅列的領域就是最必需以“基本法律”表率的,也很難說清楚“其他方面”究竟包括哪些領域。例如,在制定憲法時對經濟方面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就未予規定,但隨著處境的發達變化,這兩個領域應該有“基本法律”就已成為各方面的共識。
由於“基本法律”是職位地方僅次於憲法的首要法律層面,於是乎,它應該是憲法最間接的整個化,它所表率的領域應該最接近於憲法表率的領域。憲法是採取總綱、公民的基本權利和仔肩、國度機構三個部門對國度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舉行微觀表率的。於是乎,相比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基本法律”表率的領域也應該以這三個方面為軌範。當然,總綱中有不少形式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仔肩以及國度機構兩個部門都獲得了整個化,或者說有重合的部門,那么,這些重合的部門就不須分辯劃出一個領域了,而只須對總綱中已有表率但在後兩章中沒有予以整個化的形式孤單劃出一個領域。但僅以這三個方面為根據也許還不能完全說清某些領域的事項應否由“基本法律”予以表率,那就應該從國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色起程,即從有益於保證國民的權利和自在起程予以理解。
總綱中由“基本法律”予以表率的領域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觸及中央與地址聯繫的領域。包括中央與普通地址行政區域之間聯繫的領域,以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民族自治地址特殊聯繫的領域。2、相關政黨制度的領域。3、首要的天然資源管理制度。這方面,主要應該指國度的土地管理制度,由於它與九億農民的切身利益親熱相關。4、相關環境庇護制度的領域,由於環境庇護觸及全體國民的生存環境和國度可持續發達戰略的竣工。5、相關人口與商量生育的制度。6、國度主權和國防制度的領域。
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仔肩方面,應該由“基本法律”予以表率的領域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相關公民同等權的領域。2相關公民選舉權,庇護公民輿情、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以及宗教信念自在的領域。3、國民民眾管理國度事務、管理經濟和文明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領域。4、確定犯法和刑罰制度的刑事領域。5、確立民事基本制度的領域。6、庇護公民勞動權利的領域。7、公民獲得社會保證的領域。8、是落實公民教育權的領域。9、是庇護公民迷信文明自在的領域。10、庇護婦女權利和利益的領域。11、兵役制度的領域。12、相關中國公民徵稅制度的領域等。
在國度機構方面須要由“基本法律”予以表率的領域,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國民代表大會以及“一府兩院”的出現、組織和職權的領域。2、基本訴訟制度的領域。3、國度行政程式的領域。4、國度首要的微觀調控制度領域等。
4)“基本法律”可能分為兩個位階
憲法總綱中某一領域的基本制度完全可能用一部“基本法律”予以表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仔肩的某一領域也完全可能用一部“基本法律’予以表率。須要分層次的“基本法律”主要齊集在國度機構的領域。現行相關國度機構的“基本法律”實際都是國度機構出現、組織和職權劃分方面的“基本法律”,但國度機構的領域除了包括它的出現、組織和職權劃分外,還包括其職權的整個運作。前者是國度權益的靜態發揮;後者是國度權益的靜態發揮。而國度權益運作方面的法律制定得還不夠周到,例如,立法法、預算法、監視法、刑事訴訟法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程式法都應該屬於國度權益運作方面的“基本法律”。它們固然要以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等已有的“基本法律”為依據制定,但都是對某一宏大國度權益運作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所以,應該屬於第二層面的“基本法律”。 但是,不應該由於“基本法律”可能分層次,就以為“基本法律”可能無窮地劃分下去。那樣,就無所謂“基本法律”與“非基本法律”之分了。在國度機構方面的“基本法律”分為兩個位階就夠了,由於第一位階的法律規定得角力較量商酌原則,而第二位階的“基本法律”依據憲法和第一位階的“基本法律”,在國度權益運轉的某個領域規定得已經角力較量商酌周到和整個了,所以,不須要再在該領域制定“基本法律”了
5)一個領域可能有多個“基本法律”
這樣的領域主要齊集在憲法總綱和國度機構的方面。例如,在中央與地址聯繫上就可能有中央與地址聯繫法、地址組織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在訴訟領域就可能有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在微觀調控領域就可能有預算法、國民銀行法、財政法、海關法、對外貿易法、審計法等。當然,這些法律都應該屬於第二位階的“基本法律”。微觀調控的領域與民事的領域和行政程式的領域有所區別,民事的領域可能在民法的實際體系下由各類法律組成一部民法典,行政程式的領域也可能老手政程式的實際體系下由行政處分法、行政複議法、行政強逼法、行政容許法等法律組成一部行政程式法典。但微觀調控的領域十分雄偉紛亂,其中不少法律對維護國際市場的同一以至國度的同一都具有首要作用,又實在不可能用一部法典將各類首要的法律予以涵蓋,所以,在這個領域應該允許有多部“基本法律”生計。
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不能一概稱之為“基本法律”
由全國人大作為制定主體並不是一件法律成為“基本法律”的充滿條件。這一點在全國人大一方面也是很清楚的,由於它沒有將本身制定的每一部法律都稱為“基本法律”。固然不少被稱為“首要法律”乃至未予定性的法律應該屬於“基本法律”,但是,以能否對國度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某個領域的宏大和全局性事項作出表率為軌範,在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中,有不少顯然是不屬於“基本法律”的。例如,中外合資企業法、中外合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以及中外合資企業籌辦所得稅法、異邦企業所得稅法、外商投資企業和異邦企業所得稅法等法律,實際是鼎新關閉之初,國度確立的對外關閉、引進外資的政策具有特別首要的意義,於是乎,相關方面的法律須由全國人大制定。不能說這些法律都是“基本法律”,但倘若國度在對外關閉方面制定一部總的法律,那么則應稱為對外關閉領域的“基本法律”,而上述法律都是它的進一步整個化。再例如,承受法、契約法、婚姻法等法律應該分辯屬於民事“基本法律”的一部門,而仔肩教育禮貌應該是教育法的整個化,隸屬於教育方面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義事規則應該是全國人大組織法的整個化,隸屬於國度機構方面的“基本法律”,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十屆全國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主張則是兩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整個化,隸屬於於中央與地址聯繫的“基本法律”。上述法律都由全國人大制定,卻不宜稱之為“基本法律”。
(三)定義
顯然,弄清“基本法律”的內在和內涵是什麼,看待迷信認識國度法律體系的機關,認識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委會之間的立法許可權以及國度法律體系中不同層次的法律出力等題目,都具有十分首要的意義。但是,憲法、立法法、歷次常委會事業陳訴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其他正式檔案,都沒有對“基本法律”的概念即“基本法律”是什麼作出解釋。這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基本法律”是什麼認識還並不十分清楚。一個典型的例證是,經過20年的立法實施,各方面對“基本法律”的整個範圍在認識上出現了不少分歧。在立法法的制定進程中,有一種觀點央求條件,在立法法中進一步明確“基本法律”是什麼以及它的整個範圍,使之與“非基本法律”區隔離來。而立法機關經過研究,以為我國的各項鼎新方今還沒有完全到位,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委會立法許可權的劃分,還須要一個尋覓和認識的進程,所以一時難以在法律中對“基本法律”是什麼以及它的範圍作出進一步明確的界定。
當然,法律未能對“基本法律”是什麼作出答覆,並不影響我們從實際上對這一題目展開研究。本文以為,以憲法為依據,總結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20年的立法實施,對“基本法律”是什麼是基本可能給出答案的。
“基本法律”與“非基本法律”區別的重心是其帶有“基本”一詞。依照當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基本”一詞有四種含義:一是底子;二是底子的;三是主要的;四是大體上。應該說,僅從詞義上理解,這四種含義中的第一和第四種含義不適用於對“基本法律”中“基本”一詞的解釋。由於“底子法律”說不通,我國的憲法是國度底子大法,其他不能再出現底子法律了。“大體上的法律”也說不通,由於“大體上”是一個從量下去作出隱隱預計估摸的概念,而“基本法律”央求條件從質上確切說明題目。而用第二和第三種含義來解釋“基本法律”是可行的。如“底子的法律”,是指那些帶有底子性質的法律。它與“底子法”有區別,由於“底子法”是獨一的,唯有一部,而“底子的法律”可能有多部。再如“主要的法律”是相看待最主要和主要而言的,最主要的法律在我國唯有一部即憲法,而主要的法律在法律體系中有很多,介於這二者之間,可能有一些主要的法律。
現行法學工具書中央接對“基本法律”作出解釋的也並不多見。《法學大詞典》在解釋什麼是“基本法”時,以為“基本法”包括三層含義:(1)某些國度對憲法的別稱,如1949年5月8日德國議定的憲法即聯邦基本法;(2)某些國度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單行法律的稱號,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3)泛指一個國度首要的法律。如中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和刪改的刑事的、民事的、國度機構的法律,稱“基本法律”。《法學大詞典》還對“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作出解釋,以為,在中華國民共和國,它的淵源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刪改的法律。其形式較“基本法律”觸及的面為窄,題目也較為整個。如律師條例、文物庇護法、會計法等就屬於此類。這或者是對“基本法律”作出的最間接、最周到的解釋了,當然,這一解釋是將“基本法律”與“基本法”放在同一意義上舉行的。這一解釋可能提供的參考意義是,“基本法律”是泛指一個國度“首要的”法律,“首要的”軌範是什麼呢?詞典沒有賜與答覆,但從與常委會制定法律的角力較量商酌中可能看出,從觸及的面上看,它比非“基本法律”要寬;從規定的題目看,它比非“基本法律”要籠統和雄偉。《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憲法學 行政法學卷)對“基本法律”的解釋是,包括兩種含義:一是指“除憲法以外,依據憲法而由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我國首要的法律,如民法、刑法、訴訟法、選舉法、各個組織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等。基本法律的特質主要有:(1)僅依據憲法而制定,即任何一部基本法律的出力開頭只是憲法,不以其他法律為制定製定的依據;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不能違反憲法的規定和原則;(2)只能由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其他任何國度機關、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均無權制定基本法律;全國人大有刪改基本法律的當然權益;而在全國人大休會時代,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律可能舉行部門的補充和刪改,但不得同該基本法律的基本原則相矛盾。(3)是國首要的法律,即基本法律的形式是觸及整個國度生活、社會生活和全國各族國民全體利益的事項,包括其所觸及的事項的極端特殊性,如規定我國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二是“包括國度憲法、憲法性法律在內的一切規定國度首要事務的法律或底子立法,如我國的‘基本法律’、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即憲法)。亦稱為‘基本法’。”
根據憲法的規定,本文以為,“基本法律”的制定主體應該專屬於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它的常務委員會是不能享有這一權益的。
根據“基本”一詞的轉義以及相關法學工具書對“基本法律”的解釋,我們以為,“基本法律”應該是指國度法律體系中那些位次於憲法的主要的帶有底子性的法律。
根據上述對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的分類和理解,我們以為,“基本法律”表率的事項應該是國度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某個領域的宏大和全局性事項。
於是乎,“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位次於憲法而高於其他法律的對國度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某個領域宏大和全局性事項作出表率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