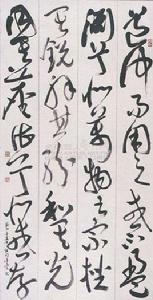詞語出處
和合它們的光彩,也共同吸納它們帶來的塵埃。
“王弼註:“無所特顯,則物無所偏爭也;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恥也。”沒有特別推崇的,物(生命體)的競爭就可以避免偏向;沒有特別輕賤的,物的厭棄就可以避免偏向。從王弼注的這層意思,後世對“和光同塵”的解釋,引申出“與世浮沉,隨波逐流而不立異”(《辭源》)的意思。對“和其光,同其塵”的通常的譯解是,“涵蓄著光耀,混同著詬塵”(任繼愈《老子新解》),“含斂光耀,混同塵世”(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
詞語翻譯
沈善增《還吾老子》:和合它們的光彩,也共同吸納它們帶來的塵埃。
沈善增《孔子原來這么說》附錄《“和其光,同其塵”新解》: “和其光”,就是在發展方面、在創造性方面,要“和”,要在發揚個性,維護多樣性、豐富性的基礎上積極融和;“同其塵”,就是在保持相對穩定方面、在基本原則方面,要“同”,要一律平等、一樣嚴格地遵守規則。
“新解”是在沈善增讀了《禮記·樂記》以後修改的。
詞語解釋
中國傳統文化里真是有無與倫比的寶藏。像《禮記》,五經之一,四書里《大學》、《中庸》兩篇也是出自《禮記》,《禮記》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應該特別的重要。但我讀《禮記》的感覺,卻是塵封已久,窟藏的金子基本上被厚厚的歷史塵埃所湮埋。儒家數一數二的重要經典的狀況尚且如此,遑論其它。但反過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之豐厚,遠遠超出我們的認識和想像。而且,我們的遺產是活的,不像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臘神廟那樣徒使今人驚嘆古人不可思議的創造力;但今天我們科技的整體實力肯定是大大超過了古人,凝結在物質文明里的古人的智慧,最大的作用,是告誡今人,特別是自以為掌握了改造自然的科技手段的現代人不要太妄自尊大。而凝結在中國文字中的古人的思想、哲學、智慧,不僅使中華民族成為現存於世的唯一的幾千年歷史、血脈不斷的古老民族,並且將在未來世界的建設中,起到正確的引領作用,對建設新世界是偉大的福音,因為這些思想、哲學、智慧,是經過幾千年歷史的考驗,有大量的正反經驗教訓可資證明。這樣的寶藏,我們只要發掘出一點點,中國乃至世界就受益無窮。
《樂記》將“樂”歸之於“天”,“禮”歸之於“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純明完備的禮樂,好比代表天地行使職能的官員。為什麼這么說?因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乾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音樂是從人心中生出的,是人心感觸事物,引起情感的變化,發而為聲的。情感的變化是最直觀的,也是很便於交流,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又是不可抑制地不斷地在發生的,所以,將“樂”歸之於天。古人對“天”的定義:一是先天,它是發生的原因,而不是發展的結果;一是天的功能是“生”,是創造,所謂“天生之,地成之”。“樂”是民間自發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被創造出來的,故而歸之於“天”。
相對“樂”來說,“禮”是後天的,是對行為規範的總結,是民間自發的文化活動,如祭祀、婚慶、治喪、交友、宴賓等活動中禮儀習俗的沉澱、升華,故而歸之於“地”。
這樣定性以後,《樂記》推論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契約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作樂以應天”,應“天”就是與“天”象徵的創造性相應,就是讓民眾心情愉快,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因此把“樂”的功用看作如“春作夏長”,“仁也”,“仁”就是愛。
“制禮以配地”,配地就是與“地”象徵的成果相配,就是讓民眾各得其所,按照一定的遊戲規則來合作、競爭,群居生活。因此把“禮”的功用看作如“秋斂冬藏”,“義也”,“義”就是“理”,遊戲規則不是誰的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按照邏輯規則來形成的,可以用邏輯思辨來證實或證偽的;也是“利”,按照這樣的遊戲規則來辦事,是可以共贏獲利的;又是“宜”,按照遊戲規則行事,是最適宜的,也就是內耗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因而,“禮”是文明成果,是對以前行事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提高。
“ 樂”的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和”。“和”的概念就是從音樂中來的。“和”的古字“龢”,由“龠”與“禾”兩部分構成。“禾”是聲符,表音;“龠”是義符,表義。“龠”是上古就有的樂器,據傳在大禹時代就用龠為舞蹈伴奏,有說就是排簫的前身,“龠”字中有三“口”,下部的“冊”字代表橫排,說明此樂器是多管橫排。“龠”演奏時可能多管同時發聲,構成和弦音,這是中國古人對“和”的最初的形象直觀。“和”,就是不同個性融合成內容豐富的整體存在。所以,古人說:“如樂之和,無所不諧。”(《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和諧”一詞就出典於此。從“和諧”的定義可以看到,“和”不是一般的“同”,只要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和”是一種高級的同,一種充滿活力的同。它不是為了維護個體的統一性而要壓抑個性,相反,卻要發揚個性;不是要消滅整體內部的差別,相反,卻要維護整體內部的豐富性。所以要這樣,就是為了使整體富有整體活力,故說:“大樂與天地同和”。
而“禮”的最主要的就是“節”,就是有所約束。孔子說,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故而說“大禮與天地同節”。
“禮”與“樂”都要求“同”,但“樂”是“同和”,“禮”是“同節”,這兩個“同”性質很不相同。但隨著君權的增強,獨裁的加劇,對“同”的理解越來越傾向於“同節”,“同”越來越變成被統治者的桎梏。重視禮教的孔子,又及時提出樂教,而且把“樂”歸之於“天”,“禮”歸之於“地”,“天尊地卑”,含有“樂”高於“禮”的意思,就是為了糾“禮以地制,過制則亂”之偏。而“樂”首先是民心自發,君主聽樂而知民情,“慎所以感之者”,以改進政治措施,這充分體現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因為秦以後君權獨裁已占據主流話語,即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尊已非孔儒,孔子的重樂倡和的精神,就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後人只知有禮教,不知有樂教,或者認為樂教是藝術教育,是禮教的輔助手段,不知道在孔子的儒學裡,樂教要高於禮教。“樂”是創造性的,“禮”是總結成果。沒有“樂”的創造,就沒有“禮”的成果。
關於“和”與“同”應有區別的觀點,中國古人其實多有論述,最著名的還是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但我們對孔子之所以說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是認識不足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無為而治,無知、無欲、不仁、不棄,儘可能地為民眾提供個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的發展空間。為了說明不是刻意拔高孔子,再引一段《國語·鄭語》中的論述。
鄭桓公看到周幽王倒行逆施,很擔心,怕殃及自己,就詢問史伯,周幽王的弊病在哪裡?史伯說周幽王是“去和而取同”,指出“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和”的政策是像陽光普照,能使萬物生長的,而“同”就難以為繼了。什麼是“和”?“以他平他謂之和”,用他的天性、喜好去規範他、使他順利發展。如果“以同裨同”,只使周圍的小圈子裡人得到好處,“盡乃棄矣”,到頭來就必定受到大多數人的唾棄。這話說在老子、孔子提出“和其光,同其塵”“和而不同”的二百多年前,可證明中國古人早對“和”的概念有了深入的研究。
中國人過去經常在處理個性與集體性、發展與穩定、民主與集中等問題上感到困惑,過去搞經濟有“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說法。如果吸收老子、孔子關於在創造性方面要“和”、在基本原則方面要“同”的思想,以“和”為主、以“同”為輔的思想,對正確處理這些關係是大有裨益的。我們還可以由此看到,和諧社會與創新性社會是“同出而異名”,或者說,“和諧”理念為創新性社會提供了觀念的支撐。從這裡還可以看到,如果說我們過去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國學”,或者說“國學”還不是一門成熟的學科,那么,我們今天更要努力建設國學,因為中國的國學,不僅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對整個人類的明天的發展道路,都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當代中國人,中國的專家學者、知識分子,義不容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