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公元前1500至前1000年形成的《梨俱吠陀》中,也提到一些女神。其中,最古老的女神似為諸神之母阿底提(Aditi),她的名字出現了近80次,卻幾乎從未被單獨提及,而總是與她的兒子們阿底多群神(Adityas)一併提到。她被描述為密多羅和伐樓拿、阿厘耶門以及國王和人們的母親。阿底多群神除了包括伐樓拿、密多羅、阿厘耶門、跋婆、達剎等偉大天神外,甚至還包括眾神之王因陀羅。阿底提是“無限的”,無邊無垠,廣闊浩瀚,越過雲層,穿過天空。她明亮輝煌,是眾生的護持者,為人們排憂解難,賜予一切平安和福祉。人們常祈求她幫助擺脫罪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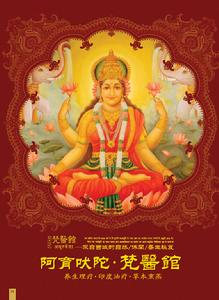 吠陀女神
吠陀女神然而,這樣一位諸神之母,在實行父權家長制的吠陀諸部落的神殿中,似乎早已大權旁落,日趨沒落。在詩中,這位女神公開奉承因陀羅。而在《梨俱吠陀》的晚出部分,詩人們甚至不願公開宣稱阿底提是眾神之母。及至梵書文獻中,阿底多群神之一的達剎已經等同於創世者生主(Prajapati)。由此表明,隨著畜牧經濟的發展和父權制社會組織形式的加強,吠陀諸部落已不願最低限度地承認這位古老的諸神之母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他們逐步創造出一位男性創世者,他最終以達剎——生主的形式出現。此後,阿底提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在史詩和往世書神話中,則已成為達剎之女。
應該提到的另一位女神是大地女神波哩提毗(Prithivi),她通常與天神帝奧斯(Dyaus)一起被祈求。《梨俱吠陀》中只有區區一首短詩讚揚她,而在《阿闥婆吠陀》中也僅有一首長詩歌頌她。在《梨俱吠陀》中,天和地被描繪為宇宙的父母。但是在許多段落中,天是典型的父親,地是母親。在某些段落中,詩人聲稱父親母親皆由其他神明所生。波哩提毗被稱作“慈母”,亡故者去往她那裡。黑《夜柔吠陀》中的《鷓鴣氏本集》與《鷓鴣氏梵書》稱波哩提毗的名字源自字根√prath,意為延伸。她具有偉大、堅定和光輝等屬性,她負載群山,支撐樹木,使大地豐饒。
《梨俱吠陀》中還提到穀物女神悉多(Sita)和娑羅室伐底(Sarasvati)等女河神,女神底提(Diti),夜女神(Ratri),語言女神(Vac)以及其他為數不多的女神。
《梨俱吠陀》中最重要的女神是黎明和朝霞女神烏莎斯(USAS),共有20首優美動人的頌詩對她禮讚,300多首詩提及她。她光彩奪目,袒露酥胸。詩人們讚美她“宛如少女,雋美異常,母親為你梳妝打扮;你赫然而現,朝霞為衣,怡然自得,神采飛揚,其他霞光均望塵莫及。”每日清晨,她乘坐駿馬所曳之燦爛金車巡遊天宇。她開啟天門,驅除黑暗與夢魘,帶來光明。她蒞臨世間,喚醒眾生,使萬物復甦,使鳥兒飛翔。詩中寫道:“朝霞女神促使阿耆尼點燃,並與太陽之目展現被造萬物,喚醒人們起身禮拜,向諸神舉行盛大的獻祭。”這位美麗的女神是太陽的妻子,跋婆的姊妹,伐樓拿的親屬,天的女兒。她與阿耆尼關係密切,後者常被認作是她的情人。她又與孿生黎明之神雙馬童有關。她還是“敵對者的剋星,為法而生者,法的維護者,歡悅的賦予者,一切悅耳之音的促成者,帶來吉祥,……”人們祈求她喚醒眾神,帶領他們去飲蘇摩。吟唱者們在盛讚她的同時,熱切祈願道:“使我們擁有財富,並使敵對者遠避;為我們準備豐美的牧場,以解燃眉之急。為我們驅逐仇敵,帶來財富;對歌者慷慨博施,雍容華貴的婦女。”“霞光萬道,照耀環宇,送來光明,給予我們漫漫長晝,噢,霞光,噢,女神。賜我們以食,我們因而歲熟年豐、繁榮昌盛,車輛和馬匹眾多。”值得一提的還有《梨俱吠陀》中的兩頌詩:“朝霞日復一日永遠光彩熠熠,女神今日亦給我們帶來光明,並賦予我們無窮的財富。她每日照耀晝之來臨;永生諸神,她以己力使萬物運動,而不衰敗。”“太陽生於朝霞之腹,一輪紅日,伴隨歌聲之抑揚而冉冉升起。”[6]朝霞每日重生,使太陽出生,並“永生諸神”,這說明,烏莎斯似為諸神以及自身之母,隱約閃現著大女神的古老身影。
雖然《梨俱吠陀》對烏莎斯的美好描述數量頗多,然而有趣的是,在後期吠陀文獻中,她的地位一落千丈。她甚至在隨後的印度宗教史上全無蹤影,在史詩和往世書里也難覓芳跡。即使在《梨俱吠陀》中,對於她的尊崇也並非一成不變。例如,她不能與諸神分享蘇摩祭。在《梨俱吠陀》IV.30.8-11中,詩人毫不猶豫地稱頌眾神之王因陀羅戰勝烏莎斯的英雄氣概:你擊敗了天的女兒(烏莎斯)——一個一心作惡之人,因陀羅啊!這是一件彰顯威力和雄風的功績。因陀羅啊!你這位偉大的(天神)壓倒了烏莎斯,儘管天的女兒趾高氣揚。當鬥志昂揚的(因陀羅)將車摧毀,烏莎斯倉皇逃離她破損的車。她的這輛車支離破碎,她自己則遠遠逃遁。[7]
對此,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高善必在《印度古代文化與文明史綱》中指出:“……作這種推測是合理的,就是某些別的地方不知道的特殊的吠陀神是沿用了前雅利安人的,如黎明女神烏莎斯,……他們當中,烏莎斯曾同因陀羅在毗耶娑河岸進行過一次有名的激烈戰鬥,結果,她的牛車被砸爛,而女神逃走了。……烏莎斯同希臘的黎明女神也有關係。”[8]
根據這種因陀羅——烏莎斯傳說和高善必所言,似可推斷,吠陀諸部落中存在著壓制烏莎斯崇拜的教派,因為這種崇拜可能來自一種前吠陀的母神崇拜宗教。在描述了因陀羅對烏莎斯施暴的同一首詩中,也涉及他戰勝非吠陀部落酋長們的情節。他掠奪蘇什那(Susna)的城市,擊敗達薩憍哩多羅(Kaulitara),殺死五千個達薩伐爾金(Varcin)的追隨者,為陀比提(Dhabhiti)獻上一百座石築的城池,殺掉三萬名達薩(Dasa)。兩個故事被結合在同一首詩中決非偶然。因此,因陀羅——烏莎斯傳說應源於部落紛爭。
《梨俱吠陀》稱烏莎斯為“諸神之母和阿底提的對手”。但她為何是阿底提的對手?她又是哪些神祇的母親?因陀羅對烏莎斯的敵視說明她原本不是吠陀部落的一位女神。鑒於因陀羅打擊烏莎斯的故事在《梨俱吠陀》的多首詩中都被重複,因此它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孤立事件,不應被忽視。同被稱作諸神之母的阿底提對於烏莎斯也懷有敵意,說明後者可能曾屬於不同的神殿。整個事件應為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宗教理想之間的鬥爭的反映。同時也說明,在吠陀神殿中,遠古時期普遍存在的女性崇拜原則幾乎不復存在。女神在數量上可以忽略不計,在地位上也微不足道。惟一的例外是烏莎斯,卻受到男神一統天下的吠陀神殿中的英雄因陀羅的攻擊和摧殘,落荒而逃。
印度梨俱吠陀時期的雅利安人主要從事畜牧業,善於征戰。一般來說,遠古社會中,在畜牧業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必然會有向父系家長制的完全轉換。因為,與農業經濟相比,遊牧部落需要更大的勇氣和付出艱辛。在無垠的草場上,面對頻仍的天災人禍,狼群襲擾,為了保護畜群,使部落得以繁衍生息,強健的體魄、過人的勇力乃至一個卓有成效的領導皆必不可少。於是,在遊牧部落中母權的重要性日漸減弱,而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地位急劇上升,終達至尊。此外,在遊牧生活中,牧人們不得不生活在炎炎烈日、電閃雷鳴和狂風暴雨之下,故而他們的宗教主要與天空相關聯,星系與自然現象經常化身為神明,以人的形象出現。遊牧宗教的至高神靈通常等同於統領其他神明的天神,一如一位父權制大家庭中的家長。以上種種原因,促進了男尊女卑、等級森嚴的父權制社會的產生。因此,梨俱吠陀的宗教是父權制的,是遊牧武士社會的反映。這與中國古代父權制的建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遠古女媧氏時,中國尚處於母系氏族部落社會,其時洪水泛濫。為避洪災,為治洪水,伏羲族、黃帝族、炎帝族等部落聯盟形成。治理洪水的大業,體魄、膽識、勇氣、毅力乃至強有力的領軍人物不可或缺。在這一過程中,父權日升,中國逐漸進入父權家長制的階級社會。儒家的文化淵源——代表父權的原始宗教即宗法禮教得以確立。
入印早期,梨俱吠陀諸部落不事稼穡,只是把它留給土著去做;並且,他們如同一切遊牧武士,蔑視農業,認為那不是征服者之族應當從事的職業。《摩奴法論》稱:“人們以為務農好;這個生計是受善人譴責的;鐵端的木棍既傷土地又殺地里的生靈。”[9]實際上規定了禁止高等種姓婆羅門和剎帝利從事農耕。由於農耕不是梨俱吠陀諸部落獲得食物的主要生產方式,故在《梨俱吠陀》中地母的身影難得一見,在《梨俱吠陀》中她僅被呼喚過一次。在此,雖然她被喚作母親,被稱作萬物之本,並與天空一起,被喚請賜福,但她與遠古時代母系氏族原始宗教中位居至尊的地母或大母神有著天壤之別。在吠陀宗教中,女神們屈居從屬地位,作為偉大天神的妻子,她們的作用更是不值一提。她們不過是天神的模糊反映,無甚獨立的力量。即使是諸如阿底提和烏莎斯這樣所謂的重要女神,在隨後的宗教史上也無些許重要意義。而早期吠陀文獻中也未發現如難近母、迦梨女神、安比迦、烏瑪等往世書中重要女神的名字,只是在後期的吠陀文獻中我們才發現對這些女神的偶或提及。鑒於在《梨俱吠陀》中無這些女神的記載,我們可以假設她們原非吠陀神明,後來才被吠陀部落採用。母神的不同名稱似乎原本是指不同的部落神,她們後來與印度河文明大神獸主——濕婆相結合。
從印度史前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中至尊顯赫的大女神,到吠陀時期地位日趨衰落的諸女神,說明包括宗教神話在內的意識形態的演變過程,歸根結底是由社會存在的發展決定的。隨著生產關係、社會經濟制度的變化,人們的社會意識也或遲或早發生相應變化。這又一次證明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著名論斷:“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0]
然而,當舊的經濟形式已被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取代,與舊的經濟形態相適應的社會意識並不會即刻退出歷史舞台。母系氏族社會的原始宗教歷史悠久,在漫長的歲月中,早已與女性崇拜的習俗和思想一起,形成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融入民族和社會的文化傳統之中,使人們難以與其一刀兩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它還會保留,只要條件適當,它便會改頭換面,以新的形式出現在新的宗教中。而當一種新的宗教出現時,為了擴大影響,吸引更多信徒,也自然會乞靈於傳統意識形態。因此,當父權制的遊牧部落的武士們侵入母神崇拜者的領地時,雖然引入了帶有濃郁的英雄主義色彩的男性天神,但並不能完全消滅母神崇拜的派別。
“雅利安古希臘人能夠使他們的宙斯和波塞冬矗立於雅典的高山之巔,卻不能推翻中央神廟中雅典娜的至高權威,以及她在土著雅典人民心目中的無上地位。”[11]在埃及,伊希思的光輝被奧希利斯所取代,然而她的影響並不能消除殆盡。相反,對她的崇拜在埃及以外的各地人民之中獲得廣泛傳播。
在中國,母系氏族原始宗教的傳統也沒有中斷。在男神確立了統治地位、父權家長制的一統天下之中,雖然這一傳統被降到民間,流入四夷,但女仙崇拜之風仍延綿不絕。道教中對女仙之首西王母的尊崇,對眾多女仙的歌頌和對女性成仙奇蹟的渲染,顯然是原始宗教女性崇拜的遺存。
印度吠陀諸部落是父神的崇拜者,但他們並不能消滅前吠陀的地母,於是大地女神被允許留在吠陀神殿中,當然她的威力已不可與丈夫天父同日而語。雖然女神在吠陀時期處於弱勢地位,但一伺時機成熟,她又再現昔日的輝煌。曾幾何時,她又搖身變為印度教性力派、佛教密宗等教派中的提毗(Devi)、佛母等大女神,頗具遠古時期威儀凜然、掌控一切的母神之風範,與其一脈相承,其深遠的影響延續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