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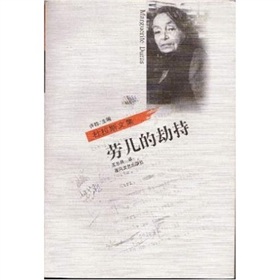 勞兒的劫持
勞兒的劫持勞兒瓦萊莉斯坦茵的故事確切的開始時間,是舞會最後的來客走進T濱城市立娛樂場舞廳大門的時候。它持續到黎明時分,勞兒V斯坦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舞會結束,夜晚終止,這個故事媳滅,沉眠,大約有十年光景。然後,某一天她目睹一對情人在街上親吻,這一吻又喚醒了這個故事……"我書中的所有女人,無論年齡大小,都來自勞兒。也就是說她們對自己都有某種遺忘。她們都是眼睛明亮灼灼有光的……""勞兒V斯坦茵,她已經成為我所有的書中居於首位的一個人物,這是很奇特的。我的這個小瘋子。正是她,銷售得最好。"
前言
有關勞兒的背景
文/王東亮
在詛咒世界的工滅、兆示大地的沉淪方面,瑪格麗特杜拉斯從不吝惜言詞與筆墨,人們不僅能看到《毀滅吧,她說》(一九六九年)這樣意指明晰的書名,也能聽到她作品中人物的妄語譫言:“讓世界消亡!讓世界消亡!”(《卡車》,一九七七年)而早已將虛構與現實、文學與生活的界線打破的女作家,在作品之外更是無時無處不在激揚著她的憤世與厭生。一九七九年某日,在極度消沉、頻於自絕(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正如她酒精中毒被送醫院急救一樣)的邊緣,她與一位打過電話來的朋友又談到了“世界的末日”,並使用了“沉沒”這個詞。朋友問她:“您真的認為末日將臨呈?請構想一下,一個世紀以後再沒有人讀您的作品了。”她馬上回答:“我?我的作品會有人讀的。在一份蓋洛普民意測驗上,我屬於人們最後還要讀的那一打作家中的一個。”
不難看出,對杜拉斯來說,寫作的誘惑還是大於死亡的衝動,而對其作品在她死後是否有讀者的在意更勝於“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終極關懷”。人們無法知道她希冀傳世的是哪些作品,也很少有作家像她那樣懂得什麼是文學時尚,但從她自己的傾向、作品本身的價值尤其是傷口所提出的問題看,這裡面大概至少有這部與童話《睡美人》有互文關係的經典之作、小說《勞兒的劫持》,或譯《勞兒V斯坦茵的劫持》。
這是一部奇特的小說,從書名開始就浸透著某種隱晦和歧義。事實上,國內法語界專業人士尚未就書名達成一致,有的譯成《洛爾維斯坦茵的迷狂》,有的譯成《蘿拉維斯坦茵的沉醉》。這裡的《勞兒V斯坦茵的劫持》也是個地奈的選擇。實際上,法文書名中,定冠詞與連詞除外,只有女主人公的父名較少疑問,“斯坦茵”是日耳曼語系中的姓氏,在杜拉斯的文學世界中,它常常與猶太姓相連。至於(勞兒V),那是(蘿拉瓦萊莉)的簡寫、縮寫,書中女主人公在發瘋後就是這樣自稱並這樣讓人稱呼她的。論者一般都注意到從到的轉換中名字的西班牙及女性特質的減損與消失,從到縮寫V的變動中真實名字的隱藏與截斷。至於難以定奪的,它是杜拉斯有意選用的多義詞,主要有“強奪、綁架、劫持”與“迷狂、令人著迷、狂喜、迷醉”的二層意思,也與宗教的樂極升天及世俗的誘拐婦女有些關聯。依杜拉斯本人的說法:“這本書應該叫做(劫持、誘拐),之所以用是想保留它的歧義”(《法蘭西文學報》,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一五月六日)。然而,即便作出了“劫持”的選擇,書名還是令人困惑:勞兒到底是劫持的主體還是被劫持的對象,也就是說,她是劫持者還是被人劫持?或許,這正是作者設定的誘餌,正如拉康所說“劫持者及村拉斯本人”,是我們讀者被杜拉斯誘拐、劫持,中了魔一樣被吸引到她的文本世界中,與她的筆下人物一起經受著某種痴迷、狂亂。
至於女主人公勞兒乃至整部小說的來歷,據法國符號學家讓克羅德高概教授在“杜拉斯文本的符號學分析”中記載:“有一天[杜拉斯]去一家治療心理脆弱患者的醫院。裡面的男女通常是一些接受藥物治療的病人。她到的那一天,是一個節慶的日子。大家在慶新年,有一個舞會。進入舞廳的時候,病人們在跳舞,當然有些人病症嚴重得一眼就能讓人看出他們是病人。在那裡跳舞的其他人中有一位年輕女人面絕對平靜。她跳得如此之好,人們會誤認為她一點兒病也沒有。可是,這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非常嚴重。正是看到了這么個人才使村拉斯產生了寫一部精神病人的書靈敏,後來就寫出了《勞兒的劫持》。”(《話語符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勞兒的劫持》一發表,就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從當時發表一一些主要書評文字中可以窺見其反響之一斑。
《世界報》,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據書名看,應該把《勞兒的劫持》當作一次著魔來接受。除此之外,該書是讓人不適、令人生厭的。[……]
瑪格麗特杜拉斯意圖何在呢?描寫一例神經官能症還是把握女性在愛情痛苦的反彈上的極端顯現?[……]
神經官能症、痴迷著魔、被過去的創傷糾纏不休,難道這些主題不都令人想起羅布格里孜孜不倦的《去年在馬里安巴德》嗎?[……]但是杜拉斯並沒有憑藉自己的想像力將兩人之族慣徹到底。[……]她的作品中最缺少的,便是對著魔迷狂的演繹闡發。她很快就跌落到自己的世界之中,這世界自《如歌的中板》以後越來越局限於愛的創傷。
《費加羅文學報》,一九六四年王月七日:
讀《勞兒的劫持》,首先讓人有點好戀《安德馬斯先生的午後》行文的完美、自如[……]但過不久便會注意到本書中的缺陷恰是它的長處所在[……],對話的作用只是為了讓我們去感受沉默的內涵[……],那些看來敘述得很笨拙的場景是為了向我們提示出某些缺失、某些空洞、甚至是某種虛無。我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感受,大概是因為這一虛無也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而我們也不願意對它有一個更清醒的認識。
女基督徒獨立青年團閱讀委員會(FIGF):
一個知曉事物等級之所在的基督徒面對這部貪瘠的傷口不可能不表示驚訝,作者的聰明和才智不足以掩蓋書中內容的空乏。[……]
所有的敘述都以冷峻、客觀的方式進行,自始至終沒有任何道德判斷介入。儼然一份臨床報告。冰冷的語調為這一極其險峻的敘事添上了某種高潔的色彩,而這種高潔又通過非常古典、純粹的語言得到強化。可是,這種對神經官能症的研究還屬於文學嗎[……]
瑪格麗特杜拉期在現代小說中占據著首要的位置,人們不可忽視她寫的書[……]。但是,喜歡她以前作品的人這次定將對這本書感到失望,即便它符應著“一種新美學”。《勞兒的劫持》看來是部失敗之作。
《費加羅報》,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這也許是瑪格麗特杜拉斯最美的小說。令人困惑並且有著看似簡單的服務。[……]
瑪格麗特杜拉斯身上所迸發的,是才華和聯慧。在文學事業中,沒有比女作家聽憑其感受去理解去闡釋更罕見、更美的了。聰明才智在這裡服務於她隨著跡象的出現去破解、去翻譯的本能。
這部小說技巧嬤熟細膩。它得到“新小說”作家的讚美,他們從中發現了他們自己所關注的事情,但杜拉斯卻以一種個人的方式和語氣將其表達出來[……]瑪格麗特杜拉斯停留在句子的表層、面部的平面。但是,藉助她獨特的才能,她懂得在詞語的閃爍模糊及動作的猶豫不決中截取出更深層的隱秘來。
《解放報》,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
《勞兒的劫持》是一部獨特的作品,首先是晦澀難懂[……]。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小說和電影劇本是一些悲劇詩篇,其中的人物常處在一個放大並加強著日常行征的危機時刻。[……]
杜拉斯運筆強勁且遲緩地表達出生命中的這些時刻,這樣的時候我們感受到自己是無能為力的旁觀者,在命運面前感到迷惑、恐慌不安;她用慢鏡頭的手法表達一些與撞車、垂死與尋震相類似的事故,[……]
“世上的任何愛也不能代替愛本身”,杜拉斯的一部小說(《塔吉尼亞的小馬》)中有個人物如是說。她所有作品要表達的別無其他。[……]與瑪格麗特杜拉斯堪為同類的不是新小說的作家們,而是寫出了偉大的形而上中短篇小說的契訶夫。
勞兒甚至牽動了結構主義大師、心理學家雅克拉康的神經,他為此專門著有“向寫了《勞兒的劫持》的杜拉斯致敬”(一九六五年)一文,開始了對這部小說的精神分析解讀。而杜拉斯本人對拉康在“致敬”中所流露出的男權中心思想的不滿,作品本身的女性人物-男性敘述著-女性作家寫作方式及其所提出的問題,又使得對小說的女權主義批評形成不小的規模。可以說,是拉康的“致敬”使得《勞兒的劫持》受到了知識界先鋒派、精神分析學家及女權批評家的廣泛關注,從而激發了文學評論界對杜拉斯與《勞兒的劫持》的研究熱情;又是拉康的盛名及其一以貫之、在“致敬”中絲毫不郵藏掖的矯飾語言與晦澀文體,嚇跑了許多的普通讀者,使《勞兒的劫持》漸漸被公眾視為難讀、難懂的作品,杜拉期本人也因而漸有了隱晦作家之名,直到一九八四年《情人》的成功才使她重新“通俗”。
儘管小說中勞兒的女友塔佳娜將勞兒的病因部分地歸咎於勞兒少時就有的某種心不在焉、某種若有所伯、某種心智不全,拉康還是像書中敘述者雅克霍德一樣,更傾向於考察“舞會事件”本身。在拉康看來,構成場景即所謂“原始場景”的,是舞會中兩個一見鍾情的男女跳舞時的忘我與沉醉,眾目睽睽之下勞兒成了被排隊在外的第三者:一個女人突然出現,就“動持”了她的示婚夫。整部小說可以說是這一場景的不斷回閃與重現,它與另一個幻象中的場景一起不斷纏繞著勞兒:她的未婚夫在他們去過的旅館房間裡“為另一個女人、一個不是她勞兒的女人脫下衣服”。勞兒走向了沉默與沉睡,十年一夢的婚姻生活,卻在自己的家門口被另一對情人的親吻喚醒。她走進這個二人世界,“劫持”了女友的情人,以欲望的主體身倫重演了“原始場景”的三人劇。
只是,在拉康看來,這不是能導致“治癒的事件”,新的三人劇更像是系了個更緊的打不開的結,勞兒沉溺於更、更深的欲望之中:“看”。她的“看”動搖著雅我的“我思”,分裂了認識的主體,“使敘事的聲音變成了敘事的焦慮”,使敘述者、男主人公無所適從、不知所終。正如拉康所說:“這種三人的存在,是勞兒安排的。正是因為雅克霍德的;'我思'以過於接近[病者]的治療--小說結尾處他陪她'朝拜聖地'而不是讓事件發生--纏繞著勞兒,勞兒才變瘋了……小說的最後一句話將勞兒拉回到黑麥田 ,看來是一個不夠果斷的結尾,它讓人猜想應對那種令人感動的理解有所提防。被理解不適合勞兒,'劫持'是不可救藥的。”
拉康認為,創作了勞兒這一人物形象的杜拉斯走在了精神分析之前,應該向藝術家表示“敬意”:“儘管瑪格麗特杜拉斯親口告訴我說,她不知道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勞兒來自何方,並且我自她其後的話中也能隱約看到這一點,但我認為一個精神分析學家有權採取的--或許不被如此認可的--立場的惟一好處,便是繼弗洛伊德之後
與瘋狂合為一體
文/黃晶
女性批判家、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對杜拉斯的作品的看法是:它不適合脆弱的讀者,因為它讓人與瘋狂擦肩而過,它不是從遠處展示著、觀察著、分析著瘋狂,讓人有距離地承受期望著一個出路,相反,它與瘋狂合為一體,直向你衝來,沒有距離,來不及躲開。
《勞兒的劫持》便是這樣一本杜拉斯將瘋狂進行到底的小說。
勞兒是一個有著從未改變的絲質身體的絲一樣的女人,一不小心,她就會絲般地在你手中滑落,逶迤於地,”你從她身上抓住的那一點點東西也是值得做一番努力的。“就是這樣一位站著的睡美人卻對麥克·理查遜--一個富少,產生了瘋狂的激情,並與他訂了婚。無法想像,他是怎樣被勞兒發現並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但隨後T濱城娛樂場舞廳卻上演了一場經典的拋棄的劇目:麥克·理查遜當著勞兒的面,棄她而去,追隨一位年長於他的女人--駐加爾哥達領事的妻子。勞兒卻始終微笑著。但在這幕劇快要拉上帷幕的時候,在一聲驚叫聲中,勞兒瘋了。
一切從瘋狂始,但杜拉斯並不打算擱足於此。”在我看來,既然要在勞兒·V·斯坦茵的故事中虛擬出我所缺少的環節,更正確的做法是平整土地、深挖下去、打開勞兒在裡面裝死的墳墓,而不是製作山巒、設定障礙、編造事端。“杜拉斯要將瘋狂進行到底。於是就有了孤魂野鬼一樣遊蕩於城市中的勞兒,有了躺在森林旅館後面的黑麥地里看著她愛著的人與他的情人幽會的房間的視窗的勞兒,有了與情人一起回到她被遺棄的T濱城的勞兒。
勞兒所有的瘋狂就是為了重建世界的末日,這是她在散步中看得越來越真切的自己的思想。這樣一個無法言說的人,因著一個無法言說的、缺失的詞,便處在了一種無法言說的瘋狂狀態。”她相信,她應該深入進去,這是她應該做的,一勞永逸地做,為了她的頭腦和她的身體,為了它們那混為一體的因為缺少一個詞而無以言狀的唯一的大悲和喜。“杜拉斯所做的也似乎是在外化自己內心的悸動時去尋找那一失去的詞,”一個並不存在而又確實在那裡的詞,在語言的轉角出等著你,向你挑戰。“
杜拉斯的這種瘋狂是如何攫取觀者的呢?一方面,敘事者我的突然出現,又是這么特殊的人物--勞兒好友的情人及勞兒愛上的人,使人物具有了穿透性,敘事的屏壁被打破,使觀者很容易進入。同時,杜拉斯令人嘆為觀止的奇妙的語言及譯者用心良苦的翻譯,使你輕而易舉地便被每個詞、每個句子、每種細小的感覺、每個凝於言語之外的意境所俘獲,所駕馭。人們可以不斷地聽到震耳欲聾的句子的爆炸的聲音。杜拉斯的語言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本質的語言“達到的效果:“寂靜的轟鳴”。海德格爾說,“言說作為世界四重性的築路運動,把萬物聚集到面面相對的近處。這種聚集靜謐無聲,平靜的一如時間之為時間,空間之為空間,一如時--空戲劇靜悄悄地上演。這種無聲的聚集,無聲的召喚,……我們稱之為寂靜的轟鳴。”
我於是開始懷疑:是否真的有人讀了杜拉斯的小說,而後跟著瘋掉了。
殺吧,她說
[法]米歇爾·芒索
據傳,是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已經成了一個傳奇,據傳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每一篇手稿被她丈夫羅伯特·安泰爾姆交給了伽利瑪出版社,他對雷蒙·格諾說:
“如果這部的稿出版不了,她會自殺了”。
這句話毫無疑問是屬實的,這裡,強烈地迴響著杜拉斯“全是或者全非”的聲音。作家通過奠定作品基礎的激情來以死相挾,她生活中處處可見的威脅,過激和譴責,在這句話中,都已經能聽得出來。
對於杜拉斯來說,死是始終被申明的。在眼眶裡,在交流中,在享樂的時候:
“你殺了我,你這是為我好。”
死亡和罪行遊蕩在她所有的小說、劇本、電影和訪談里。然而在羅伯特·安泰爾姆代言的申明中,除了用詞上無可挽回的暴虐,並沒有任何超俗之處。一個年輕作家急於通過自己作品的發表獲得承認,這樣只會帶來相當平庸的開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無法構想生活中可以沒有寫作,這根本算不得什麼。
文字或者生命,寫作或者死亡,對於所有只能超越世界才能承受它的人來說,這是共同的辯證法,杜拉斯顯然屬於這些人里走得最遠的--因為她總要走向極端--,從這種無生命出發,而這正是將文字神聖化的條件。
“我始終是這樣,在邊緣,始終。”
“我的生活並不存在。從來就沒有中心。沒有路,沒有線條。”
“他們的生活很可憐,作家們,我說的是真正寫作的人。”
“我可以用寫作來代替維持生命,廢寢忘食。”
“我感覺自己並不存在。”
“寫作,就是自殺,但不是通過死亡。”等等。
杜拉斯為迷失辯解。寫作、進而達到藝術,這不是在思考,這是迷失。對於她推崇的藝術家伊夫·聖-洛朗,她說道:
“有些人像他一樣被迷失自我所誘惑,甚至還想屠殺這種被某些人稱作生活的自我面貌。” 有一天,她會說:
“寫作,就是葬禮,人們是生活在對死亡的證明中。”
有時她一連幾個小時坐在陰暗裡,埋在她的柳條椅中一動不動,讓人感覺是個幽靈。
她投身到亡靈的國度里去了嗎?在這個國度里,有在她幼年時便死去的父親,生下來不久便夭折的第一個孩子,還有在她年輕時喪命的二哥。她迷失了自我,這是看得出來的,她游離於自我之外,游離於理性之外。
“甚至在我投入到一些故事中時,無論故事情節多么激烈,都很難到代這種感情,即全身心準備走向彼岸。” 從這個彼岸,這個異世或者從這個遠古的從前,她成為一個“通靈人”,回來了,充滿著虛無和失語,卸卻了自我的重負。
“沒有人承受得了我的存在,我自己也只是勉強承受。”
“我不知道是誰在寫。”
她覺得自己像馬蒂斯一樣是個“過渡者”。
她希望與“寫的那個人”結合在一起。她說她與弗朗西斯·培根很貼近,尤其是當培根這樣陳述時:“我對偶然能夠予我的東西非常貪婪,我期盼著它,它遠遠超出了任何我可能通過邏輯計算出來的東西。”
杜拉斯也尋找著偶然,尋找著遵循倫理學和美學要求的那種果敢。
“這裡才有野性。”
除了生下來就具有野性之外,還要能逾越所有的社會限制,跨過種種界限和規範,這樣才能發現存在於自我當中社會所不能及的東西。
“這是一種無法侵犯、無法滲透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東西。”
像蘭波一樣,她設計著自己的結局。她帶著同樣有意識的刻意的激情,同樣無意識的對某種命運的痴迷,回應著詩人:
“現在,我儘可能使自己廉寡鮮恥。為什麼?我想成了詩人,我盡力使自己變成'通靈人'。這就要在各方面無羈無絆去到達未知的所在。痛苦是巨大的,但必須堅強,必須生來就是詩人,而我看出自己是詩人。這根本不是我的錯,這么說是錯的:我思考。應該說:有個我在思考。請原諒這種文字遊戲:'我'是個他者。那些自以為是小提琴的木頭真是傻。”
杜拉斯,她,在酒精中放浪形骸。她想死,但她害怕。她喝酒,她沒有失去雙腿,但失去了肝臟。她,同樣,這不是她的錯,她被“選中”了。她在世上就是為了受苦,為了揭示不幸,有人嘲笑她,在她讀自己文章或者看自己劇本上演哭泣的時候,實際上,她哭泣是因為聽到了那種神秘的生命。歌手芭芭拉也說過:“在我唱歌時,我感覺唱歌的不是我。”
芭芭拉對那些承受痛苦的人表示憐憫,對於杜拉斯來說,涌苦是世界是無可避免的問題。
她厭惡那些將視線移開的人,她恨那些自以為幸福的人,那些蠢人,那些滿足於幻覺的傲慢之徒。她對那些拒絕規則的人感興趣:瘋子、妓女和罪犯。她興致勃勃地出入流氓、氓人、小人、怪人聚集的地方。Shoah這個世上恥辱至極的證明困擾著她。有時,她想成為猶太人。而後,她笑了,她的幽默救了她:“我也攪了進去。”但對她來說,來絕猶太人的行為證明了人類的本性絕對是野蠻的。她思考得越多,就越發被罪行所征服,不再承受或者希望死亡,她要壓倒死亡,通過和受虐狂不同的行動,與其被殺還不如殺人,與其做犧牲者不如謀殺,她要摧毀一切:友誼,受情,義務。
“讓世界走向毀滅,這是惟一的政治。”
她電影的標題《毀滅吧,她說》不是一句空洞的宣言。惟一可能……因為它不可能……存在的,是那種自我摧毀的激情。
對於她的女主人公,《英國情人》中的那個謀殺者,杜拉斯已經說過:
“克萊爾拉納想和我們所有人一樣去殺人。如果她寫作的話,她就不會殺人了。她的罪行比一本書還寫得清楚。”
“殺人”這個詞因此可以代替寫作這個詞。杜拉斯說到“寫作的罪行”她承認(或者說她坦言):
“殺人的想法是我生命中的一個恆量。是最永恆的一個恆量”。
她還進一步自我解釋道:
“寫作,是對新鮮的肉,對屠宰,對力的消耗的一種欲望”。也是一種盲目。
當她拍攝電影時,也採用同樣的方法:
“我與電影處於一種謀殺的關係之中。”
但謀殺的衝動左右了她,她在廢墟上建造。她確認人們只能在毀滅之後才能建造。她證明這一點,她的創造不再貧瘠,她又編出了另一部電影。對那些待產室里的情人,勸他們剃除往昔,並不異反覆絮叨。刀子在斷裂中看到了新生,斷裂,謀殺和屠宰,對於重組她遠離了的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罪行幫助她呼吸。
“不應該撒謊,任何人都有殺人的想法。我打開一張報紙,我有了殺的想法,納粹和我的區別,法西斯和我的區別,就是我知道我有這種能力,納粹卻天真地相認他們有殺人的權利。”
杜拉斯,作家,通過中間人殺人。《副鄰事》,這本她確認為本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書籍中的副領理,大喊著死亡,將槍瞄準了一些狗。
根本談不純潔,便同時又像一個孩子,面對自己蠢行造成的過失不知所措,杜拉斯承認道:
“作家,殺人,做壞事。”
是的。就是這樣,她無能為力,她想殺了照料她的護士,她想殺了揚安德烈亞,那位理解她的男伴。她說有些時候她受不了和諧和溫情。有些時候她必須迎合這個世界的恐怖,去擊碎,去毀滅。她說,完了以後,她會哭,也震驚於自己的暴行。
如果接受不了有時會存在一些被炙烤的想入非非的作家,人們就會可悲地對他們的暴行做出反應,並帶著憤恨和報復,但如果人們去靠近他們,就會知道任何正常的心理學都無法運用到他們身上。萊奧納爾伍爾夫,維吉尼亞的丈夫寫道:“她屬於那些衡有的生物,我認為他們都是天才,當然這些天才是一些比其他人複雜一些的生物……刀子不懂可能的東西。她懂的東西是不可能的……當她寫書時,是進行一種非常危險的冒險……作品耗去了她的精力,使她蒼白無力。”
杜拉斯不想和任何人比,從身體上說,她旺盛的生命力也一點不同於維吉尼亞全爾夫蒼白的典雅。然而和維吉尼亞伍爾夫一樣,她始終必須去摧毀兄弟的幽靈,多少帶些亂倫關係的兄弟,托比,雅克或者保羅,令人畏懼的愛人,從池塘或者海洋深遠的禁區突然出現,糾纏她,讓人犯罪。
維吉尼亞伍爾夫最終投入水中,淹沒了自己的肺。而瑪格麗特最後窒息而亡,氧氣瓶就放在床腳下。她早就預見到了:
“我將死於我的肺,會呼吸不暢而死。”
像缺少空氣的普魯斯特那樣想入非非,象卡夫卡一樣把寫作看作是殺人,她用一把斧頭敲碎了在人們心頭冰封的那個湖裡的冰。
精彩書摘
她真的來了,她從一個擠滿了晚上回家的人的汽車裡走下來。
當她向她走來的時候,她那非常舒緩、溫柔且循環不斷的腰肢扭動使她的行走的每一刻都像是對她自己輕柔的、隱秘的、無盡的謅媚,馬上映入眼帘的是那霧蒙蒙乾巴巴的一頭黑色濃髮,那白色的非常小的三角臉上占據著一雙巨大的、非常明亮的眼睛,眼中因拖著通姦之軀的不可言喻的內疚而凝集著某種沉重的憂愁,一看到這些勞兒自己就承認認出了塔佳娜卡爾,只是,勞兒認為,這個名字幾個星期來就在這裡那裡、遠處近處票浮,現在它在那兒了:塔佳娜卡爾。
她不引人注目地穿著一身黑色運動套裝。但她的頭髮是精心修衡過的,插著一朵灰色的花,用金質梳子別起,她用了全部的細心來固定住易散的髮式,又長又厚的黑色頭帶遮住她的前額,貼著她的明亮眼睛,使它們看上去更大、更憂戚,它本該只被惟一的目光觸摸,不可能在飄飛的風中不受損壞,她大概--勞兒猜想道--將自己的目光囚禁在暗色的短面紗中,為了在時機到來之刻惟有他才可以觸動並毀壞其奇妙的隨和,只一個動作她就浸沉在自己跌落的密發之中,勞兒突然回憶起來並且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那明亮的眼睛與濃密的黑髮的重合。那時人說她遲早有一天不得不把頭髮剪掉,這頭髮讓她感覺疲憊,它的重量會把肩膀壓彎,它的濃密凝重也會使她臉部變形,眼睛會變得更大,臉孔會更小,缺膚少骨。塔佳娜卡爾沒有剪掉頭髮,她成了個多發的勝利者。
那一天,就是這個塔佳娜嗎?或者有一點兒是她,或者完全不是她?她也將頭髮散披到後背上,穿淺色裙子的時候。我不再清楚。
他們彼此說了幾句話,從這同一個林陰道走去,走過了鎮子。
他們前後錯開一步走。他們幾乎沒有說話。
我相信看到了勞兒V斯坦茵大概該看到的東西:
他們之間有一種驚人的默契,它並非來自互相了解,而是正好相反,來自對了解的輕蔑。他們對無言的沮喪、對恐慌、對深度的冷淡有著同樣的表達。互相接近的時候他們走的更快。勞兒V斯坦茵窺伺著,她孕育、製作著這對情侶。他們的姿態騙不了她。他們彼此沒有愛。對她來說這意味著什麼呢?別人至少會這么說。她,卻有不同的說法,但她不說。使他們聯繫在一起的不是感情的支配,也不是幸福的支配,也不是幸福的支配,是其他的限制在無悲無喜之中的東西。他們既不幸福也沒有不幸福。他們的結合建立在無動於衷之上,以一種一般的他們隨時體會到的方式,任何的偏好都被排除了。他們在一起,就像迎面開來非常近地交錯在一起的列車一樣,周圍肉體的影色與植物的景色別無二致,他們看不到,他們並不孤單。可以和他們和平相處。通過相反的途徑他們得到了同勞兒V斯坦茵一樣的結論,他們,是通過做、說、嘗試、誤解、來往、說謊、失去、贏得、前進、再返回,而她,勞兒,卻沒費吹灰之力。
有一位置要去獲得,十年前在T濱城她沒有成功地得到。哪兒?她不配有T濱城歌劇院的位置,哪一個?應該先滿足於這個然後再去開避通道,朝向他們、其他的人居住的遙遠的彼岸前進一點。朝向什麼地方?彼岸在哪兒?
長長的、窄窄的建築物從前大概是個營房,或者是某個行政大樓。一部分用來作車庫。另一部分,就是森林旅館,它口碑不佳但卻是城裡的情侶們惟一的安全去處。林陰道叫森林大道,旅館是這條等的最後一個門牌號。建築物前面有一排很老的榿木,其中缺了幾棵。後面延伸著一片很大的黑麥田、平滑,沒有樹木。
在這一觀平川的鄉間,在這片田野上,太陽還沒有離去。勞兒知道這家旅館,因為她年輕的時候與麥克理查遜來過,散步的時候,有時,她大概一直走到這裡。是在這裡,麥克理查遜向她做出了愛的誓言。冬日午後的回憶也淹沒在無知無識之中,淹沒在她的腳步聲中緩慢的日復一日的S海市的冰結之中。
S海市的一個青春少女,就是在這個寺方,開始了化妝--大概持續了幾個月--為參加T濱城的舞會。她是從這裡出發去參加舞會的。
在森林大道上,勞兒失去了一點兒時間。既然她知道她們要去哪兒就沒有必要緊跟著他們。冒著被塔佳娜卡爾認出的危險是最令人擔心的糟糕結果。
她來到旅館時他們已經在上面了。
書摘
勞兒,在大路上,等待。日落了。暮色降臨,紅霞一片,大概伴著憂傷。勞兒在等待。
勞兒V斯坦茵在森林旅館後面,待在建築物的拐角處。時間過去了。她不知道現在出租的還是不是窗子開向黑麥田的那些房間。麥田,離她有幾米遠,隱沒,越來越隱沒在綠色與乳白色的陰影里。
森林旅館三樓一個房間的燈亮了。是的。房間還和從前一樣。
我看得出她是怎么做的。很快,她就走進黑麥田裡,任自己溜進去,找個坐的地方,躺下。她的前方是亮燈的那扇窗。但勞兒在光線照不到的地方。
她在做什麼她的腦中沒有想過。我還是認為第一次她在那裡時,她對此沒有意識,如果有人問起她會說在休息。一直走到那時走累了。下面要走的路也很累。還要重新出發精神煥發,精疲力竭,她深深地呼吸,這晚的空氣似蜜,甜得令人睏乏不堪。她沒有去想哪狼來的這一妙不可言的虛弱,使她躺在田地里。她任其所為,使其充盈到窒息的程度,粗暴地無情地搖動她,直到勞兒V斯坦茵睡去。
黑麥在她的身下吱嘎無--飽餐、狂食著這並不存在、看不見的演出,有其他人在那裡的一個房間的燈光。
某些記憶,經仙婦的手指,從遠處掠過。在勞兒剛躺在田裡不久它就輕輕地觸到碰她,它向她展示著,在夜色漸深的時刻,在黑麥田裡,這個女人看著一扇長方形的小窗,一個狹窄的舞台,像石頭一樣侷促,上面還沒有任何人物出場。勞兒她也許害怕了,不過只是一點點,她害怕可能與其他的人有更大的分離。但她知道有些人會抗爭--她昨天還這樣--他們在有一點理性使他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麥田裡時會跑著回到他們的家。但這是勞兒學到的最後的懼怕,別人今晚在她的位置上會有的懼怕。他們,會充滿勇氣地將它囚禁在自己的心房。而她,恰恰相反,她珍愛它,馴服它,用她的手在黑麥田上愛撫它。
地平線,在旅館的另一側,失去了一切色彩。夜降臨了。
男人的影子在長方形的光線中經過。第一次,然後是每二次,方向相反。
光線有了變化,它更強了。它不再來自房間深處,窗戶的左側,而是來自天花板。
塔佳娜·卡爾,披著黑髮裸露著身體,也經過了光線的舞台,緩慢地。她也許是在勞兒視線的長方形內停下來。將身體轉向男人應該在那兒的房間深處。
窗戶很小,勞兒應該只能看到兩個情人腰部以上的身。所以她沒有看塔佳娜頭髮的底部。
以這樣的距離。他們說話時,她聽不見。她只能看到他們的面部運動,這面部運動與他們一部分身體的運動一樣,無精打采。他們很少說話。並且,只有在他們經過窗戶後面的房間深處時,她才片得到他們。他們面部的沉默表情很相像,勞兒發現。
他又在光線中走過,但這次,穿著衣服。過後不久,塔佳娜卡爾也出現了,還是裸著:她停下來,挺了挺胸,頭輕輕地抬起,然後上身做了個鏇轉的動作,手臂伸向空中,雙手達到頭部,她把她的頭髮攬到胸前,卷一卷,撩起來。與她的清秀苗條相比,她的乳房是沉重的,已經相當松塌,這是塔佳娜全部身體上惟一一處於這種狀態的部位。勞兒應該記得從前它們是多么挺拔高聳。塔佳娜卡爾與勞兒V斯坦茵年齡一般大。我想起來了:當她擺弄自己頭髮的時候,男人走過來,他俯下身,將他的頭搭在她柔軟、濃密的黑髮上,親吻她,她繼續撩起她的頭髮,任他親撫,她繼續撩頭髮又放下來。他們從窗戶的背景中消失了很長一會兒。
塔佳娜又一個人回來,她的頭髮重新散落著。她走向窗前,嘴裡銜著一支煙,曲臂而倚。
塔佳娜卡爾離開了窗前,再出現時穿著衣服,重新穿上了那身黑套裝。他也經過窗前,最後一次,外衣搭在戶上。
房間的燈不一會兒就滅了。
大概是電話呼叫的一輛計程車在旅館前面停下來。
勞兒站了起來。夜色一片。她手腳麻木,開始幾步走得趔趄但很快,一走到小廣場,她就找到一輛計程車。晚飯的時間到了。她大大地遲到了。
她丈夫在街上,他在等她,驚慌不安。
她撒了謊,大家相信了她。她說她為了買一樣東西而不得不去了遠離市中心的地方,這東西她只能到市郊的苗輔中去買,是一些苗木她想來在花園與街道之間建一座籬笆牆。
大家對她在陰暗無人的路上走了這么長時間溫柔地表示同情。
勞和對麥克理查遜的愛對她的丈夫來說是妻子的操守的最安全保障。她不可能再找到一個與T濱城的那位一摸一樣的男人,要不她就該虛構出這樣的男人來,而她什麼都不虛構,讓倍德福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