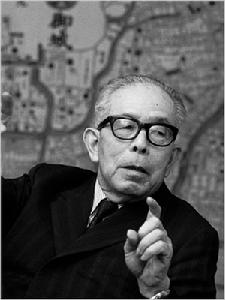生平簡介
 前川國男東京文化館
前川國男東京文化館1909年,前川一家隨任畢返京的父親移居東京,其後前川分別就讀於東京真砂國小、東京府立第一中學、舊制官立第一高等學校(高中),以及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前川一生興趣廣泛,教養深厚,尤其酷愛音樂,對歌劇更是情有獨鍾。成為建築家後的前川,設計建造的以公共建築如博物館、美術館,以及音樂廳居多,除其建築理念外,這與其深厚的文化藝術,特別是音樂修養不無關係。前川這一精神氣質及其建築思想的核心,除學前新瀉的童年記憶外,一高的經歷,似乎影響尤著。
一高時代,
生平履歷
 前川國男邸
前川國男邸前川在巴黎兩年,從具體的製圖、建築設計到建築理念上,深受柯布西耶薰陶。但在生活情趣上,卻頗受士官學校畢業、時任日本駐法使館武官木村隆三的影響。木村雖生於大阪,其祖父卻為弘前藩有力士族之出。前川因舅父佐藤尚武而結識木村,由於年齡、志趣相仿,兩人一見如故,十分投契,幾乎每晚不是去歌劇院聽歌劇,就是去紅磨坊或影院等娛樂場所盡興。1930年春,木村任期畢,與前川同船返國。木村遵祖父遺訓,決定在故里弘前建研究所推動地方民藝的產業化。因此,研究所大樓的設計,自然拜託給了前川。前川與弘前的建築緣起,由來於此。
 東京都美術館
東京都美術館明治初期的洋風建築,主要出自各外國工程師之手,部分參與工程的日本人工匠,日後也嘗試模仿洋風建築,卻因專業知識、建材、施工水平等局限,加之獨自的理解,多在洋風構造體上,裝飾和風屋檐或屋頂,故有「擬洋風」之謂。直至明治二十年代(1887年以後),受過正規訓練,留學海外歸來的辰野金吾等嶄露頭角後,擬洋風建築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至1922年前後,現代建築思潮及其樣式,開始在日本登台亮相。
從弘前這一地方城市來看,建築樣式的變遷狀況,與上述時序頗相仿佛。弘前的洋風以及擬洋風建築,大多出現在明治二十年前後。在弘前的洋風建築史上,當地出身的大棟樑(土木工匠)堀江佐吉,可謂居功厥偉。現存的洋風或擬洋風建築,絕大多數不是由其本人,便是由其弟子設計施工的。如東奧義塾外國人教師館(1901)、青森銀行紀念館(1904)、紀念市立圖書館(1906)、弘前學院外人宣教師館(1906)、弘前偕行社(1907)、弘前教會(1907),以及第八師團長官舍(1917)等。

如果說,弘前洋風建築的鼻祖非堀江莫屬的話,那么,前川則無疑為弘前現代建築之魁。
所謂「現代建築」,也即合理建築。現代建築反對古典主義的過度裝飾,甚至一度聲稱「裝飾即犯罪」。在造型上,追求幾何學的抽象美、機械美學的均衡性;在技術材料上,強調採用最新工業技術及其製品,如鋼筋、玻璃和混凝土。1920年代,以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賴特(Frank L. Wright)、柯比傑以及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為代表,形成以講求空間構成、規則性,以及忌諱裝飾為三大原理的國際建築樣式(international style)。特別是1926年柯比傑的「新建築五原則」,以及1928年6月28日在瑞士拉薩拉城召開的現代建築國際會議(CIAM,至1956年為止共召開十次),既為現代建築架設了理論框架,也賦予了其倫理性精神。可以說,直至1960年代末,在迭次紛起的各種思潮當中,現代建築始終占據主流位置,而巍然屹立其中的掌舵人,始終為柯布西耶。
個人成就及履歷
前川的處女作木村產業研究所(1932),及其晚年的作品之一弘前市齋場(1983),皆建於弘前──位於日本本州最北端青森縣境一座不無異國風情的文化古城。此外,前川在弘前的作品還有:弘前中央高校講堂(1954)、弘前市政廳舍(1958)、弘前市民會館(1964)、弘前市立津輕病院(1971,現為弘前市立病院)、弘前市政廳擴建大樓(1974)、弘前市立博物館(1976)、弘前市綠色相談所(1980)。作為日本現代建築名聞遐邇的領軍人物,前川的作品,儘管地域橫跨歐亞,數量多達三百多件,但如此集中弘前一隅,創作時間跨度如此之大,可謂絕無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