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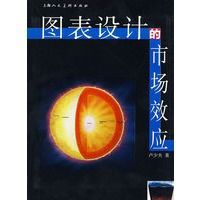 兩性對話:20世紀中國女性與文學
兩性對話:20世紀中國女性與文學荒林:由西方發源的工業生產帶來城市的極致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使人認識到自身的力量,同時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發生巨大的變化,從而使西方的人從神學的巨大黑暗之中解放出來,走向了世俗的、人的世界。中國社會的工業化受西方社會工業化的推動而發展,因此我覺得中國社會的現代進程所面臨的問題本身跟西方有很大的區別,這樣就使中國人的現代經驗也不同於西方。這樣一種被動的現代進程使中國人面臨的,首先是西方現代話語影響。我們是在遭遇西方現代話語,同時參照西方現代話語的過程之中來實現自己的現代化,所以面臨著既要從封建社會解脫出來,同時又要在承受外來的侵犯感、壓迫感中完成自身社會的轉型。20世紀中國人的解放不同於西方人從神性黑暗中出來,它同時面臨一個民族從另一些民族的強勢陰影之下解放出來,又面臨著個體的人從封建的壓制和天道、神權、族權、父權等一些金字塔的壓力和結構中走出來的複雜狀態。中國這樣一種世俗社會的形成,經歷了近百年的歷史,而且至今仍呈現一種多元化的、多規模的、多狀態的現象。因此中國的現代性體驗,既是多層次的,也是多狀態的。至於談論中國人的現代性,我想它是一個讓人感到非常複雜和棘手的問題。
王光明:談論現代現象和現代性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談到現代現象的時候,它是分層面的。在文化現象中,現代性又還可以分出其他幾個方面的層面,比如說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是作為一種精英話語,就是作為一種文人、學者和藝術家圈內的一個話語世界。比如從尼採到福柯,從薩特一直到米蘭·昆德拉,當然也包括畫家凡·高、音樂家辛柏格等等。作為一種精英話語,他們的現代性體現在他們對於工業社會是一種反抗的姿態。作為現代性的另外一重表現形態,還在整個現代以來的普遍性的、不斷高漲的民眾文化的造反運動。這樣的民眾運動,甚至包括中國的許多社會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也是現代性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在社會現實當中,它構成人的生活行為、感受方式的形態上的變化。甚至我們現在討論的女性主義,
或者說女性主義文學這樣一些事件,都跟精英話語,跟民眾性的造反運動有關聯,所以現代性的現象是非常複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