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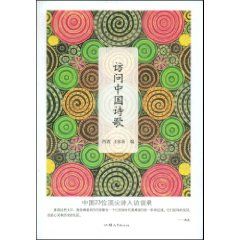 0
0叢書名:創美人文書系
平裝:322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7811203626,9787811203622
條形碼:9787811203622
商品尺寸:23.6x16.8x2.4cm
商品重量:440g
ASIN:B001NEITSM
內容簡介
《訪問中國詩歌(特價)》收錄了對當代中國最頂尖的23位詩人的訪談,這些詩人是:昌耀、牛漢、林莽、楊煉、翟永明、柏樺、張曙光、王家新、孫文波、肖開愚、陳東東、清平、蔡天新、西川、臧棣、西渡、桑克、周瓚、朱朱、姜濤、胡續冬、冷霜、蔣浩。在這些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們為了建築新的詩歌理想,闡釋寫作動機,探討寫作技巧,不約而同地拿起了批評之筆。這就為我們理解20世紀90年代豐富的詩歌文本提供了獨特而難以被替代的參照系,也為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詩歌領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其性質既是革命性的,又是建設性的。歷史的發展似乎又一次驗證了龐德的命題“詩人是一個種族的觸鬚”,劇變中的社會現實在這一時期的詩歌文本中得到了豐富而真實的反映。
編輯推薦
《訪問中國詩歌(特價)》:創美人文書系。媒體推薦
中國23位頂尖詩人訪談錄重讀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詩歌在一個巨變的時代艱難前行的一串串足跡。它們是詩的見證,也是心靈和歷史的見證。
——西渡
我注意到有人已經快到無法慢下來,我注意到人正失去虛度他時間的能力,正像也失去了自己的精力變得集中的天賦。
我知道人幾乎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僅擔任一個角色,尤其是現在,一個詩人無疑是一頭恐龍,並無生存的可能。
——朱朱
作者簡介
西渡,1967年8月生於浙江。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1989年畢業後任職於北京某出版社。著有詩集《雪景中的柏拉圖》、《草之家》、《風或蘆葦之歌》,詩論集《守望與傾聽》,編選過《太陽日記》、《彗星——戈麥詩集》、《戈麥詩全編》、《北大詩選》、《先鋒詩歌檔案》、《經典閱讀書系·名家課堂》等。王家新,1957年生於湖北丹江口市。曾下鄉當知青三年。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從事教師、編輯等職。1992年初赴英做訪問學者,回國後曾任教於北京教育學院,現為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詩集《紀念》、《遊動懸崖》、《王家新的詩》、《未完成的詩》等,隨筆散文集《人與世界的相遇》、《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取道斯德哥爾摩》、《為鳳凰找尋棲所》等。
目錄
昌耀“荊冠詩人”的最後聲息——答《青海日報》記者張曉穎
牛漢
歷史結出的果子——答《詩刊》記者曉渡
林莽
我一直在努力尋找那些寂靜中的火焰——林莽訪談錄
楊煉
“在死亡里沒有歸宿”——答問
翟永明
完成之後又怎么樣——書面訪談
柏樺
詩人要勇敢,要有形象——答楊鍵、朱朱、韓雪等
張曙光
生活、閱讀和寫作——答鋼克
王家新
回答四十個問題(節選)
孫文波
生活:寫作的前提——答文林
肖開愚
個人寫作:但是在個人與世界之間——肖開愚訪談錄
陳東東
它們只是詩歌,現代漢語的詩歌——陳東東訪談錄
清平
對西渡提問的一些回答
蔡天新
詩是可以攜帶的家園——答《東方時空》記者
後記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詩歌領域發生的變化有目共睹。這種變化的強度和劇烈程度超過了任何其他藝術領域,其性質既是革命性的,又是建設性的。歷史的發展似乎又一次驗證了龐德的命題“詩人是一個種族的觸鬚”:劇變中的社會現實在這一時期的詩歌文本中得到了豐富而真實的反映,雖然這一反映的廣闊和深刻程度從未得到恰當的闡釋,——某種程度上還被有意遮蓋著。一種敏銳而豐盈的歷史感不約而同地進入了這個時代那些優秀詩人的詩歌意識中。自70年代末新詩潮發軔以來,中國詩歌第一次以從未有過的自信和開放眼光向廣闊而豐富的存在敞開了自身。這種變化的起點多少帶有某種戲劇性。80年代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在進入90年代之際出現了令人怵目的分化和重組。這種分化和重組一方面體現在對80年代詩歌的本體論理想和文本理想的質疑和揚棄,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新的詩學理想的探討和確立。詩歌寫作不但在一個嶄新而又困難重重的環境中得到了延續,而且其有效性在某種程度上反而得到了加強,在變化中保持和發展了詩歌的可貴的人文品質,並提供了一批極有質量的詩歌文本。“90年代中國詩歌”遂因此成為新詩史上一個醒目的存在。由於批評的缺席(王家新引鐘鳴的話謂至少脫離文本5年、10年),90年代的詩人不得不同時擔當起批評家的部分職責,出現了一批優秀的詩人批評家(90年代詩人普遍的高學歷和豐厚的學識修養也為詩人從事批評工作創造了條件)。臧棣、王家新、肖開愚、歐陽江河、西川、黃燦然、陳東東等一批優秀詩人,同時又是出色的詩歌批評家。文摘
昌耀“荊冠詩人”的最後聲息①
——答《青海日報》記者張曉穎
張曉穎(以下簡稱張):您常自喻是一個“頭戴荊冠”的詩人,長期以來,您和您的詩都曾受到不應有的冷遇。應該說,今天這種狀況已得到了根本的改變,無論是專家還是讀者,都對您和您的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對此,您想說些什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荊冠”改為“桂冠”?
昌耀(以下簡稱昌):其實凡是我寫的東西,我感受到的都是時代給予我的。我在詩中寫出我對時代的感受,寫出我的美學追求、我的社會理想。至於是否被人接受,是否被人肯定,對我並不重要。讀者層次是多種多樣的,我不可能叫他們都接受,也不必強求。您說我的詩曾受到冷遇,我想這是正常的,但是我覺得多數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我的同時代人,以至於年長一代的讀者,都還能接受我的東西,這點我感到很欣慰。我的創作基本上分兩大塊:一個是在藝術上的有益探索,這方面比較偏重一些;另一個是抒寫我的內心世界,謀求與更多的讀者溝通。另外有少數比較難讀的詩,在圈內被叫好和欣賞。前幾年我的創作已積累到一定程度,但是出版比較困難,這就使我的詩普及程度不夠。在這方面,青海人民出版社做了些工作,為我出了幾本書,但多數還要靠我自己發行。我對自己寫的東西是比較自信的,因為我寫東西不是單純為了去當一個詩人。作為一個詩人,我覺得對社會應該有自己的聲音,對於美、對於善,應該做出自己的評價,包括自己的美學追求。我的詩不是遊戲之作,裡面都有些嚴肅的主題,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可,這就說明我的詩有存在的必要,有它的生命力,這也是我所追求的。“荊冠’’是命運決定的,至於“桂冠”,那是讀者給我的榮譽。這是兩回事。張:有人稱您為一個宿命的詩人,這種“宿命”和您畢生追求的崇高精神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昌:我對人生的看法是,從人生最初哇哇啼哭著降生到這個世界,仿佛就已被注定一個悲劇的命運。從生到死,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順的,都充滿了苦鬥這樣一種精神。從這點來說,它是宿命的。但是,人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後退。我在詩里表達過這樣的感覺:就像在一條船上和激流搏鬥一樣。此外,就人類社會發展而言,也無不血淚斑斑。許多思想家、宗教家、仁人志士都為人類的拯救或理想國的建立做出自己的努力,而且這種努力現在仍在繼續。如果說,這是善的精神,那么,我一生實際上都在敬重這種精神——包括基督那種犧牲自己、拯救人類的精神,包括釋迦牟尼普渡眾生的理想,都讓我很感佩。然而善的道路是如此曲折多艱,我的《唐·吉訶德軍團還在前進》正反映了我感受到的這種無奈。不管怎么樣,人生總要有點苦鬥的精神,沒有退路可走,也就是說,痛苦是絕對的,但是鬥爭也是絕對的(所謂“鬥爭”,是向命運的鬥爭),這種精神便是一種崇高的精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過這樣一種意思。詩是崇高的追求,因之艱難的人生歷程也顯得壯美、典雅、神聖、宏闊而光彩奪目。這就是我對“宿命”的理解。
張:您在《題(命運之書)》一文中這樣寫道:“對於我,命運僅僅是一卷書。”在這卷書中您讀到了什麼?又讀懂了什麼?在與命運的抗爭中,您是否重新領有了自己的命運,或藉助您的詩實現了對命運的嘲弄?昌:《命運之書》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探討命運的書,一個是對命運的書寫。我生命的整個歷程已經貫穿在跟命運做鬥爭這樣一個自始至終的過程。我是一個不大合時宜的人,在1950年代我是一個“右派”,到現在這個時期,好像我又不合潮流,這就是我的命運的必然結果。但是我對自己的追求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在詩里毫不諱言地說過:一個詩人應該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我覺得我的追求應該是和老百姓的追求貼得很近,這不妨參照我在書里題寫的一段話:“簡而言之,我一生傾心於一個為志士仁人認同的大同勝境,它富裕、平等,體現社會公正、富有人情。這是我看重的‘意義’,也是我文學的理想主義、社會改造的浪漫氣質、審美人生之所本。我一生羈勒於此,既不因嚮往的貶值而愧怍,也不因俱往矣而懊悔。如謂我無力捍衛這一觀點,但我已在默守這一立場……”(《一個中國詩人在俄羅斯》)因此,我對命運始終不認可,如果我認可了,那么也許我的命運就得到改變了。我年輕時就因為命運而受難,二十多年後,我更沒必要更改我的初衷。讀了我的書,就知道我的命運就是這樣一卷書。我沒有更改自己,沒有更改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沒有更改自己的人生態度。我想,在這方面,我就是我自己,我的命運是自己選擇的,我是主動的。可以說,通過我的詩,我實現了對命運的嘲弄。張:對青藏高原,您一定是有話要說的,因為您的許多作品都反映了青海的地域特徵,比如《青藏高原的形體》,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從文學的角度認識青藏高原呢?昌:我到青海來是1955年,那年我還不滿19歲,那完全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本來可以上大學,但我熱愛文學,特別是這種邊遠地區,對我有一定的誘惑力,所以我就投身到青海來了。在1957年,我就是因為一首詩,被打入社會的最底層,所以我跟青海的關係、感情是比較複雜的,它既是我自己的選擇,同時又使我感到痛苦……(詩人說到這裡,百感交集,潸然淚下)最近有朋友對我說過,在我的詩里,我可以摧毀一切,但在生活當中,一切可以摧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