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血色黃昏》
《血色黃昏》《血色黃昏》為你講述了文革時期,以一個北京知青在內蒙古的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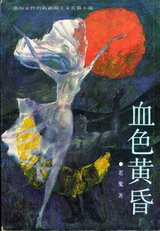 《血色黃昏》
《血色黃昏》這是一個北京知識青年在內蒙古的真實經歷。1968年冬,主人公林胡和他的同夥一起步行去內蒙古,自願紮根邊疆。兵團成立後,他因給指導員提意見而開始挨整,最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眾叛親離的專政生活中,度過了8年最底層的生活。期間他不斷地申訴掙扎,又不斷地被批鬥。
這一充滿悲劇色彩的靈魂,真實坦蕩,半是天使,半是魔鬼。他迷信拳頭,剛愎好鬥,四處碰壁,卻又嫉惡如仇。不屈不撓,不媚不俗。
作者以主人公的經歷為主線,向讀者展現了當年內蒙古兵團戰士的生活和心理狀態。狂低俗作品請刪除雨 違規書籍請自行刪除,否則報警處理中,60多條棉被蓋上了種子庫房頂;熊熊烈火里,69個青春的生命瞬間化為黑炭;送戰友上大學的路上,50多名女知青集體悲嚎。最可悲的是成千上萬知識青年的狂熱勞動,夜以繼日的開墾,換來的卻是美麗的大草原被一片片沙化。
全文語言剛勁粗礪,色彩沉雄悍野,內蘊真實豐富,讀後令人慨嘆、回味不已。
鑑賞
 《血色黃昏》
《血色黃昏》《血色黃昏》是老鬼根據自己八年草原生活的經歷創作的,出版的時候它被稱作“一部探索性的新新聞主義長篇小說”,作者在作品題記中甚至說:“它算不上小說,也不是傳記。
作者描寫主人公林胡的形象:他偏執、多疑、暴戾、好鬥,卻又剛毅、倔強、不媚、不俗、嫉惡如仇,1968年,他步行到內蒙古草原,自願紮根邊疆。兵團成立後,他因打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在自尊淪喪、人格扭曲的日子裡,林胡面對眾叛親離,度過了8年的勞改生活。
8年中,他孤獨、迷惘地在痛苦中掙扎,那一場場輾轉反側的畸形反思;一聲聲來自監獄的狂喊、怒罵;一紙紙發向兵團備級領導的申訴信、大字報;尤其是主人公注入全部生命的柏拉圖式的單戀和赤裸裸的野獸般的原始性慾,令人觸目驚心。
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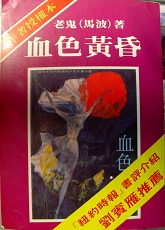 《血色黃昏》
《血色黃昏》比起那些纖麗典雅的文學作品來說,它只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塊石頭,粗糙、堅硬。”它沒有雕飾,沒有虛構和誇張,只是用樸素的、真實的敘述,向讀者展示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的原生狀態。正是這種寫實特徵,決定了作品思想內容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不同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從作品中開掘出不同的內容。但從總體上看,其內容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來認識。
首先是社會歷史層面。它描繪了特定歷史年代內蒙古草原混亂而又狂熱的社會生活:上山下鄉,階級鬥爭,革命大批判,等等。在這種生活中,人們喪失了理性、良知和秩序。國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搞所謂的草原建設,結果造成的是對草原的殘酷破壞;善良的牧民貢哥勒只有18隻羊,卻被劃了“牧主”成分,成為階級敵人,接受批判和勞動改造;真誠、純潔的城市青年滿懷報國熱情來到草原上接受“再教育”,而那些肩負教育使命的軍人、幹部大多是利慾薰心的流氓惡棍;一個知青僅僅因為打了一個流氓無賴,就被逮捕、被痛打、被審訊,從精神到肉體都受了七八年的折磨。
其次是人生層面,即向讀者展示特定社會環境中的人生形式。
林鵠等四人滿懷豪情來到草原,但八年過去,他們各自採取了不同的人生態度:林鵠野獸一樣沉默而又堅韌地活著,一個根本不愛他、甚至不願和他說一句話的姑娘成了他全部的精神寄託;雷夏講義氣、愛面子,最厭惡“叛徒”,但最後卻無意中背叛了肝膽相照的朋友,為了離開草原拍馬溜須;徐佐永遠忠於自己的信仰,病魔、酷刑、艱苦的生活都不能阻止他對真理的追求;金剛為了能夠平靜、安全地活著,崇尚“畏怯哲學”,把吃、穿看作人生的最大享受。這些不同的人生形式都既有局限性,又有合理性。特別是把它們放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去看的時候,就更難以肯定地判斷它是好還是壞。金剛和雷夏墮落了,但不墮落又難以生存;徐佐有信仰、有追求,但幾個小看守就可以像對待一隻雞一樣捆他、吊他、打他,置他於死地。
其三是心理學層面。
“階級鬥爭”中那種群體性的非理性狂熱,林鵠在石頭山上的生活中漸漸地“獸化”、喜歡孤獨,稚氣未脫的小看守從對徐佐的折磨中獲取生活樂趣,徐佐的瘋狂與飢餓感,等等,這些問題都屬於社會心理學的範疇。上述三個層面由淺入深,構成了《血色黃昏》所呈現的那種生活原生形態的基本框架。在展示這種生活形態的時候,作者的傾向性是十分鮮明的。表現在政治評價上,是對個人崇拜、主觀主義、以權代法的批判。表現在道德評價上,是對真與善的讚美和對假與惡的鞭答。純潔的青年忠於黨和國家。敢給領導提意見,下雨時用自己的被子蓋公家的糧食,為救火獻出生命,而某些“革命幹部”卻幹些泄私憤、損公肥私、姦污女知青的勾當。貢哥勒曾經被林鵠抄家、痛打,但卻在林鵠最孤獨、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冒雨送他去看病。表現在人性評價上,是對雄性力量的讚美——身處逆境的林鵠具有頑強的生命意志;又瘦又弱的徐佐卻有比鋼鐵還硬的骨頭,病魔和酷刑摧不垮他。《血色黃昏》雖然是一部以展示生活的真實形態為基本追求的作品。但其美學追求也是自覺的。作者在作品第四十七章中說:“獻身是一種美,求生同樣是一種美。難道一個餓人用牙齒咬斷瘦狼喉管,伏在獸毛里吮吸狼血不是一種驚心動魄的美嗎?”這種表述正可以用來概括這部作品的美學風格。作者對主人公林鵠頑強的生命力的描寫,對徐佐超人的毅力的描寫,對具有原始色彩的草原風光和草原生活的描寫,使作品具有了慘烈、悲壯的風格——或稱作“雄性風格”。
作者簡介
 老鬼
老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