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譯者: 劉佳林 納博科夫傳
納博科夫傳作者: 布賴恩•博伊德(Brian Boyd) 紐西蘭
副標題: 俄羅斯時期(上、下)
ISBN: 9787563383368
頁數: 820頁
定價: 66.00元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裝幀: 平裝
出版年: 2009年7月
內容簡介
本書從納博科夫的家族歷史與完美童年寫起,到納博科夫一家踏上美利堅國土前一刻結束,在時間段上與納氏唯一一部自傳回憶錄《說吧,記憶》剛好重合。在這部享譽世界的納博科夫評傳中,納氏虛實相間欲與還休的記憶不曾說出的,博伊德替他說了下去;納博科夫的讀者們不曾讀懂的,博伊德替他們讀了出來。納博科夫畢生創作中所有精心埋藏的典雅謎題,向讀者發出的狡黠挑戰,都被博伊德一一破解--也許,他正是納博科夫所召喚的那個最優秀的讀者。作為納博科夫最權威的研究者和傳記作者,博伊德以一個學者的深邃,一個理想讀者的洞察力,一個講故事好手的天資,勾勒納博科夫生平跌宕,專注於刻寫其“生命紋理”,更在對其作品的詳盡解讀與“解密”上做足功夫,是一部納博科夫愛好者與研究者們無法繞行的“納氏寶典”。
博伊德重拾納博科夫抖落的回憶線頭,甄別,辨偽,組合,串連,翻轉,復原了納博科夫在聖彼得堡、克里米亞、柏林、巴黎的生活場景,並帶領讀者一路蜿蜒而行,穿梭於其生活與創作之間。博伊德致力於納博科夫謎一般的個性及其對其創作的影響,揭示出納博科夫對人類意識的哲學思考,描述其哲學觀的發展軌跡,並就這些觀念之於其藝術創作的影響加以闡發,輔以大量精緻透闢、獨具慧眼的文本細讀,提煉出納氏其文其人所獨有的詩學特徵:獨立與花樣。他指出,作為一名作家、昆蟲學家與博物學家,納博科夫喚醒了我們對細節、整體與和諧的注意,他提醒我們,只要不以想當然的眼光看世界,我們就會發現庸常的生活洪流中潛藏著的藝術品質,從而深入一個更加豐饒的世界;在感受作家無窮的創造力的同時,看到世界那無限的創造的神奇。我們是時間與個體意識的囚徒,然而,在藝術或科學中,在記憶、想像、意志與良知之下,人類心靈可以自由馳騁,穿越自我的禁錮與時間的鐵柵。
源於熱愛與懂得,博伊德的評傳與納博科夫的行文風格一脈相承,其結構之完美,論述之精妙,解讀之細膩,引征之繁複,行文之詩意,蘊涵之豐盈,無處不流溢出大家氣魄,至今無出其右者。
作者簡介
布賴恩·博伊德(Brian Boyd),紐西蘭奧克蘭大學英語系傑出教授,國際知名學者,納博科夫研究權威,成果榮獲多種獎勵,並被譯成12種文字。他最富盛名的學術成果包括兩卷本傳記《納博科夫傳:俄羅斯時期》、《傳納博科夫:美國時期》,關於《微暗的火》、《阿達》的研究著作以及他負責的網站“阿達線上”。此外,他還編有《美國圖書館中的納博科夫》(三卷本,1996),合編《納博科夫的蝴蝶》(與羅伯特·麥可·派爾合作)、《詩歌與譯文》(與斯坦尼斯拉夫·什瓦布林合作,哈考特,2008),並幫助義大利阿德爾斐七星詩社出版社和西班牙銀河出版社編輯納博科夫全集。他的近期著作包括《論故事的起源:進化、認識與小說》(貝爾克納普/哈佛,2009)以及《文學的進化論研究:藝術與科學讀本》(哥倫比亞,2009)。目前正研究撰寫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傳記。目錄
插圖說明日期說明
中文版序
引言
第一部分 俄羅斯
第一章 自由血統:過去的花樣
第二章 醒來的世界(聖彼得堡,1899—1904)
第三章 第一次革命與第一屆杜馬(聖彼得堡,1904—1906)
第四章 蝴蝶(聖彼得堡,1906—1910)
第五章 學校(聖彼得堡,1911—1914)
第六章 戀人與詩人(彼得格勒,1914—1917)
第七章 流亡滋味(克里米亞,1917—1919)
第二部分 歐洲
第八章 成為西林(劍橋,1919—1922)
第九章 重組(柏林,1922—1923)
第十章 繆斯登場(柏林,1923—1925)
第十一章 流亡生活場景(柏林,1925—1926)
第十二章 異想(柏林,1927—1929)
第十三章 作家納博科夫
第十四章 《防守》
第十五章 反與正(柏林,1929—1930)
第十六章 明亮的書桌,黑暗的世界(柏林,1930—1932)
第十七章 遠景(柏林,1932—1934)
第十八章 翻譯與轉換(柏林,1934—1937)
第十九章 奔波(法國,1937)
第二十章 《天資》
第二十一章 窮困(法國,1938—1939)
第二十二章 尋找出路(法國,1939—1940)
致謝
文獻目錄
索引
譯後記
媒體評論
這部傳記精妙絕倫,作者才思飛揚,令人手不釋卷,欲罷不能。布賴恩·博伊德的這部著作用力甚勤,堪比納博科夫那本百科全書式的譯著——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它是難以企及的範本。
——麥可·德達,《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
博伊德先生天資過人,他出色地將生活與文學融為一爐……在這部令人難忘的傳記中,他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我們所知甚少的納博科夫……作為傳記,(博伊德的)著作將難以逾越。這是對傳主一生的準確描繪,是對那個時代的忠實寫照。
——謝爾蓋·達維多夫,《紐約時報書評》
當今時代,出色的文學傳記屈指可數,這部傑作無疑將首屈一指……布賴思·博伊德有精彩的故事可講,他講得很精彩。
——希爾頓·克拉默,《華爾街日報》
一部(文學傳記)傑作,傳記家與偉大作家從此形影不離,相得益彰。
——約瑟夫·科茨,《芝加哥論壇報》
博伊德博學多才,因此作為納博科夫的傳記作家,他當仁不讓……他對一個生命的敘寫無比“真實”,他對俄國文學的理解無比全面,他對納博科夫研究的幫助不可或缺。
——簡·格雷森,《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編輯推薦
《納博科夫傳俄羅斯時期(套裝全2冊)》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洛麗塔”傳奇的締造者,馳騁於俄語、法語、英語三度空間的文學大師,何處才是其精神家園?
三十年來最權威的納博科夫傳記
一部二十世紀的政治史、精神史
納博科夫傾斜著文學的層面,傾斜著生活的層面。閱讀納博科夫,我們不再只是觀察人物之間的戲劇,我們自身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變成了主人公:讀者面對著作者,心靈面對著它的世界。在他最優秀的作品中,納博科夫讓我們認識到,他的世界不是現成的,而是當著我們的面在生成,我們參與創造越多——觀察細節,將各部分聯繫起來,努力解決它們提出或隱藏的各種問題——這些世界就變得越“真實”,同時,這些真實就越可能成為通向進一步真實的台階。隨著發現不斷增加,激動的脈搏會跳得更快,驚奇感會更強,直到最後,我們站到了新真理的門檻前。
納博科夫說,那就是事物的本來面貌。只要我們不是想當然地去看世界,我們就會發現生活核心潛藏著的藝術品質,它引領我們深入這個世界,讓我們不斷接近創造的神奇,也許還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承諾,我們可以與所了解的一切建立新的關係。
——布賴恩·博伊德
文摘
1982年起,我開始偷偷地研究納博科夫在俄羅斯的生活,1990年我第一次訪問了這片國土。戈巴契夫的時代,蘇聯經歷了劇烈的變革,1986年起,納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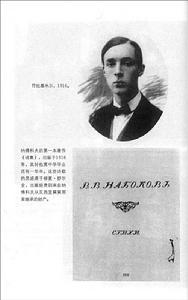 插圖
插圖像納博科夫一樣,我從未去過中國,不過我希望這種情況不久能得到改變。在講授英國文學課程時,我會在導論部分夾帶一些關於托爾斯泰和李白的介紹。納博科夫關心他在俄國讀者心中的地位,但對中國卻考慮不多,只是在《天資》中,他讓康斯坦丁·戈杜諾夫一車爾登采夫在天山、南山、戈壁、長江上游、拉薩、阿爾金山和塔克拉瑪乾地區做過蝴蝶科考工作。20世紀二三十年代,納博科夫的一些作品曾在俄國流亡者的中心之一哈爾濱出版。西蒙·卡林斯基是第一個發表研究《天資》著述的美國學者,也是納博科夫書信的第一個編輯人,他就是在哈爾濱長大的。30年代時卡林斯基還是一個小男孩,但已經愛上納博科夫的小說。1919年以後,納博科夫再也沒有踏上俄國的土地,不過在想像中,他最後一部完成了的小說《瞧,這些小丑!》的主人公瓦季姆·瓦季米奇卻回去了。在回憶中,他的青春歲月才智平平,沒有什麼獨創性,詩性而又浪漫。他迷戀的是現成的經驗,迷戀的是現成的詞語。等他走出這段歲月後,納博科夫獲得了一些教訓:發現自我屈服後,對習慣有了更強烈的恐懼;他對那種宣稱追求藝術、因此可以對所選擇的真實生命恣意妄為的做法感到厭惡;他認識到易燃的情慾和永不熄滅的初戀之火有著本質區別。是的,與後繼者點燃起來的詩情一樣,柳夏激發的詩句也一樣沒有什麼創造性,但在與她的交往中,納博科夫獲得了一種感情的光與熱,這些光與熱將在未來五十年的散文寫作中不斷閃爍、釋放。
納博科夫對柳夏的熱情無助於他的學習。雖然小孩子時他是數學奇才,但1907年的肺炎讓他失去了這種特殊天賦,他在捷尼謝夫的數學……
後記
一般說來,後記往往有點像影片的片尾,生動活潑的畫面忽然間變成了單調的、機械滾動的字幕,儘管製片人對演職員、贊助商等種種信息詳細交代,唯恐遺漏,但觀眾大多早已起身離場。那些依然能夠安靜地坐在池子裡,聽著與主題相關或無關的片尾曲,望著一排排滑過去的名字,直到“劇終”的字樣在讓人覺得晃眼的燈光照耀下消失於銀幕才走開的人,要么是“利益攸關方”,要么是真正的影迷,要么就是果戈理筆下那對著馬車軲轆發獃的農民。不過,照納博科夫的說法,發獃是“生存還是毀滅之沉思的原始形式”。經過20個月的艱苦努力,完成了這部對本人而言體量比較大的譯著之後,我其實是有許多話要說的。從2007年9月3日魏東先生打電話跟我商談此書的翻譯至今,家事國事、身內身外,我親歷、目睹了太多的離合悲歡,失望希望。這樣,翻譯《納博科夫傳》於我除了是一種久存的心愿與責任外,有時還是一種寄託,甚至是一種強迫性的情感轉移。坦率地說,我對這本傳記非常用心,翻譯過程中,為之歌哭淚笑的時候也有過。我沉湎很深時,妻子都有些擔心,她逼著我跟她到超市去換換腦子,可在我眼裡,那些促銷的廣告牌、琳琅的貨架和推著購物車在商場晃悠的顧客都不真實,倒是柏林街頭的電車、波羅的海的海灘、費奧多爾和濟娜站在朦朧路燈下的形象讓我覺得親切,仿佛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