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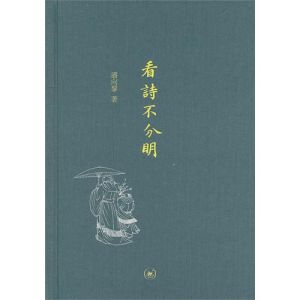 封面
封面目錄
 書摘
書摘看詩不分明——寫在前面
可忍,可不忍
不可忍
愛情和人生,誰短誰長?
空氣之美
從陰山到三峽到綿州
珠璣與文章
車·馬·三生石
落霞·落英·夜半鍾
男女還是君臣?
知之不如不知
中毒記
梅花訊息
人間有味
致命的江南
部分內容
詩是空氣,詩是呼吸【1】讀關於唐詩的各色文字,常常驚訝於詩歌在當時生活中的地位。
雖然早就從專家們那裡學到、記取了這樣的“梗概”:當時科舉舉士,李世民在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高興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加上以詩取士,使得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幾乎都是詩歌作者。詩歌作者群空前廣大,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和尚、道士、妓女。詩歌影響遍及社會各階層,元(稹)白(居易)之詩傳誦於“牛童、馬走之口”、“炫賣於市井”之中,寫在“觀寺、郵候牆壁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競習。(參見余冠英、王水照《唐詩發展的幾個問題》及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
但是在和一些“情節”相遇和重逢時,仍然感到吃驚,才知道自己的想像和事實相比是何等蒼白。懷著這種愉快地“受打擊”的心情,一路追尋,終於發現,在那個時代,詩歌是空氣,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詩歌是呼吸,所有的人每時每刻都不能停息。
看“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這句。詩本身質樸無華,談不上出色,但是它所揭示的歷史真實卻讓我驚嘆。
這齣自白居易的《藍橋驛見元九詩》。元和十年,白居易從長安貶江州,經過藍橋驛,看到了八個月前元稹自唐州奉詔回長安路過這裡時,在牆上留給他的詩。白居易出長安和元稹回長安,有一段道路是一致的,所以既然在一處看到了元稹留給他的詩,後面沿途的許多驛站,可能還有元稹的題詩,白居易就每到一處格外留心。讓我驚嘆的不是這兩位詩人間的友誼,不是他們命運的沉浮,而是當時那種交流的方式和詩作發表的自由度。試想:長路迢迢,一路行去,每個驛亭都有詩,墨痕歷歷,詩韻淋漓,在牆上,在柱子上,在你目光所及的每個角落。其中有你的朋友的作品,甚至就是留給你的。這是多么激動人心的事情。
而白居易到了江州之後,還有新的發現。他在給好友元稹的信里說:這次我從長安到江州,走了三四千里地,一路上經過許多小旅店、鄉村學校、寺廟,還坐了客船。這些建築,這些船隻,到處都題著我的詩。(這就不是作者自己題上去的,而是別人將白居易的詩寫到牆上和柱子上了。)他還說:路上遇到的人,不論男女老少,有的是體力勞動者,有的是出家人,他們都能背誦我的詩。詩歌在社會上就是這樣受歡迎,這樣朝野傳頌,無遠弗屆。
詩的太陽照徹,詩人之間容不下任何“相輕”的陰暗,他們是那樣光明地互相欣賞和敬慕。李白是這樣看孟浩然的:“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是這樣看李白的:“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而杜甫自己擁有眾多鐵桿“冬粉”,其中詩人張籍愛得別出心裁,唐《雲仙雜記》中說他居然將杜詩當藥喝。具體“製法”是:拿來一卷杜詩,燒成灰燼,然後調了蜜製成蜜膏,經常衝來喝,他說這是為了“令吾肝腸,從此改易。”真是痴得可愛。
離風雅、教化最遙遠的階層呢?那就看看強盜吧。
詩人李赦有一首《井欄砂宿遇夜客》:“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漢夜知聞。他時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這首詩是獻給強盜的。
《唐詩紀事》記載;李涉曾到九江,在一個渡口遇到強盜,問他是誰,隨從報了他的名字,強盜首領說:“若是李涉博士,我們就不搶他的財物了,久聞他的詩名,給我寫一首詩就可以了。”李涉就寫了這首詼諧的詩,說“看來我也不必想隱姓埋名了,連你們都知道我的名字,何況如今世上一半是你們這樣的人了”。當時那個強盜首領很高興,反而送了許多東西給李涉。
無法無天、殺人越貨的綠林好漢尚且如此尊重詩人,詩人在當時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詩是空氣,詩是呼吸【2】
不要說朝野上下和“天下英雄”(所有讀書人),就是出家人,也和詩割不斷緣份。
因為不可能以之換取功名、博取前程,所以僧人做詩便多了“為藝術而藝術”的非功利色彩。
詩人駱賓王跟著徐敬業反武則天,還寫了著名的《討武曌檄》,武則天讀了吃驚地問:“誰寫的?”然後說:“宰相怎么會錯過這樣的人才?”後來敬業兵敗,他不知所終。傳說他隱於靈隱寺了。宋之問游靈隱寺,得詩兩句:“鷲嶺郁岧嶢,龍宮鎖寂寥”,兩句之後卡殼了,這時有位老僧續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氣勢磅礴,點石成金。宋之問大吃一驚,到第二天早上再去找他,已經不知去向。有知情的僧人說破:“那是駱賓王。”這位大詩人一時技癢,就暴露了行藏,只得又去別處藏身了。
比半路出家的駱賓王純正的僧人,寫詩的也大有人在。皎然、貫休、齊己是其中的代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一這樣評價唐代的詩僧群落:“其有集傳於今者,惟皎然、貫休及齊己。皎然清而弱,貫休粗而豪,齊己……風格獨遒。”清人則列出了這樣的名單:“唐釋子以詩傳者數十家,然自皎然外,應推無可、清塞。齊己、貫休數人為最,以此數人詩無缽盂氣也。”(賀貽蓀《詩筏》)這數十家中應該還包括寒山、景雲。
皎然是南朝詩人謝靈運的十世孫,在當時詩壇影響很大,韋應物、劉禹錫、陸羽等都和他結交。貫休因為“一瓶一缽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之句,被人呼作“得得和尚”,他不畏權勢,屢召怨恨。齊己的《早梅》是名作,不過這位詩僧更難得的是對詩的價值的自覺:“自知清興來無盡,誰道淳風去不還?三百正聲傳世後,五千真理在人間。”(《詠詩寄知己》)
不要說人,就是唐代的鬼都對詩念念不忘。
“大曆十才子”之一的錢起在省試(各州縣貢士到京師由尚書省的禮部主持的考試)時面對“湘靈鼓瑟”這個命題,寫了一首詩,最後兩句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深得試官嘉許,贊為“絕唱”,被擢為高第。但這兩句的原創者不是他,而是鬼。這是錢起在一個月夜聽見的“鬼謠”,在考試時看到詩題里有一個“青”字,想起了這兩句,就把它寫進詩中,果然不同“凡”響。這鬼,真正是才華過“人”啊。這在《舊唐書.錢徽傳》有記載(錢徽是錢起之子,也是晚唐著名詩人)。
說到鬼神不免淒清,那就說個熱鬧的吧。李白沉香亭奉旨作詩實在太爛熟了,我更愛這一則:旗亭唱詩畫壁。
薛用弱《集異記》記載: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來到旗亭(酒樓),一起小飲。後來來了一群梨園伶官在這裡舉行宴會,然後是幾個正當妙齡、打扮奢華的歌女出場,她們唱起了當時流行的詩歌名作。王昌齡等人就偷偷約定:“我輩各擅詩名,一直難分勝負。今天可以暗中聽她們唱什麼,誰的詩被唱得多的,就算贏。”第一個歌女唱了,是:“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就在牆上畫了一痕說:“一絕句。”一會兒有人唱:“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云居。”高適就畫一痕說:“一絕句。”接著又一個唱道:“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就又畫一道說:“二絕句”。王之渙並不著急,就說:“這幾個都是沒品位的,所以唱這種下里巴人的貨色。”他指著其中最漂亮的,說:“等這個唱來,如果不是我的詩,我就終身不敢與你們爭衡;若是我的詩,你們就該奉我為師。”大家笑著等下去。那個最漂亮的歌女終於唱了,輕啟朱唇,鶯聲嚦嚦,唱的不是別的,正是:“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果然是王之渙的名作《涼州詞》。王之渙鬆了口氣,揚眉吐氣地說:“看,你們兩個鄉巴佬,我難道是瞎說的嗎?”三位詩人不禁一起大笑起來。
多么奇妙的聚會。多么輝煌的牆壁。多么幸福的詩人。
詩是哭,詩是笑,詩是空氣,詩是呼吸。這一切確實發生過,那個朝代,叫唐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