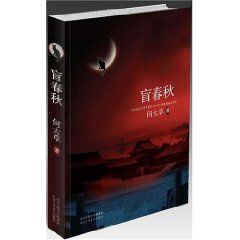 0
0基本信息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第1版(2009年5月1日)平裝:335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7530209736,9787530209738
條形碼:9787530209738
商品尺寸:23.4x16.8x2cm
商品重量:522g
ASIN:B002BNKOQY
內容簡介
《盲春秋》講述了:美國漢學家宇文長安,從九十歲的修道士西芒手中,獲得一部殘缺不全的神秘手稿。手稿於二百多年前,由傳教士從中國帶到歐洲,一直秘藏在葡萄牙寶萊塔修道院。宇文長安邀請精通歷史的中國作家一同破譯、整理。經十二年的考據、查證、探訪,手稿終於逐一還原,一段塵封了三百六十年的歷史真相大白:大明帝國覆滅的廢墟中,傳教士救出一位雙眼燒瞎的女子,竟是末代公主朱朱!隱姓埋名45年後,她開口說話,向史學家講述父皇崇禎的身世謎團、他與李自成的法華寺密晤、王朝轟然坍陷的真實內幕。
編輯推薦
《盲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懸疑大作!葡萄牙寶萊塔修道院發現一部神秘手稿!
竟是明朝末代公主朱朱的口述實錄!
聽盲公主講述大明王朝衰亡之謎!
媒體推薦
首部長篇歷史懸疑小說,盲公主口述歷史——葡萄牙保萊塔修道院一部殘缺不全的手稿,揭開明王朝傾覆的驚天秘密,真相是我們用手掬起又從我們指縫間漏走的水。《盲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懸疑大作!葡萄牙寶萊塔修道院發現一部神秘手稿!竟是明朝末代公主朱朱的口述實錄!聽盲公主講述大明王朝衰亡之謎!
作者簡介
何大草,本名何平,1962年夏出生於成都,祖籍閬中,1979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成都晚報》任記者多年。發表中短篇小說一百多萬字,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刀子和刀子》、《所有的鄉愁》、《我的左臉》,小說集《衣冠似雪》等。根據《刀子和刀子》改編的電影《十三棵泡桐》獲2006年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審會特別獎。現執教於四川師範大學中文系。
目錄
代序長安來信第一卷木樨地
第二卷午門以深
第三卷我在地上的父
第四卷俊仆
第五卷闖入者
第六卷櫃裡乾坤
第七卷李自成
第八卷吳三桂
第九卷春月
附錄:另一卷帶刀的素王
附錄:另二卷二十七個逃亡的人
代跋自無定河
序言
何先生:您收到的這封長安來信,並非來自兩千年以前,而是來自七千英里之外:我即長安。
確切地說,我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stephenKing,漢語一般譯為史蒂芬·金,但作為漢學家,我更喜歡別人稱呼我的中文名字——宇文長安。我目前任教於紐波特大學歷史系,學術方向為漢唐的蠶桑業及其輸出。如您所知,長安是漢唐的偉大都城。我曾兩次造訪長安故地,時令均在寒露前後,所謂“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心情是百感交集的。當我說出“我愛長安”時,請您不要誤會,這絕非病態的自戀,正相反,是對無法重現的美好年代的緬懷,“長安”是那個年代中的絕色。
我和中國淵源極深,甚至早於負笈哈佛東亞文化研究所的歲月。從廣泛的譜繫上說,現主持哈佛東亞所的孔飛力博士是我的同門師兄,他研究乾隆朝妖術大恐慌的力作《叫魂》,在漢學界卓有影響,還很可能在中國翻譯出版。相比之下,我著作寥寥,不敢以“述而不作”自我辯解,實在是生性懈怠,頗近清末之旗人,常以茶、酒自娛,佐以中國古典詩詞,在風月中快哉。三年前我決意撰寫論文《蜀錦考》,查找的文獻厚可盈尺(抑或三尺),奈何庸碌度日、蹉跎時光,迄今未能完成其中一半。先師墳草數青,墓木已拱,我每念及愧對師門,總汗顏無以自容。師兄諸人視我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卻又不忍痛責,只能溫言相勸,漢學博大精深,如燦燦寶山,汝已在赴寶山途中,切莫空手而回,云云。種種教誨,使我感動之餘,數度下了決心,終究是要寫完《蜀錦考》。但是,建議我不揣冒昧給身居錦官城的您寫信的,卻是我的女友,她姓唐,芳名歡君,——而且,這封信與我的論文並沒有關係。
歡君籍貫重慶沙坪壩,出身中醫世家,1989年從四川大學哲學系退學後赴美,打工之餘,不倦於旅行、求學。有一年夏天我去大峽谷旅行,旅途中暑,上吐下瀉,躺在汽車旅館奄奄一息。有個陌生女孩給我扎了針,那些可怕的、有靈性的針,銀光閃閃,刺破我的肚子,快意無比,讓我感覺撈回了一條命。這個女孩即是歡君。我們的志趣相距甚遠,卻相談甚歡,遂攜手而回。她現為紐波特哲學博士候選人,攻叔本華和尼采。今年春節她回重慶省親。順道去成都的母校拜訪師友,在歷史系彭邦本教授——您的老同學——家作客時,偶然翻到您惠贈他的小說集《宣和以遠》,對其中描寫李清照南渡的一部中篇,印象頗深。返美後,她向我聊起您和您的作品,從而知道您從川大歷史系畢業後,在成都做過十餘年記者,後來專事小說寫作,現在是南方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駐校作家。歡君還特意說明,她和您可稱“校友”。校友,在我看來,即意味著某種程度的信任。這一點十分重要,和我將在下文中提到的一部來歷複雜、命運多舛的手稿有關。
說到我的女友,請允許我多一點嘮叨:歡君雖自我預設為女哲學家,但與弗蘭納里·奧康納《善良的鄉下人》中的女哲學博士歡姐(Joy)殊無共同之處,歡姐尖酸、無趣、邋遢,而且拖著一條假肢;而歡君雖著力於悲觀之哲學,卻長於游水、登山,性情活潑、幽默,喜俳諧、滑稽,最上癮的電影莫過於伍迪·艾倫和周星馳(私下也翻一翻拉辛和高乃依)。她不僅敦促我給您寫信,為我的中文作細緻地潤色,還提醒我在中文裡濫用“親愛的”、“尊敬的”將顯得有一點肉麻。故而,何先生,我只稱呼您為“您”。若有不敬之處,還請見諒(而責任在歡君)。
關於那部手稿,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
去年聖誕節前夕,我奉母令偕歡君前往葡萄牙北部,探望在群山環抱的小鎮保萊塔修道院擔任神職的舅公吉爾伯托·西芒。舅公已過九旬,個子又高又瘦,一頭紅髮,臉色蒼白,極符合中國古人對紅髮夷鬼的想像。
後記
長安兄,您好。從收到您的第一封來信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二年。十二年前的九月末,我正在北京採訪一個會議。閒來無事,和一個同行去逛紫禁城。我們是從天安門的門洞穿過御道,經午門進入故宮的。那天不是周末,旅遊季節也過了,故宮中人跡寥寥,在午後的陽光下,有些枯寂蕭索的味道。後來我們從神武門出去,又登了景山。景山的樹木正達到深秋前的極盛;有一棵槐樹前立了牌子,說這是崇禎自縊處。但從前的那棵槐樹沒有了,現在是新栽的,也就是說,是贗品。我還是在它面前照了相,穿著黑色的體恤,胸前有一大塊紅綠凌亂的圖案。再轉一條彎曲山道,看見大石上蹲了個瘦得如猴的老漢在拉二胡,琴聲割耳,難聽死了。我們走攏,剛好他一曲拉完,主動問我們,從哪兒來的?我們說,四川。老漢就慈祥地虛了眼睛,又問,四川人民能吃飽嗎?同行點點頭,說,托福,還能吃飽……老爺子,您的琴好像有問題。老漢笑笑,說,是有點問題,自己動的手,就花了十元錢。
從北京回來沒多久,我就收到了您的信;後來,就是一整箱的手稿複印件。這十二年中,我幾乎天天都在後悔,不該輕率地答應你們。我本該想到的,我的能力難以勝任你們的重託。而參與這部手稿的整理,不啻就是一場災難;至少,也是一場沒日沒夜的噩夢。這部手稿不僅混亂,而且浩繁,仿佛還在不停地生長出來……每天,當我一展開這堆字宇清晰,而語句狗屁不通的紙張時,我腦子裡就會響起北京老漢割耳的二胡聲。我絕望地想過,它沒有完成,是因為它注定就無法被完成。至少有兩次,我動了把它們付之一炬的念頭,那一刻,我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不相信它的煙火也會無窮無盡。但是,一次我搜遍家裡的桌面和大小抽屜,都沒有找到打火機。另一次,我從小區的園丁那裡借到了火柴,在擦燃火柴棍的一剎那,天空一聲雷鳴,大雨就落了下來,澆濕了火柴棍,也澆滅了我心頭的惱火。我嘆口氣,我承認,手稿既然能夠幸免於難,大概真是另有安排吧。於是,在把它們踢入角落十天、半月後,我又會把它們重新放上案頭,錙銖計較地抄抄寫寫,圈圈點點。當然,我也不能不承認,能夠任由它拖累我十二年,不僅在於我當初的允諾,也不僅在於我的恐懼,還因為整理的過程也在零星而又持續地帶給我一些歡悅。我就像一個盲詩人(你的歡君曉得他是誰)描述過的倒霉漢學家(他湊巧和您一樣都名叫史蒂芬),用半輩子的光陰來考索被遺忘的迷宮。最後,他和我一樣,對著各自為之榨乾心力的東西說:“它沒有完成,然而並非虛假。”結局是,他被一個德國華裔間諜的最後一顆子彈擊斃了。而我,這十二年來,仿佛為了逃避某種追擊,或剛好相反,為了尋找與手稿有關的某些蛛絲馬跡,而攜帶著它四處旅行。如您所知,我是南方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駐校作家,除了課程和薪水這兩樣不多,卻有大筆閒置的時間自由支配。我跟所有成都人一樣,與生俱來地惰性、懶散、閒適,還有輕度的幽閉症。而為這部手稿所展開的逃避與尋找,把我從蝸居的小屋、沙發、床上趕出門去,輾轉於一個個車站、碼頭,以及數不清的城市、村莊、客棧……此時此刻,我就坐在北京北郊、無定河畔的一戶農家院落里給您寫信。頭上兩棵白楊披滿盛夏的陽光和有力的風,樹葉亮得炫目並發出颯颯之聲。從打開的院門看出去,是幾塊瘦瘠的菜畦、瓜地、豆棚,長著青草的河灘,寬闊河床上的幾線淺水。生機尚存,但一切都在於涸。無定河當初是以它的水勢洶湧聞名的,就像它的名字,喜怒無常,恣意橫流。康熙三十七年,才為了馴服這條河流而堅築了長堤;康熙皇帝還用御筆改寫了河名:永定河。許多年過去了,不管是叫它“無定”還是“永定”,它只能是眼前這個樣子了,如一個男人被熬乾後趴在床上,再沒什麼氣力了。我選擇無定河邊完成手稿的最後修訂,是我覺得這兒是故事落幕的最為合適的地方。
文摘
第一卷木樨地○一
你說你要重寫一部歷史,這我幫不了你。
今年穀雨過後,我的臉就像現在這樣,搭了一塊面紗,去法華寺海棠院喝了一回茶。海棠是盛放過的,這會兒都已經快謝了。院裡坐滿了喝茶的客人,稍遠處的一把高凳上,有個河南後生蹲在上面說評書,關雲長千里走單騎。我身邊有人在談論剛剛南巡歸來的康熙爺,他說會稽的老道獻給這個爺一個肚臍生香、弱骨豐肌的女子,夜夜侍寢,弄得龍體歡悅。他說完,四下是一片的嘆息,就連老禿驢都在感慨,“阿彌陀佛,論調和陰陽,還是牛鼻子更有辦法的。”一個老者,中氣飽滿,聽他的聲音,就猜得到是鶴髮、尖嘴、猴腮的,還一定食過大明的俸祿,至少是做過四品的言官,他接過禿驢的話來,拍著茶桌說:“本朝的祥瑞,就由這香氣可見了。”我差點把一碗茶水,潑在了他的老臉上:這話,你該拿到太和殿上去說罷。
可我長長地吸口氣,甚么都沒說。海棠是在謝了,樑柱和磚的縫隙里,卻還留著讓人昏沉沉的海棠味。距我上次來法華寺看海棠,看一個人,已經整整四十五個年頭了。世道變了,人心變了,大明的言官,也剃光半個腦袋,屁股後邊拖了長長的辮子……只有海棠的味道,禿驢們的袈裟,鐘磬的鏗然一響,還和四十五年前沒有兩樣,也和一千年前,是一模一樣的。冰涼的銅,石頭,瘦嶙嶙的狗,有時候是比人還要有心有肝的。那天,在我出了山門要上轎時,有一個年青人跟出來,向我施禮。他說他是一個畫家。他懇請我答應讓他替我畫一幅肖像。他說他可以畫得非常逼真,讓我如對一面鏡子。我說:“一個女人,已經很老了,她還需要對著鏡子乾甚么?”畫家改了口,說他可以比照現在的我,畫出十六歲時候的模樣。“天!”我笑起來,他被我沙啞的笑聲驚蒙了,笑聲就跟成群的蝙蝠似的,有力地拍打著牆壁和他本人。後來,我把笑聲收了,告訴他:“你所說的一切,都毫無意義,你沒有看到嗎?我是一個瞎子啊。”
不需要我把這話向你重複一遍罷,年青人。你們不傻,都有著夜貓般的眼睛,狗一樣的鼻子,我隱姓埋名四十五年,還是被你們找到了。告訴我,從我身上咬下一口肉,真的可以讓一頁紙,或者很多的紙,傳之不朽嗎?你野心勃勃,心思過人,在這個年紀上,就寫出了有關明清換代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兩部史書,這是不錯的。兩部書,據說都在士林中偷偷傳閱,可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這也很不錯。寫了書,沒人肯讀,就自己咕噥,說要收起來,藏在屋樑上,留給百年之後的聖賢,真是打腫臉充胖子,自取羞辱。聖賢基本上是不讀書的,他們一日三省其身,也就是說,大多時候都在想事情,所謂面壁思過,就是對著牆發獃。哪天牆塌了,他們就破壁出來,功德圓滿了……這都是瞎扯!你寫的史書,我讓人給我念過,念了幾百個字,也許再多一點罷,我就已經厭倦了,像曬過的海棠葉子,沒了興致了。你寫了很多人,寫得不算差,但還是簡單了。要記住,寫在紙上的人,總是沒有活過的這個人複雜。大唐的時候,有個叫惟儼的禪師,也就是個老禿驢,他說過一句話,身體力行的是戒律,嘴裡講出來的是說法,留於心中的才是禪。這是說得不錯的。禪是這樣,還有別的東西也是這樣,譬如,記憶,愛和恨。噯……世上就沒有一支筆,能夠把記憶完全地掏出來。你也不能,計六奇。
十天前,我收到你第一次遞進來的帖子,“計六奇”,的確是讓人過目不忘啊。到現在我都還在琢磨這三個字……你父親是個很有意思的人,大概是個沒有功名的書生罷,抑或,是無錫捏泥人的匠人,總之,活著心有不甘,也洞見了世情機關密布,才給你取了這么個名字?喔,是的,一條河溝里的魚,要蹦人大澤去討吃的,光有力氣和膽量是不夠的,要拿鼻子嗅,要比心機深。我喜歡上你的名字了,也不討厭你這個人。比起木訥的男人,甚或如木偶般滑稽的角色,還是野心勃勃的青年比較能討我的歡心的……好罷,我可以跟你講講我,可我講出的話,真可以被稱做歷史嗎?我是始終如一相信自己的;你呢,你不要自己騙自己。
設若,我告訴你,大明萬曆三十二年,客奶奶入宮為後來的天啟皇帝做奶媽時,曾給他抱去了一隻貓。貓長大,卻成了一隻虎,使紫禁城鬧出了虎患來。你相信嗎?喔,你點頭了,這很好。我再告訴你,會稽老道獻給康熙的肚臍生香的女子,其實是一隻麝妖,你還相信嗎?哈,你猶豫了……你還可以多想想,想上半輩子再回答,也是不遲的。但是,如果你恪守“眼見為實”這個迂腐的誡條,又何必聆聽我這個瞎子的聲音呢?瞎子的聲音,來自沒有盡頭的黑暗,居於這黑暗中央的那個人,——噢,上天之子,並非人啊——他無時無刻地,還能讓我看到他消瘦的側影,深長的呼吸。嗯,你過來,再過來一點,我要你跪在我的膝前,握住我的右手。你有勇氣握住它嗎?這隻四十五年前,被火焰燒焦、像雀爪一樣的手,噁心罷……舔舔它、舔舔……對了,就這樣……噢,我的天,四十五年了!我守口如瓶,跟一個守身如玉的老節婦沒兩樣,卻讓你輕易觸犯了我的(一部分)秘密。計六奇,你這個小混蛋。
○二
我在地上的父,大明帝國末代的君王,崇禎、懷宗、思宗、莊烈帝……朱由檢,被撰寫歷史的人認定,已於崇禎一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拂曉時分,和他的貼身太監,自縊於煤山壽皇亭旁的兩棵槐樹上。父皇,死在了眾口一詞的記載中。對於這一記載,我是無話可說的。我對父皇的全部記憶,都停止於這個著名的拂曉前。拂曉前的某個時辰,也許是在幾次細雨的間隙罷,兩個黑衣、蒙面、禿頭的人悄然穿過紫禁城蛛網般的小徑,摸到了他的宮中,並匍匐在他的龍椅前。禿頭人的聲音蒼老、嘶啞,懇求父皇允許在他倆的保駕下,逃離到千里之遙的故都南京,統帥南方軍隊為捍衛大明江山作長期的抵抗。
這時候李自成的大軍已在京郊紮營。北京城籠罩著晚春時節憔悴的花香與遼闊的寂靜。從韃靼高原上吹來的陣風帶來了大面積的黃沙,由於路斷人稀,黃沙在街面上積成了一圈圈弧形的波痕。一部分富戶早已料到城破就在指日,裹了細軟遠走高飛。而更多的人家則關門閉戶,蟄伏在深巷宅院中茫然無措。父皇派出的最後一支維持帝國秩序的馬隊在正陽門一帶逡巡不前。你知道甚么是大軍壓境、孤城困守嗎,計六奇?全北京城的人都看到,桌上的一杯茶或者一碗酒,都因為李白成鐵騎的敲打而發出了輕微的顫抖。
那兩個禿頭人為了說服父皇,不停地拿額頭叩擊著地磚,咚咚有聲。血從他倆的眉心流下來,把蒙臉的黑紗分為可怖的兩半。但父皇只是長久地沉默著,用纖長的十指反覆地撫摸著龍椅的扶手。父皇的目光越過匍匐在腳跟前的禿頭人,若有所思地眺望著紫禁城的黑暗。紫禁城今夜的黑暗,同十七年來的黑暗一樣,深色、稠密,渾無邊際……父皇抬起一隻手臂,甚至沒有看一眼禿頭人。他揮了一揮手,結束了他們之間並沒有開始的交談。他可能是說了兩個字,“去罷。”
禿頭人無望地轉過身去。就在他倆轉身的短促時刻,在一瞥之間,肯定看見了在燭影的邊緣、帷幄的下邊,露出兩隻紅色的繡鞋。當然,像他倆這樣有某種特殊技藝的夜行人,或許早在向父皇叩頭之際,就應該聽到了帷幄後面有人發出的絲絲鼻息。但他倆除了流血的眉心兩側,異常疲憊的眼睛,看不出任何的表情。他倆轉過身,像影子一樣地消失了。
躲在帷幄後面窺視的人就是我,父皇最寵愛的女兒。
我看見蒙面的禿頭人消失後,父皇仍一動不動地坐在龍椅上,仿佛從不曾有人打擾過他的冥想。今夜的燭火在靜謐中發出嘶啦啦的燃燒聲,照見父皇鬢角上的斑斑白髮。他的面容同禿頭人一樣,是疲憊的,而且烙滿了早到的皺紋。但與此同時,我又有了一些驚訝的發現:父皇的神情完全變了,就像一個離群索居、苦苦修行的隱士,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忽然都想清楚了。他的雙眼是平靜的和明確的,沒有了我所熟悉的那種迷惑與憂傷。
這一年,我說過,是崇禎一十七年,歲在甲申,夷歷1644年,父皇三十四歲,我一十六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