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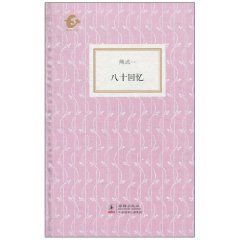 0
0精裝:159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32
ISBN:751100394X,9787511003942
條形碼:9787511003942
商品尺寸:18.8x12.2x1.6cm
商品重量:222g
品牌:海豚出版社
ASIN:B00495XWUC
內容簡介
《海豚書館·八十回憶》主體《八十回憶》含《代溝與人瑞》、《初習英文》、《出國鍍金去,寫<王寶川>》、《談談蕭伯納》四篇,最初分別載於1986年7月、8月、9月、10月《香港文學》第19、20、21、22期。內容基本涵蓋了作者一生的主要經歷,包括兒時經歷、交往的朋友、怎么學習英文、如何出國留學,以及用英文翻譯改編中國傳統戲劇《王寶川》的經歷,包括與英國戲劇界和漢學家的交往等等。除此之外,《八十回憶》還收錄了“外編”三則,分別是:《<天橋>中文版序》、《<大學教授>中文版序跋》、《<難母難女>前言》。這三部作品分別是他創作的小說、劇本和翻譯的劇本。《天橋》最初是英文寫作的小說,在英國美國出版,又陸續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捷克文、荷蘭文等在各國問世,後由作者本人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大學教授》是作者1939年用英文創作,以中國近代歷史為背景的話劇,在英國戲劇節上演,1989年在台灣出版其中文版。《難母難女》是作者非常敬仰的英國劇作家巴蕾的作品,二次世界大戰前作者譯成《巴蕾戲劇全集》因故未發表,1985年應《香港文學》雜誌之邀,將其中《難母難女》中文譯稿交之連載於《香港文學》上。編輯推薦
《海豚書館·八十回憶》是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目錄
八十回憶代溝與人瑞(3)
初習英文(9)
出國鍍金去,寫《王寶川》(23)
談談蕭伯納(46)
外編
《天橋》中文版序(73)
《大學教授》中文版序跋(86)
《難母難女》前言(147)
序言
俞曉群、陸灝和我,在將近二十年前就有過一次“三結義”。那時,我剛要“退居二線”,但是賊心不死,還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讓我結識許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資源。原單位的新領導不會不讓我再做點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輩的領導是不希望我再做什麼事的,我的願望會讓新領導他們很為難。誰讓我在過去一些年裡那么不會伺候老人家呢!這時我概括過自己的心情:出於愛的不愛和出於不愛的愛。我只能離開我鍾愛的原單位,同新結識的朋友們去“三結義”了。完全沒有想到,封建社會裡的自由結義形式竟然勝過我多年習慣的領導任命方式。我們的“三結義”居然越搞越熱火。沒有多少年,做出來的東西,無論質與量,都讓我驚喜不已。舉例來說,先是《萬象》雜誌;接著是《新世紀萬有文庫》,幾百本;後面來一個《書趣文叢》,六十來本……這些成績,都是我過去不能想像的。自然,這些書的問世,還得感謝許多參與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舉了。
那時“三結義”的“桃園”在瀋陽的“遼教”。以後時過境遷,我們的劉備——俞曉群——遷出瀋陽,於是,現在再次“三結義”,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對我來說是個新鮮事兒。但我知道海豚愛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給海豚一個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給天使一個擁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愛的饋贈…’海豚痛苦地低鳴。”
現在,解決海豚痛苦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來自黃浦江邊的著名漁人——陸灝。陸灝結識天下那么多能寫善譯的天使,他們會一一給海豚以深愛,以宏文,讓海豚名副其實地成為一條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頑強的魚——俞曉群領導下的出版大魚。
我遙望海豚的勝利和成功,樂見俞曉群、陸灝兩位愉快的合作,特別是讀到大量我仰望和結識的天使們的懷著深愛的作品。我高興自己現在也還是“三結義”中的一員,雖然什麼事也沒力氣做了。我今年七十九歲,能做的只是為人們講講故事,話話前塵。以後,可能連這也不行了。但是無礙,我不論在不在這世界,還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俞、陸的合作會有豐富的成果。遙祝普天下的天使們,多為這兩條來自祖國南北兩隅的海豚以熱情的支持!
文摘
一九五○年蕭伯納九十大慶,當時文藝各界的朋友二十七人,各人寫一篇文章,合出一本紀念他九十大壽的文集。我適恭逢其盛,也濫竽充數的湊上了一篇,聊附驥尾。我大意說:當年我到英國去的時候,私心中最大的願望是見三個人:一個是高斯華綏(JohnGalsworthy),一個是巴蕾,還有一個就是蕭伯納。高斯華綏在我到英一個月之內便去世了;那時正值巴蕾臥病在一家私人療養院中,不能見我;蕭伯納不久以前已經啟程到中國去了,假如他到中國去為的是看我,因此相左,那我就一點也不感覺失望,反而會更加自滿,可惜他回英和我見面時,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他到中國去看的最重要的目標是“萬里長城”!有一次,我偶然對一位朋友說,蕭伯納到中國去不是看任何人,而是看萬里長城,中國有好幾萬萬人,難道就沒有一兩個人值得他去看的嗎?我心中難免有一點氣憤。這位朋友善意安慰我說:這可以表示我既然來了倫敦,不在中國,便也無人值得他老先生一顧!假如這句話不是開開玩笑的應酬話,只要一星星的真實性,我都應該高興萬分了!可惜這純是開玩笑!不久之後,我就聽見國內的朋友們大吹大說:他們和蕭伯納大打其交道,說得天花亂墜,妙語如珠!可是我親自問問蕭伯納,他對於某某大作家,某某名教授印象如何?他慘然的搖搖頭,還說,他一個都記不起了!他說,其中只有一位仁兄對他的印象最深,此君彬彬有禮,禮貌極其周到,送了他一本書:這是他本人一本所譯蕭伯納的雙文對照盜印本。蕭伯納對於這位老兄恬不知恥的印象極深極深!蕭夫人那時在旁邊聽見了——她總是不離開他左右的。她馬上插口道,那不是在中國,那位先生是一位日本人。她可肯定中國不會有這樣無恥之徒。
另外可有一位老先生,蕭伯納應該記得他的。他們會面之事,雖非蕭伯納親口告訴我,其真實性卻可靠。在香港的盛大宴會中,有人向蕭介紹一位大教育家。蕭一面和他熱烈的握手,一面親切的替他禱告道:“願上帝保佑你,幫助你!”這一樁趣聞,傳聞極廣,有很多朋友,都詳詳細細的向我報導,大約中國教育界的圈子,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蕭伯納自己卻一點也記不起來了。
名人也有名人的困苦。無論甚么人都認識你,知道你的一切!可是你絕對沒有可能去認識他們的一小小部分!其實他們並不真認識你或去知道你,他們只是自認為知道你,這卻更糟,於事無補。以蕭伯納而論,他可以算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了。關於他的事,早已出版了好幾十套書——其中還有一本“字典”,一本墓志銘(那時他還健在,並沒有死。)再說各報紙各雜誌上所登他的趣文雜事,更是不計其數了。話又要說回來,一個作家,生平著了幾十本書,其名仍不見經傳,還要他自己去寫他的自傳,也有他的苦惱。我認識幾位作家,他們經常雇用公共關係宣傳員,替他們鼓吹宣傳,我們中國大人物,要想揚名千古,只須請一位當代大文學家,替他寫一篇小傳,就好像請一位大畫師,替他畫一幅全身真容一樣。寫小傳,不比畫相,不必要本人參與,只要他自己,或去由他的家人,把他的生平事實,擇其中要想流傳後世的,詳詳細細記下來。大文豪根據這些材料,運用他生花的妙筆,改寫成一篇可歌可頌的不朽傑作,易如反掌。據說有一位惡作劇的文人,替人寫小傳時,競將來稿一字不改,照樣全抄,他自己只加上一句:說某某先生生平事略,根據其送來稿件如下。這真叫人無可奈何!假如有什麼大人物要請蕭伯納寫小傳,那才有意想不到的妙文章可看或可讀,或者是不可卒讀呢!
有一位名滿天下的大聞人,據說全世界的人可大別為兩種:一種是知道他的人,一種是不知道他的人。拿這方法來用在蕭伯納身上,並不合適。比較合適一點來講,當今全世界的人,可大別為兩類:一是喜歡他的人,一是不喜歡他的人——現在世界上哪兒還有不知道他的人呢?凡是看過他幾十齣戲的人,讀過他幾十本書的人,自然而然會覺得和他簡直是老朋友,提起他來會用他的名號而不用姓氏了。所以大家都稱他為G.B.或G.B.S.!英國有一位專欄記者,對任何人都是稱他們的小名或呢名。如稱首相邱吉爾為“溫尼”女議員亞思多夫人為“蘭西”,他對蕭伯納則不稱他為“喬治尼”或“伯尼”,可見他對蕭老還有幾分尊敬之意。
有一次,巴蕾突然問我道:“你常常去看蕭嗎?”蕭字和戲劇同音——台灣時髦作家譯為“秀”——我當時愣住了不知何意,還以為他是問我常常去看戲呢。他補充道:“我猜想蕭伯納一早醒來,高舉雙手,大聲叫道:妙哉妙哉!我就是蕭伯納!”——這表示他自鳴得意:“我就是大名鼎鼎的蕭伯納”——這句話也不能算稀奇,有許多巴蕾的朋友也會認為巴蕾一早醒來,也會如法炮製!我平心而論,假如有人發覺他一切成功,萬事已登峰造極,就難免有這種感覺。處處得意,事事順心,自己對著自己揚眉吐氣,是可原諒的。
當然,攻擊蕭伯納的人也不少,也許現在的作家,誰也沒有他所受的攻擊那么多。前面我提到,早已有人替他出了一冊“墓志銘”,我想尚在人間的作者,誰也沒有享受過這樣的特殊光寵!
好像大家都發現了,只要你去攻擊攻擊蕭伯納,你馬上就會受人注意。假如他回敬你一下,那是你鴻運高照,你從此之後,在文壇的地位就此奠定了基礎。未出名的作家,就把此道為進身文藝界的不二法門。凡在大庭廣眾之中,登壇發言之人,沒有一個不把蕭伯納這個名字,做他們救駕的法寶的。假如觀眾有一點疲倦的現象,注意力略見散漫,只要他們引述一兩句他們老朋友蕭伯納的妙語,全場的空氣馬上大不相同。你所提的妙論,不一定正確,也許你竟可以胡造一兩句,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大家的興趣就來了。
當今文藝界的圈子之內,有形無形中有一兩個不言而喻的秘密黨派,雖然沒有明確的正式組織,但是它們通行於全世界各國各地,我真不知道它們是怎么來的。他們黨同伐異,每逢到了一個新同黨,群起而護之;有了敵人,群起而攻之。他們真講義氣,真不講道理,令人無可奈何。比方說,所有的某派作家,你捧我,我捧你,那怕他們彼此既不相識,也不曾讀過彼此的作品,照樣攻守同盟,決不放鬆。成名的老作家,夸譽初出茅廬的後進。愛爾蘭的作家,人數比不上某派作家,也和他們如出一轍,常常由他們的老前輩,推出後起之秀,宣揚培植,愛護備至。當然,要是新作家果然不錯,後來他自然也會成名。但是偏偏有些莫名奇妙的怪東西,叫人無法卒讀,惟他們老前輩也把他們說得天花亂墜,所以使得我發生了一種特別反感,我以後再也不相信他們的瞎吹瞎捧了。以後對於這種書,再也不敢問津了。唯有蕭伯納一人是一個例外,他早年從沒有得到他同鄉——愛爾蘭人——的恩惠,後來也沒有去培植同鄉。至少我希望他以後決不要去為了同鄉的緣故去吹捧新人。說也奇怪,他同鄉對他的批評,倒是毫不客氣,他也根據禮尚往來的明訓,不留餘地的回敬一番。我並不是鼓勵內戰的人,文學批評達到了最高峰時,正是我生平認為讀到最痛快的妙文難得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