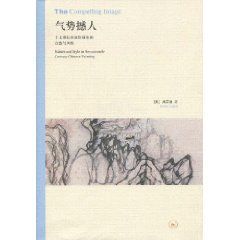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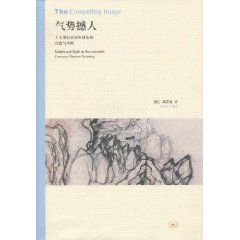 0
0外文書名:ThecompellingImage
叢書名:高劇翰作品系列
平裝:301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9787108030214
條形碼:9787108030214
商品尺寸:24.4x17x2cm
商品重量:581g
ASIN:B002NEFBVE
內容簡介
《氣勢撼人》講述了:高居翰(JamesCahill),1926年出生於美國加州,曾長期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藝術史和研究生院的教授,以及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中國書畫部顧問,他的著作多由在各大學授課時的講稿修訂,或充分利用博物館資源編纂而成,皆是通過風格分析研究中國繪畫史的經典書籍,享有世界範圍的學術聲譽。1978至1979年間,高居翰教授應哈佛大學最負盛名的諾頓(CharlesEliotNorton)講座之邀,發表系列演講,《氣勢撼人》所收錄即當時演講的內容。
十七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面臨改朝換代、人心惶惶的混亂時代,但在藝術史上,卻是畫家創作力最旺盛的時代。高居翰在書中提到:“即使在世界藝術史上,歐洲十九世紀以前的畫壇,也都難與十七世紀的中國畫壇媲美。”這是一部以最淺顯的方式帶領讀者由小見大,進而透視中國繪畫本質的大書。透過作者雄辯而生動的解析,以及豐富細膩的圖版對比,讀者可以毫無困難地進入中國十七世紀多位藝術大師——包括張宏、董其昌、吳彬、陳洪綬、弘仁、龔賢、王原祁、石濤——的心靈與創作世界,同時,也可以一窺中國藝術里自然與風格的複雜辯證關係。
編輯推薦
《氣勢撼人》所收錄即當時講演的內容。此處,我僅僅稍事改寫,並附加幾處簡短的說明。這些講稿(在此已重新編次為篇章的形式)的原意,並非在於交代整個十七世紀的中國畫史;有關十七世紀畫史,我在別處另有處理,拙著中國畫史系列中,第三冊與第四冊將分別以晚明與清初的畫史為探討主題。媒體推薦
高居翰的《氣勢撼人》,是目前為止有關十七世紀中國繪畫的論著中,最具震撼力的一本。——方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教授、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主任)
高居翰基本上倚賴兩個工具:一為其對繪畫風格的精闢形式分析,另一則為其以畫家之身份背景及生活方式為探討作品內涵之切人角色。前者來自於他在西方美術史方面的訓練,非一般中國傳統學人所熟習,後者則出於他長年以來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鑽研,以及一種具有審慎批判態度的理解。通過這兩個利器在畫家作品上的聯繫,他遂得以引導讀者進入時代的文化深處。
——石守謙(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美術由於傳統太長,無論是資料掌握或觀念的自由度,都形成入門的障礙。高居翰的中國美術史,提供了一個新穎而不同的視野,對我們重新面對自己的傳統有耳目一新的啟發性。
——蔣勛(台灣東海大學美術史教授)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高居翰(JamesCahill)譯者:李佩樺等目錄
三聯簡體版新序致中文讀者
英文原版序
地圖
第一章張宏與具象山水之極限
第二章董其昌與對傳統之認可
第三章吳彬、西洋影響及北宋山水的復興
第四章陳洪綬:人像寫照與其他
第五章弘仁與龔賢:大自然的變形
第六章王原祁與石濤:法之極致與無法
簡寫書目對照表
注釋
圖版目錄
索引
序言
1979年3至4月間,我應哈佛大學諾頓講座(CharlesEliot,NortonLectures)之邀,發表了一系列講演,本書所收錄即當時講演的內容。此處,我僅僅稍事改寫,並附加幾處簡短的說明。這些講稿(在此已重新編次為篇章的形式)的原意,並非在於交代整個十七世紀的中國畫史;有關十七世紀畫史,我在別處另有處理,拙著中國畫史系列中,第三冊與第四冊將分別以晚明與清初的畫史為探討主題。如果讀者對於突然切入此一主題感到無所適從,可以參考上述畫史系列的首二冊,即《隔江山色》與《江岸送別》,以建立背景知識,不過,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實則並不需要此種背景知識,因為本書寫作的原意即在於作為專書發行。從任何相關的參考書目中,我們可以發現,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繪畫研究的範疇多集中在十四世紀左右的元代,以及十七世紀的明末清初階段,其他的階段幾乎完全被忽略。這兩個階段乃是中國畫史中極關鍵的時刻,一旦我們了解了其中的堂奧之後,同樣地,也能進一步地明白分列在這兩個階段之前或之後的繪畫景況。本書所處理的乃是明末清初這一階段,亦即十七世紀的中國繪畫,而且,藉由當時代繪畫與相關的畫論著作,我們也進一步地探討了一些藝術史性與藝術理論方面的課題。
諾頓講座以詩為依歸,而“詩”所指的,乃是一種較廣義的意思,也就是說:凡是借文藝形式來傳達意義的,都可算是“詩”;這也正是我在書中所要處理的主題:中國畫(尤其是山水畫)中究竟有哪些含義呢?而這些作品是如何傳達這些含義的?我運用了一些新的方式來探討書中這些作品,希望能夠盡力看出這些畫作在含義上,是否有某些結構存在呢?有些重要的課題,諸如畫家的社會處境等等,我僅輕描淡寫地點到為止。至於明末清初的歷史是否透露出了當時繪畫的形態,這並非我所關心的主題,我所在意的,反而是:明末清初的繪畫充滿了變化、活力與複雜性。從這些作品之中,我們是否能夠看到當時代的社會處境以及思想上的糾葛呢?或者,當時耶穌會引進西方觀念,而滿清入主中國,凡此種種,我們是否能夠從這些繪畫中,看出中國人在面對這些重大的文化逆流時,是如何調整自我的軌跡的呢?
在我原本的計畫里,此次講座的推演正如中國宇宙論中的開元創世一般。在進入主體之時,如一片“混沌”,我們用清楚明確的陰陽二元觀點來切人中國繪畫,這約莫也是最簡單不過的一種藝術理論了:一端是在繪畫中追尋自然化的傾向。
文摘
第一章張宏與具象山水之極限十七世紀的中國繪畫為什麼這樣吸引我們?無疑地,這是由於這一時期的畫家創作了許多感人至深的作品。但是,這一時期之所以引人注目,並不僅僅在於個人作品的美感與震撼力。誠如羅樾(MaxLoehr)所曾經指出,中國早期繪畫系一長期、緩慢而持續不斷的發展,到了宋代,在大師們極致的成就中,達到了高峰,其後,元代畫家放棄了在繪畫中刻意追求氣勢雄渾的效果,而為中國繪畫史開啟了第二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此一發展在明末、清初時,達到最高點。宋元以及明清之際,乃至於其後的幾十年間——亦即十四與十七世紀——是中國晚期繪畫史上關鍵且具劃時代意義的時期。這兩個時期不但產生了許許多多不朽的巨作,同時也開創了許多繪畫的新方向。在這兩個時期里,從事各種復古創作的畫家們對於整個繪畫藝術的過去,進行了影響至深的再思考。在這兩個時期里,傳統自省,進而反饋,又成為傳統的一部分,這種過程自來便是中國文化中所特有。再者,到了晚明和清初,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畫家所面臨的問題,似乎更較以往來得迫切,而且受到畫家更為慎重的處理。這些問題到清初以後,便幾乎不再受畫家們所關切了。
中國到晚明階段,已經享受了超過兩個世紀的太平歲月,多數畫家所在的長江下游地區尤其顯得安定繁榮,畫家和藝術贊助人均能過著頗為穩定自足的生活。明代於1644至1645年間正式結束,在大臣們自相傾軋殘殺之際,中國淪入了滿清“異族”的統治。但明王朝統治的崩潰,實際上自十六世紀末即已開始。朝廷內激烈的黨爭、君主的昏庸無能,以及宦官的囂張跋扈,在在都使得仕宦一途既無道德成就感,也無利可圖。當守正不阿的節操無法為有德之士贏得應有的報償,當正直之士可能因堅持原則而遭殺身之禍時,儒家經世致用的理想再也難以為繼,甚而整個儒家行為與思想體系都受到了質疑。儒家體系的崩潰過去雖也屢見不鮮,但卻不曾如此次般地導致人們對整個體系的全面而廣泛的質疑。李贄與狂禪派人士信奉個人主義式哲學,他們所著重的,乃是自我的實現而非社會的和諧,這與鼓吹回歸儒家根本和政治改革的運動,同時並存著。這是一個充滿矛盾和對立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和藝術都走極端的時代。這種情況固然讓有強烈自我目標的藝術家獲得解放,但卻使得那些需要穩固的傳統,以及遵循規範的藝術家們相形見絀。這種情況表現在藝術上,則是繪畫風格史無前例地分裂,同時,也迸發了持續百年的旺盛創造力。
如果我們嘗試在這裡描述十七世紀繪畫的多樣性,恐怕也會導致類似且令人不悅的支離破碎感。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當依循常法,試圖在這個時期的繪畫或甚至在整部中國畫史當中,找尋一種根本不存在的創作目的與方法上的單一特性。一般而言,近五十年來,中國繪畫的研究多半(而且理當如此地)著重於畫史延續性的建立,以及驗證各發展階段里此種延續特質之顯現。有些對整個傳統的看法,很早以前就已提出,之後便一再地被複述至今,諸如:中國繪畫重表現山水之真諦,而非稍縱即逝的現象;其目的在重視內在的本質,而非外在的形式;其根本上是一種線條與筆法的藝術;特重臨摹過去的作品,尤其到了畫史晚期更是如此;而且原創力也絕少受到強調,等等。這其中的每種說法都含有部分真理,然其真實的程度如何呢?我們可以用一種相對的說法來說明。有些中國或仰慕中國文化的作家對歐洲繪畫也持雷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歐洲繪畫反映了西方文明中物質主義的特性,過度地沉迷於人像,且泰半未能開發敏感筆法里所含的表現力。可怪的是,有的人會因為這種過度簡化的說法而惱怒,但是,他們自己卻往往很能接受上述那些有關中國繪畫的泛泛之談,而且,他們對於那些想要開導我們,為我們講述中國繪畫之“道”及其玄妙本質的作家,也都表現得心悅誠服。
在經過四個世紀逐漸了解之後的今天,我們(按:指西方)視中國文化為單一整體的習慣,仍舊揮之不去。此一觀念的背後,無外乎認為中國人總在追求一種和諧的理想,並採行中庸之道。,雖則此一觀念在其他學科的中國研究中,早已喪失其權威性,然在中國藝術的領域裡,卻仍是一個根深蒂固且被普遍認定的觀點。(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有敏銳眼力的藝評家們,可以在看完一個十七世紀獨創主義畫家的作品展之後,卻認為眼前的作品似乎與較為人所熟知的宋畫並無不同。他們會問:所謂個人獨創主義與非正宗派,究竟是什麼呢?另外,我也聽過有人對歐洲繪畫作類似的反應。一位眼力深厚的中國藝術家暨評論家,曾在瀏覽完美術館所展出的涵蓋義大利文藝復興之前至畢卡索等西方畫家的作品之後,抱怨這些畫作的風格雷同,並惋惜畫家忽略了正確的筆法。所幸,今日已少有人嘗試在那樣的層次上去議論中國繪畫。由於其他領域的藝術和文學相關理論,以及中國社會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辯證方法論上絕佳的例證,我們終於被追覺知到了中國繪畫史的變遷與消長,並開始從每一時代、每一畫派,或甚至每一位畫家本身所面對的多重選擇,以及從各種流風對立的理路出發,來建構畫史。而我研究十七世紀繪畫的方法,即是屬於這一種。
首先,我們可以用兩張晚明階段的繪畫來闡明一種熟見的二極性【圖1.1與圖1.2】,一張是那種依傳統形式所建構而成的作品。另一張則至少嘗試相當忠實地描繪一段自然的景色。(若有讀者發現難以立即看出哪一張畫代表哪一種畫法,其咎正在於我適才所描述的現象:想在視覺上區別作品的異同,必須先在視覺上對於素材本身有某種熟悉度。不過,這兩張畫應該要不了多久,便可看出其明顯的不同。)這兩張畫,其中一張是董其昌l617年的作品,根據畫家自己的題識,他所畫的是位於浙江北部吳興附近的青弁山。另一張則是同時代,較董其昌年輕的張宏的晚年之作。畫上的年款為l650年,所以應該算是清初,而非晚明的作品。雖然這兩張畫的創作相去三十餘年,卻不影響我們進行比較,因為我們同樣也可以拿畫家相隔僅數月的作品來作相同的比較。張宏畫裡所描繪的是距南京東南約五十英里左右的句曲山。
借這件作品,及其所在的創作背景,我們恰可引出晚明畫家所面臨的主要課題與選擇。張宏活動於蘇州(參閱地圖),且就我們所知,是號職業畫家。董其昌則系鄰近以松江為中心的山水畫派宗師,同時也是一顯赫的文人士大夫,對他而言,作畫乃是一種業餘的嗜好。在這段時期里,含董其昌在內的中國繪畫理論家,以“行家”和{‘利家”來區分職業畫家與業餘畫家。對董其昌者流而言,這種分野雖則實際上頗為含
糊,然在理論層面上,卻有其根本的必要性。董其昌所屬的松江派業餘畫家經常指責同時代蘇州畫家商業化的傾向,並攻擊他們對過去畫風一無所知。張宏的作品確實沒有任何明顯或刻意指涉古人畫風的意圖;另一方面,董其昌畫上的題識則告訴我們,其格局乃承襲自十世紀某大師的風格,不過,實際上他所採用的卻是另一位十四世紀大師的形式結構。對同時代具有涵養的觀畫者而言,這兩個層面所指涉的古代風格,他們必定能夠一目了然。我們可以將這兩張畫視為自然主義與人為秩序兩種相反且對立方向的具體表現,此種相反與對立亦即是貢布里希(ErnstGombrich)在論及文藝復興時期繪畫時,所提出之古典的對立:“可以想見,一幅畫若愈是……忠實於反映自然的面貌,則其自動呈現秩序與對稱的法則便愈形減少。反之,若一造型愈有秩序感,則其再現自然的可能性也就愈低。”(董其昌作品中所呈現的秩序感,以及內在於此秩序感的反平衡和特意造成的無秩序感等,詳見第二章討論。)
董其昌與其青弁山的畫題之間,因而便隔著一層密實的古人畫風的簾幕。董其昌曾在別處提及,有一次他行船途經青弁山,憶起了曾經見過趙孟與王蒙兩位元代畫家描寫這座山的作品;在董其昌心中,當他在認知此山的真實形象時,這兩幅畫的記憶必定已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趙孟煩的畫已經佚傳,不過,王蒙的作品卻仍流傳至今,是董其昌用來標示其畫作里文化軌跡的另一藝術史坐標。因此,真正決定董其昌畫作的主要元素,並非記憶或實地寫真,而是作品本身與過去畫史之間複雜的關聯性。畫家對於筆墨結構的關注,完全凌駕於空間、氛圍和比例的考慮之上,而筆墨結構則部分源自於既往的作品。同時,純水墨的素材表現也對作品的抽象特質有所助益:相對地,張宏所描繪的句曲山,是以淡彩烘染,展現出畫家對空間、氛圍與山水比例細微的觀察。晚明的評論家唐志契在《蘇松品格同異》一文中,簡要而貼切地道出了此二派畫風的區別,亦即“蘇州畫論理,松江畫論筆,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準繩也。筆之所在,如風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氣味也”。
董其昌本人在揭示有關真山真水與山水畫之區別的名言中,也同樣地暗示云:“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精妙論,則山水絕不如畫。”換言之,若你要的是優美景色,向大自然里去尋;若你要的是畫,找我即可。
這兩張畫的不同,非僅在於風格、流派或手法上殊途同歸的問題,而在於兩張畫分屬不同類型。我們習於將中國山水畫視為單一類型,實則它是多種類型的組合,這在晚期的山水畫尤其如此。董其昌《青弁圖》屬於“仿古”創作,他在題識中也如此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