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雜誌》
正文
此刊主張維護“藝術良心”,提倡“自由主義文藝”。編者在《我對於本刊的希望》中表示,“現實的中國文藝界”,“無論是左是右”“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了“死路”,而“處在幼稚的生髮期”的中國新文藝,“應該有多方面的調和的自由發展”,從而提出了“自由生髮,自由討論”的發展新文藝的原則,“主張多探險,多嘗試。不希望某一種特殊趣味或風格成為‘正統’”;並“根據這種信念”,決定把此刊辦成“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使其“對於現代中國新文學運動”“盡一部分糾正和響導的責任”。復刊後主編者在《復刊卷頭語》、《蘇格拉底在中國》等文章中又重申了這種辦刊宗旨,刊物本身也體現了前後指導思想的連續性。但歷史條件的變化也使後期刊物與前期在思想上有所差別:針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進步文藝界對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的貫徹和同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鬥爭,主編者提出“文學上只有好壞之別,沒有什麼新舊左右之分”,強調“反對”一些本來與文學無緣的人們打著文學的招牌,作種種不文學底企圖”。表現了對革命文藝新形勢的不滿;強調了中國民族與文化存在著極大的弱點,患“半愚昧症”,沒有“思想的生髮自由”,而要克服其弱點就要“擴大中國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受當時美國鼓吹中國“第三種力量”政策的影響,主張知識分子走“第三條道路”,顯現出更為鮮明的“中間路線”的思想色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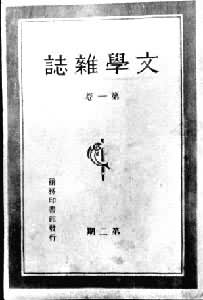 《文學雜誌》
《文學雜誌》此刊創刊時曾得到胡適的大力幫助,創刊後以“京派作家”為基幹,得到原“新月派”作家的支持,主要撰稿者(除編者外)有沈從文、廢名、林徽因、馮至、卞之琳、林庚、陸志韋等,後期撰稿者除了上述知名作家與學者外,增加新起的青年作家袁可嘉、穆旦、畢基初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