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有個亂棗墳》
作者:不歸根的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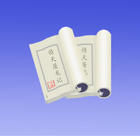 《我村有個亂棗墳》
《我村有個亂棗墳》書籍簡介
通過對我村亂棗墳過去發生的歷史事件的描寫,反映了那個社會的黑暗和對人性的摧殘.
文章截選
在良村的正南二里處,有條小河叫胭脂河。咱先不說這條河的瓜長蔓短,你順著這條河的北岸向東走上不到半里,你就會看見那塊只長酸棗不長其它雜草的地,這塊地南北短,東西長,占地面積也就是五六畝,我村的人把這塊地叫它“亂棗墳。”
聽老人說,原來這地方叫“亂葬墳。”村人嫌那葬子不吉,陰氣太重,再加上這地方只長酸棗,也就葬棗同一叫成了“亂棗墳。”這“亂棗墳”一年四季飛鳥不落腳與此,就連陰氣很重的貓頭鷹晚上都不到這裡來,只要你人站在它跟前,會是你總感到有種陰森森的冷氣加雜著一股血腥味向你撲來,隨之就象是從這地縫裡傳出“救救我。”那能讓你我毛骨悚然的聲音。所以就由過去到今天,我良村的父老幾乎很少有人主動去提它,為的是不想勾起過去那些讓我村人感到不堪回首的東西。
一
民國二十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二年的秋天,正是村西頭壯壯結婚的那一天。
那時的良村是個幾十戶的小村,一家辦喜事就等於全村在高興,更重要的是這壯娃他爸申文遠,是從河南逃荒而來,那年他河南老家因黃河泛濫,家鄉成了島國。他就帶著老婆,手拿打狗棍,夾著行里卷一路東行,走到我良村時實在走不動了,就順邊在我良村安了個家,常言說:“樹落死,人落活。”至從他到了我良村,每天衣食還能自給,三頓飯沒少,也不用再做那白浪滔天,人或為魚鱉的夜半夢,在那社會他也早就知足了,可他唯一的心病就是壯娃他媽都到了三十好幾就是不開懷,兩個人急的四處尋醫問藥,廟裡磕頭,求神拜佛。就這樣壯娃他媽到了四十開外才生了個壯壯,他爸為的就是讓他身強馬壯,就給他起名叫壯壯。因為曾有這些難成事,所以,今天壯娃結婚,申老是鼓足了勁,點著腳尖尖,擰可掙死牛也不停下車,也要把這叫梅子的女子給壯娃娶進門。那是父母的主任呀!
再說申老和老伴一整天的接親送客,在加上年紀大了,等到了家中也沒了啥大事,就和老伴早早睡了,只剩下和壯娃同輩的還在新房裡“耍媳婦。”不時的起轟聲把那新房能擠破,你看狂不狂。
“耍媳婦”也就是外面人說的鬧洞房。村里不管誰家娶了新媳婦,從第一天晚上開始就要連“耍”三天,我有時想陝西人為啥把鬧洞房說成“耍媳婦。”那是陝西人的豪氣還是陝西人的粗,是水土問題還是鄉俗問題我的確不知道,但這話讓人聽了後就有點以強凌弱,以熟欺生的感覺。反正“耍媳婦”時可不分男女老幼,你可以讓新媳婦給你點菸,給你倒水,你也可以說些髒話粗話,就是同輩的晚輩的在新媳婦身上那要緊處揣摸一兩下那也都不為過。你看,儘管已經是夜半三更,和壯壯同輩的黑三,二狗,老四等村裡的十來個小伙還在新房裡鬧,等把新媳婦身前面高的摸過了,後面高的也摸過了,甚至連那夾縫出處也都蜻蜻點水的摸了一把,按理他們該走了,你看鬼點子最多的黑三又出了個新幅幅。
黑山說:“咱別耍我嫂子了,我嫂子太嫩了,要是耍出個三長兩短,就對不起我壯哥了。”
二狗和老四急忙的問道:“那耍誰,難到今晚不耍了?!”
黑三答到:“咱咋能不耍,我說我壯哥肉硬骨頭粗,咱就耍我壯哥,給他耍個牛拉燈後咱就回。”那幾個一聽就象狗聞見了腥味,激動的嗷嗷叫,梅子當然不知道這“牛拉燈”是耍啥,我家鄉的人把男人的生殖器叫“牛”也叫“錘子。”用我這豬腦子想,叫“牛”是說那東西的勁大,叫“錘子”是一種借物比喻吧。
只聽黑三說:“動手沒,還等啥。”
黑三,二狗,老四還有其他幾個一齊上手,把壯娃抬到炕上,壓頭的壓頭,拉胳膊的拉胳臂,還有壓腿的壓腿,黑三就急忙伸手就去解壯娃的褲腰帶。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壯娃好壞也是個男的,更不要說他還是同輩的小伙頭。咋能不反抗,開始還東擰西扭,腳踢拳打,不一會就沒勁了,也就來個死豬不怕熱水燙,都是自家哥們,任他們擺弄了。只見黑三把壯娃的褲子拉到大腿下,再讓二狗端來已經添滿油的燈,那時的油燈和咱現在的酒杯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那燈是用黃土燒制的,在酒杯的內壁上有個小孔,然後把棉花搓成細繩從燈的小孔穿出來,這油燈就做成了。
黑三接過燈,把燈放在壯娃的兩腿交差處,也就是那“牛”的緊下面。黑三又從自己的身上掏出一截細麻繩,先把一頭綁在油燈上,並把油燈和壯娃的“牛”挨緊後,再把細繩的另一頭也勞勞的綁在壯娃的“牛”上。完後黑三就對壯娃說:“壯哥,你千萬不敢動,燈里的油滿滿的。你動了弄得燈倒了,油流了,把炕著了不說,把你傳宗接代的燒了你可別怪我。”又說:“我們走了,剩下的就讓我嫂子來服侍你。
他們一走,梅子抬頭一看就弄個臉紅心跳,傻了眼。你道為啥,只見壯娃兩腿大開,就象掛在架子上的豬,一個油燈放在兩腿的交岔處,那“牛”就象虹橋臥坡,非云何龍,作為女人這男人的這東西她還是頭一次見,好在沒有外人,她伸手就去端燈,壯娃驚叫著:“別動。”梅子嚇了跳,仔細一看才感到這問題不簡單,只要你梢不注意就會燈倒了,油著了,而且會把那東西也燒了,如果傳出去,還不叫人笑話死。
就在她用手在壯娃那“牛”上三比劃兩比劃的時候,壯娃那“牛”卻也在這時來了勁,躍躍欲立,大有將燈拉翻的架頭。梅子一看急了,也顧不得什麼害羞不害羞,就忙用手把那東西按著,急中生智的從頭上拔下銀簪,在燈上燒紅,在那麻繩上輕輕的一烙,那繩冒了一股煙就斷了。
還沒等梅子直起腰,就聽窗外有人在突然的喊:“新媳婦,手揣牛。”那聲音隨著吶喊也很快的飄向方。
耍房的人走了,走遠了,月亮也走到了那一片雲中,黑夜將一切都阻擋在新房之外,是乎這夜晚就是有情人纏綿的時間,你再聽城壕里的癩蛤蟆也在扯破嗓子的叫著,生怕失卻了今晚著美好的時光。
等黑三,二狗,老四這幾個鐵哥們一走,把個壯壯急的就象個火猴,就立即把梅子給炕上抱,急著就是想放他那一把火,要不是媳婦提醒他,他會連門都忘了關,當他帶著男人們特有的膳氣和那濃濃的汗臭,把梅子這個女人卷壓在他的身下後,眼前這秀美的山川,已是忘卻了一切,汗流夾背的在上面耕雲。是呀,嬌美山川人留巒,他已經將自己深深的容入在這山川綠水的懷抱只之中。當他帶著舒坦和汗水從這秀美的山川上滑落下來,就已進入深深的夢中。只有梅子一個人透過窗戶,靜靜的看著天上那不知疲倦的星,聽著城壕里叫聲纏綿的蛙鳴。
突然,不知是誰家的狗一聲驚叫,接著就是全村的狗在互相呼應著叫成一片,在那個軍閥混戰,土匪橫行的年月,莊稼人就靠的是用狗來看家護院,狗的叫聲就是信號和警報,全村的人驚醒了!就是壯壯也被媳婦梅子從睡夢中搖醒。
梅子說:“你聽,村裡的狗咋咬的這么急,會不會是土匪來了。”
也許是壯娃年輕火勝,好在伏里的夜晚也不冷,只聽他“騰”的一聲跳下炕,順手拿個槐木棍,上半身沒穿衣服就出了門,說到這,這也許是梅子一生的後悔,她的腸子也許在明天都能悔青。
其實,就在狗的叫聲越來越緊時,家家戶都把門開個門縫朝著外面看,更有黑三,二狗,老四也出了門朝著狗咬的方向走來,到了村東口,壯壯和他們站在一起朝北看,只見汽車前面的大燈將這南北路照的通明,不平的村路,被飛速的汽車用它的輪子在它的身面錘打,不時傳來咔咔的響聲,道上的塵土也被汽車捲起,就象是汽車後面著火了,冒出的滾滾濃煙,他們誰也沒有見過這陣勢,急忙蹲在城壕的蘆葦叢中,他們剛蹲下,就見汽車從身邊駛過,每輛汽車前面的踏板上站著持槍的士兵,令他們奇怪的是那些士兵在大熱天卻都戴著個大口罩,從他們面前過去的八輛汽車沒有進村,而是沿著這南北路直接的向南開去,也許是好奇心的作用,還有著年輕人的狂性,長的黑胖黑胖的黑三說:“壯哥你敢去沒?走咱看去。”
二狗看壯娃在猶豫,就挖苦著說:“對了,我壯哥那點心思咱還不知道,他還在想媳婦呢。”
壯壯說:“滾!在我心中咱幾個鐵哥門誰都比女人重要,想看咱就要小心,那些家火拿槍著,誰不想去就趕快回家,叫屋裡的人別等。”
除了幾個膽小的回了家,餘下的壯娃,黑三一共是十三個人就朝南門外跑,說到這真讓我良村人寒心,全村就那么幾十戶,他們這十三個人要是有個三長兩短,那么我良村幾乎就是三分之二的人家將是無兒的戶,媳婦就成受寡的人。他們翻過城壕,只見那些汽車開到了煙脂河,然後向東拐停到了我村“亂棗墳”的那塊地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