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我在霞村的時候》寫於1941年初,發表於同年6月的《中國文化》第3卷第1期,後收入1944年桂林遠方書店出版的同名小說集。
作品內容
 丁玲文萃 我在霞村的時候
丁玲文萃 我在霞村的時候作品塑造的是一個在遭受日寇凌辱後又忍受著靈與肉的雙重折磨而做著地下形態的抗日工作的鄉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題材的擇選以及作者對於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膽識和藝術創新方面的追求,儘管對於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從側面進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觀照視角,用作者的話來說作品提出來的是“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丁玲談自己的創作》),仍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
深遠思考
曾有論者批評作品沒有更充分地揭示主人公貞貞對於敵人的仇恨,而對民眾的落後也過於渲染。其實,就後者而言,這正是作品提出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的合符生活邏輯的依據。至於前者,那是膚淺的苛刻的要求,馮雪峰曾論述貞貞的形象說:“貞貞自然還只在向遠大發展的開始中,但她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長也是可以確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們這樣相信貞貞和革命”。(《從〈夢珂〉到〈夜〉》)這樣的把握顯然才是正確的。
創作前後
《我在霞村的時候》所影射的還不止丁玲1933~1936年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叛徒馮達”羈留南京的屈辱生活,應該還包括1931~1933年她擔任“左聯”黨團書記、“左聯”機關刊物《北斗》雜誌主編
 《我在霞村的時候》,作 者:丁玲,出 版 社:三聯書店,出版時間:1950-01
《我在霞村的時候》,作 者:丁玲,出 版 社:三聯書店,出版時間:1950-01期間的同樣屈辱的生活。1931年2月7日,國民黨在龍華秘密槍殺了“左聯”五烈士,其中就有丁玲的丈夫、詩人胡也頻。當紅作家丁玲一下子成了烈士遺孀,前此一直是獨立作家的她,在情緒激動中迅速左傾,甚至要求即刻去江西蘇區參加革命。但張聞天、馮雪峰認為她應該留在上海,為“左聯”工作,原因是“左聯”的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鬥爭》、《巴爾底山》都因為很快暴露左翼傾向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其中包括為紀念烈士秘密創刊的《前哨》。“左聯”領導因此決定利用當時未滿27歲、被魯迅看作還是“孩子”的丁玲的不太暴露的身份出任新的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丁玲自己後來說得更清楚:“為什麼要我來編呢?因為我在左聯沒有公開活動過,而且看起來我帶一點小資產階級的味道,雖說我對舊社會很不滿,要求革命,但我的生活、思想感情還有較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的味道。叫我來編《北斗》決不是因為我能幹,而是因為左聯里的有些人太紅了,就叫我這樣還不算太紅的人來編《北斗》。”(《丁玲文集》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丁玲對此是很不舒服的,她因此拚命證明自己是“紅”的,也因此最終導致了《北斗》的被查封。在整個“左聯”工作期間,丁玲一直很鬱悶。她晚年回憶批評家錢杏村說她是無政府主義者時非常痛苦。周揚一直不喜歡她這個同鄉,據王蒙說周揚甚至攻擊丁玲“她有一切壞女人的毛病:表現欲、風頭欲、領袖慾、嫉妒……”這雖是後話,但類似的歧視的氛圍在1931年至1933年就存在了,1931年至1932年丁玲給馮雪峰的兩封書信,就是有力的證據。這本來是丁玲寫給馮雪峰的情書,丁玲被捕後,為了製造輿論,便於開展營救,馮雪峰策略性地將它發表,特地題作《不算情書》,其中就有這樣抱怨的話:“好些人都說我,我知道有許多人背地裡把我作談話的資料的時候是這樣批評,他們不會有好的批評的,他們一定總以為丁玲是一個浪漫(這完全是罵人的意思)的人,以為是好用感情(與熱情不同)的人,是一個把男女關係當作有趣隨便(是撤爛污的意思)的人。”可悲的是,這種處境,正是她所深愛的終生的偶像、批評家、上海左翼文學領導者之一馮雪峰一手安排的。她後來之所以沒有及時離開南京,除了家庭因素之外(她和馮達在羈留期間育有一女),馮雪峰的再次安排也是重要因素。她找機會回上海後,要求馬上去延安,但馮主張她仍然回南京。既然國民黨這樣放鬆,何不爭取“公開工作”呢?這個思路和當時要她主編《北斗》如出一轍!《霞村》里可憐的貞貞,不也是在日本人那裡為了自己人的策略而幾進幾出嗎?“人家總以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貴榮華,實際我跑回來兩次,連現在這回是第三次了。後來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沒辦法,我在那裡熟悉,工作重要,一時又找不到別的人。現在他們不派我去了,要替我治病。”“誰都偷偷地瞧我,沒有人把我當原來的貞貞看了。我變了么,想來想去,我一點也沒有變,要說,也就心變硬一點罷了。人在那種地方住過,不硬一點心腸還行么,也是因為沒有辦法,逼得那么做的哪!”
因此《霞村》實際上寫了1931~1933年“左聯”時期的鬱悶和1940年面對1933~1936年南京時期所謂不清白的歷史的雙重的焦慮,是這樣的雙重焦慮和怨恨的一次大爆發。“我們的關係就更密切了,誰都不能缺少誰似的,一忽兒不見就彼此掛念。我喜歡那種有熱情的,有血肉的,有快樂、有憂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這樣。”但這只是小說中的“我”和貞貞認同的一面。“我”和貞貞遭遇的不同在於,貞貞取得了組織上的充分的愛和信任,懷著對未來的無限信心,終於可以離開不利於她的充滿敵意和誤會的“霞村”,奔赴展開熱情的雙臂歡迎她保護她的延安了。而小說一開始說“因為政治部太嘈雜,莫俞同志決定把我送到鄰村去暫住”,接著又強調去霞村的一路上我“很寂寞”,“精神又不大好”,儘管“我的身體已經復原了”。“政治部”在什麼地方沒有交代。即使不在延安,也一定在一個類似貞貞要去的歡迎和保護貞貞的地方。問題是“我”恰恰就是離開那個地方,來到對貞貞很不友善的“霞村”。“我”和貞貞的交叉跑動形成一種設計精巧的敘述結構,說明“我”的政治待遇還不如貞貞,儘管“我”的身體比貞貞好,但“我”的心比貞貞更苦。“我”離開了本來應該醫治“我”的“政治部”而來到處處是陷阱的“霞村”,貞貞卻可以離開霞村而奔赴可以醫治她的“光明的前途”。
作品深刻之處
《我在霞村的時候》的深刻之處在於揭示了丁玲的一個尷尬:理論上解放區應該是婦女獲得真正解放的地方,可是現實卻不是這樣,封建主義對以“貞”“節”的道德正當性繼續維持著對婦女的壓迫。身為女性作家,丁玲同情小說的女主人公,可作為革命者,她又不能否定革命大眾,於是,女性立場和政治傾向間的拉差,就構成了丁玲的游移矛盾,也導致了她的這篇小說的複雜。
作品評論
《我在霞村的時候》是丁玲在1941年創作的一部抗日文學作品,文本講述一位中國少女貞貞在遭受日寇凌辱後,又忍受著靈與肉的雙重折磨而做著地下形態的抗日工作,卻又為傳統所不容的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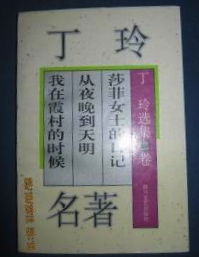 丁玲名著-《我在霞村的時候》
丁玲名著-《我在霞村的時候》貞貞本來是一個純樸的農家女子,卻不幸被日本鬼子擄去了一年多,這在世俗的眼光里,是將貞貞看做是一個“慰安婦”,然而作者丁玲卻給予了這個不叫好的形象一種特殊的情感。丁玲在這篇小說中注入了真情,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來寫成,這看得出,敘述者“我”與作家本人其實存在著高度的同一性。而在敘述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全篇洋溢著澎湃的情感,“我”關注著這個女子,以一顆女兒心去貼近另一顆女兒心。那么貞貞到底是怎么樣的一個形象呢?“我”在貞貞身上看到了什麼呢?本文將試圖探求貞貞的成長,分析貞貞作為一個世人眼中的“慰安婦”是如何尋求女性世界和實現自身價值。
貞貞的成長是一個抗爭的成長過程。她與丁玲早期小說中的知識女性一樣,有相同的特徵,自立、自強,具有個性解放的色彩。在父親替她講的親事:“西柳村的一家米鋪的小老闆,年紀快三十了,填房,家道厚實……”面前,她“向著她爹哭過……卻賭氣跑下城主堂去了。”在那個年代,中國婦女本來就受“三權”的壓迫,而帝國主義的入侵,使她們遭受的苦難更是加深了一層。然而,她並沒有像古代的“烈女”那樣死去,強烈的求生本能和生命意識鼓舞著她再次進行抗爭,與命運搏鬥。在那種非人的生活中,貞貞與游擊隊取得了聯繫,忍受著肉體與精神的痛苦默默地投身到民族革命的戰爭中。但命運總是與她過不去似的。一年多後,組織上送她回家鄉霞村養病,可是被傳統的封建意識束縛著的人們,使得霞村許多人不能正確對待貞貞的遭遇,不能對貞貞於革命的貢獻有所認識,更不可能理解貞貞偉大的自犧牲精神,甚至向她投以鄙視的目光。但越是在逆境中,貞貞越是有著頑強的個性,悄然成長。她冷靜地對待了村里人對她的非議,在殘酷的生活面前,她撫摸著自己內心累累的傷痕,拖著被污辱的身軀,帶著鄉村封建衛道士的中傷,勇敢地直面這樣血淋淋的人生,奔向延安,“而且我想,到了××(指延安),還另有一番新的氣象。我還可以再重新作一個人……”
王蒙曾經說:“少年時代我讀了《我在霞村的時候》,貞貞的形象讓我看傻了,原來原來一個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難、英勇、善良、無助、熱烈,尊嚴而且光明。”這么多有著強烈情感意義的形容詞贈與了貞貞這個人物形象,不得不說在貞貞身上所發出的光輝是不會被她那在日本鬼子糟蹋過的身軀所掩蓋的。我想丁玲給這么一個人物形象起名為“貞貞”,似乎也是一種微妙而又含蓄的抗議,就如同貞貞的成長是一個抗爭的成長。同時,她還給貞貞設計了一個為我方送情報的細節和一個似乎是無限光明的未來。丁玲還在文本中用了一個很有意味的比喻:“雖在很濃厚的陰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卻被燈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兩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洞開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沒有塵垢。借著這個比喻,丁玲把貞貞的狀態——她的確在蒙受著屈辱,但同時她也確實有著潔白的靈魂——明白地表示出來了。
萬直純在《女性尋找——從丁玲創作看現代中國女性的精神歷程》一文中將《我在霞村的時候》看作是中國現代女性自我意識發展的心路歷程的一個標誌。他認為《我在霞村的時候》表現了丁玲從“自我世界”到“男性世界”再到“整個世界”這一尋找過程中交織著現代女性對自我的確認與超越,呈現出複雜的女性意識。這一女性意識就是表現在貞貞這個形象的身上,更高層次地披露了現代女性是怎樣實現自我統一性,尋找女性世界。男權意識形態對社會有著長久的堅固的控制,在父親對自己婚事的主張、封建束縛下的村民鄙視的眼光以及日本鬼子的淫威下,貞貞並沒有屈服於這種男權禁錮,而是起身反抗:賭氣、冷靜面對,還有蒐集情報給游擊隊通風報信,並使日軍吃了一些敗仗。
在尋找女性世界的同時,貞貞也實現了自身價值。什麼是實現自身價值?筆者認為為別人創造價值便是實現自身價值的根本。在苦難中貞貞不但沒有沉淪,反而是加入了革命隊伍,為了革命犧牲自我,為了中國億萬人民的未來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熱情。她在文章中真情地告白:“人大約總是這樣,哪怕到了更壞的地方,還不是只得這樣,硬著頭皮挺著腰肢過下去,難道死了不成?後來我同咱們自己人有了聯繫,就更不怕了。我看見日本鬼子吃敗仗,游擊隊四處活動,人心一天好起來,我想我吃點苦,也划得來,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除非萬不得已。”就是這樣,這個樸實可愛的農家女孩,一路坷坎地尋找一個新的女性世界,完成了對自身悲劇命運的超越,在一種非人的境遇中找到了生存的理由,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參與了民族抗戰事業,向蹂躪她的日本強盜實施了復仇,在時代的洪流中實現了自身的價值。
在逆境中成長,貞貞的成長是一個抗爭的成長過程。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丁玲把貞貞這么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搶去作隨營娼妓,被村民看作是“慰安婦”的女子,當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在她身上有著抗日前線革命女性的特質,這種特質就是尋找女性世界、實現自身價值的拼搏精神。筆者認為這是為當代女性所必須持有的生存精神氣質。
女作家丁玲作品
| 丁玲,現代女作家。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