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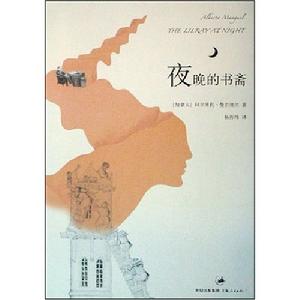
繼《閱讀史》之後,《書齋漫步》生動講述了書齋或圖書館在人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曼古埃爾在法國的家裡策劃修建了一個書齋,他受到這件事的啟發,進而告訴我們書齋或圖書館怎樣體現了許多個人乃至整個文明的回憶。本書軼事連篇,扣人心魄,從作者幼時的書架一直說到國際網際網路的“全套”圖書,從古代埃及、希臘到阿拉伯世界,從中國、羅馬講到“谷歌”。這裡有已消逝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有撒繆爾·派匹斯的私人書齋:他給體積小的書本裝上“高跟”,好讓書架上的書整齊好看;還有文學家的書齋,狄更斯、博爾赫斯等等…… 曼古埃爾在書中還講到詩人兼建築家米開朗基羅的紀念碑式的圖書館,慈善家卡內基建立的圖書館,監獄裡囚犯的口頭“回憶圖書館”等。
作者介紹
阿爾貝托·曼古埃爾
阿爾貝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有國際聲譽的文選班纂家、翻譯家、散文家、小說家和編輯。著作包括下列獲獎暢銷書:《幻鏡辭典》(A Dicitionary of Imaginary Places)、《閱讀史》(A History of Reading)、《閱讀圖集》(Reading Pictures)。他生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1982年移居加拿大,現在法國居住,被授予法國藝術及文學勳章軍官勛位。他的最新作品為《與博爾赫斯在一起》。
楊傳緯
楊傳緯,英語教授,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84-1989年曾任北京師範學院(首都師範大學前身)院長。1987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譯著有《夜晚的書齋》、《書趣》、《閒話大小事》、《OED的故事》。
本書前言
我向來喜歡遊蕩(即使沒什麼收穫),我像只追逐獵物的獵犬,看見鳥兒便大聲狂吠,把獵物追遍了,該追的卻沒去追(想什麼都乾,什麼也幹不成)……我真心誠意地訴苦:我讀了許多書,但漫無目的,缺少好方法;我在圖書館裡碰到各種各樣的作家都狼狽地絆了跟頭,未能獲益,因為我不講藝術,不講秩序,沒有記憶力和判斷力。
——羅伯特·伯頓,《憂鬱之剖析》
起點是一個問題。
除神學和幻想文學之外,幾乎沒有人會懷疑,我們的宇宙的主要特點就是它缺乏意義,缺乏明顯的目標。然而,懷著異樣的樂觀精神,我們卻不斷從卷冊中、書本中、電腦晶片中,從圖書館一架又一架的圖書孽,盡一切力量去收集無微不至的信息,苦心孤詣地想給世界找到一點類似意義和秩序的東西。我們完全清楚,不管我們怎樣努力朝好處想,我們的追求是注定要失敗的。
那么,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雖然我早就知道這個問題很可能找不到答案,但是看來尋找一下還是值得的。這本書就是講述尋找的故事。
我對於這種無窮無盡收集信息的努力非常感興趣,超過了對確切日期順序以及姓名的興趣,因此,我幾年前動筆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再編一本圖書館的歷史或一本圖書技術史(這類書已經多得很了),而只想表述我的驚異心情。一個世紀以前,史蒂文森寫道:“在一個無法取得成功的領域內,我們人類卻從不停止努力,我們當然會認為這是感人至深,令人鼓舞的。”
不論是我自己的書齋或是與公眾分享的大圖書館,都是令我著迷的地方。從我能記事的時候起,我就受到它迷宮式邏輯的吸引,感到理性(或藝術)可以統管一大堆雜亂喧鬧的書籍。置身於書叢之中,我有一種冒險的快感,我迷信某種字母或數字的排列方法會把我領到美好的目的地。書籍一向就是神聖藝術的工具。諾思洛普·弗萊在他的筆記中寫道:“大型圖書館真有語言魔力以及心靈感應的無比神通。”
懷著這種愉快的幻想,我花了半個世紀來收集圖書。我的書非常慷慨大度,不對我提出任何要求,卻給我各種教益。彼特拉克給一位友人寫道:“我的圖書室是充滿學問的,儘管它屬於一個沒學問的人。”我的圖書也是一樣,它們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我真心感謝它們會容忍我的存在。我有時會感到自己辜負了我享有的特權。
愛是需要學習的,愛書也要學習。一個人初次踏進充滿書籍的房間,不可能憑本能知道怎樣做事,怎樣守規矩,可以期待什麼,得到什麼。他可能感到恐懼——由於紛亂,由於廣闊、寂靜,由於監視,由於他不知道的一切引發的聯想——甚至在學會了規矩禮節,懂得了門徑,發現人們都很友善之後,某種畏懼的心情還會殘留著,驅之不去。
在傻乎乎的青年時代,朋友們都夢想在工程界、法學界、金融界和政界乾出一番大事業,我卻夢想當個圖書管理員。但是我生來疏懶,又毫無節制地愛好旅遊,於是又另作打算。現在我已經五十六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說,“這是開始真正生活的年齡”),我又回到了早年的理想。雖然我無權自居為圖書管理員,但是我的書架日益增多,其界限已經與整個房屋混淆不清,我就生活在這些圖書之中。這本書的名稱本來應該叫做《週遊我的房間》。遺憾的是,兩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扎維爾·德·邁斯特(Xavier de Maistre)已經占得先機了。
文摘
白天,我寫作,瀏覽,重新排放書籍,把新獲得的書籍列入書架,為了節省空間而調整分類。新來的書經過一個時期的觀察後受到歡迎。如果是“二手書”,我把書中原有的印記都維持原樣不動:先我閱讀者的痕跡,他們草草書寫下的評論,扉頁上的名字,夾在某頁當書籤的一張公共汽車票,諸如此類。不管是新書舊書,我要驅除的惟一標誌就是惡意的書商貼在書背面的價碼(但往往是不成功)。這些醜惡的白色瘡疤很難剝離,留下麻風病一樣的斑痕或者長出絨毛的印跡,上面沾上灰塵或黏液。我簡直希望發明這種黏黏糊糊標籤的人能夠墮落到特殊的黏糊的地獄裡去。
到了晚上,我坐下來閱讀,看著一排排書引誘我把相鄰的書籍聯結在一起,為它們編造共同的故事,由一個記憶中的片斷聯想到另一個片斷。弗吉妮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曾經試圖區分愛做學問的人和愛讀書的人。她的結論是“這兩種人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她寫下這樣的話:
從事學問的人是全心全意、滿腔熱情從事案牘工作的孤獨者,他搜遍群書去尋找他下決心追求的某個特定真理的微粒。如果讀書的熱情征服了他,他的收穫就會縮小,從手指縫裡溜走了。另一方面來說,愛好讀書的人一開始就必須遏制自己對學問的欲望。如果知識偶然沾在他身上,那當然很好,但是要專心去追求學問,要系統地讀書,要做一個專家或權威,那就難免扼殺了我們不妨稱為更富人情味的追求——純粹的、無偏向的閱讀熱情。
白天,系統與集中吸引著我;晚上,我懷著輕鬆的心情讀書,幾乎到了陶然忘憂境界。
然而,不論白天或晚上,我的書齋是私人的領地,不同於大大小小的公共圖書館,也不同於神異的電子圖書館(對它的萬能性我還保留著輕度懷疑)。三者的結構和習俗在許多方面是不同的,雖然三者都有共同點,那就是:都明顯地想要調和我們的知識和想像,將信息分類包裝,把我們對於世界的間接經驗集中在一個地方,而且由於愚昧、小氣、無能、恐懼等原因,又把許多人的經驗排除在外。
書評
有人問本雅明是否讀過自己所有的藏書,本雅明回答說不到十分之一,之後他反問說,你每天都用到自己收藏的瓷器么?藏書的樂趣在於所蒐集來的書本是一件件藝術品,不涉及書中的內容仍能自得其樂。而讀書是另外一種樂趣。藏書的樂趣在於形式,讀書的樂趣在於內容。無論藏書還是讀書,都是一種康德意義上的無功利般的精神上的愉悅,能把這種單純的愉悅張力表現到極致又不失蘊藉的,近期所讀的書中恰好還有一本,這就是加拿大作家阿爾貝托·曼古埃爾的《夜晚的書齋》。
這位現已定居法國的加拿大作家和藏書家極具天賦,一直以來甚得閱讀樂趣,著述甚多。我們熟悉他的中文版的作品有《閱讀史》、《閱讀日記:重溫十二部經典》和《戀愛中的博爾赫斯》。《夜晚的書齋》是他新近的作品。作者在法國的家中策劃修建了一個自己的圖書室,而且選擇的地方也很獨特,“早在15世紀時,這裡原本是個糧倉,高居法國羅亞爾省南部的山丘之上。遠在基督教時代之前,羅馬人在此修建了一個狄奧尼休斯神廟,來祭奠這位葡萄酒之神”。選擇如此具有歷史感的神跡之地修建一個圖書室,本身就是一種延續歷史的願望作祟,仔細揣摩起來,甚至有幾分建造圖書巴別塔的意味。無盡的閱讀欲望驅使背後,其實是人類征服時間和記憶的恐懼。
其實每個讀書人都希望能有自己的一間足夠大而且藏書足夠多的圖書室,從這個很簡單的角度來說,曼古埃爾讓我羨慕不已。在一個公共領域基本被遮蔽的時代中,能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私人領域,心騖八極,神遊萬仞,在書與書之間,歷史與歷史之間,記憶與記憶之間毫無阻礙地漫遊,這種愉悅已經無言可表。博爾赫斯曾經說,讀一本古書,最大的享受就是可以窺見從成書之日起到現今的全部歲月。對過去的熱情,持續到如今,時間似乎被濃縮壓乾,在文字之間,在發黃的封皮和紙頁的劃痕中隱約可見,這種神話一般的美妙每個愛書人估計都會心有所感吧。
在《夜晚的書齋》中,曼古埃爾不厭其煩地歷數自己的藏書,這種炫耀我們不認為淺薄,反而值得羨慕。正如彼特拉克所言,我的圖書室是充滿學問的,儘管它屬於一個沒有學問的人。看似是謙卑之詞,其實得意之情已經溢於言表了吧?
其實藏書讀書的樂趣說了半天,有個疑問一直沒有解答:為什麼非要是夜晚的書齋?我的回答是,我喜歡在夜裡閱讀,孤獨,寫作。而曼古埃爾說,因為只有在天黑之後,智慧之神密涅瓦的貓頭鷹才會起飛,“夜深人靜時,我從日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眼睛和手恣意在整齊的行列中漫遊,恢復了混沌狀態。如果早晨的書齋象徵這個世界一本正經而且自以為是的秩序,那么夜間的書齋似乎就沉浸在這個世界本質上混沌的一片歡樂之中。”白天的書齋是秩序的領域,而夜晚的書齋在黑暗的縫隙里,無言地在靜默中收穫著靈魂的孤獨與智慧的豐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