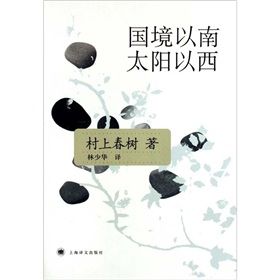內容簡介
《國境以南太陽以西》講述了37歲的男主人公,在東京市區擁有兩家興旺的酒吧,還有嬌美的妻子,可愛的女兒,他是一位真正的成功人士。但是,他的內心還是感到飢餓乾渴,事業和家庭都填補不了,而讓他那缺憾的部分充盈起來的,是他國小時的女友島本。島本不願吐露自己的經歷、身份、只希望他就這樣接受眼前的自己,只把她當成國小時那個愛古典樂的女孩。然而,就在他接受了這不可能接受的條件時,兩人卻在箱根別墅度過了銷魂的一夜。翌晨,她一去杳然、再無蹤跡可尋了。作者簡介
村上春樹(1949—),日本著名作家。京都府人。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1979年以處女作《且聽風吟》獲群像新人文學獎。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鳥行狀錄》、《海邊的卡夫卡》等。作品被譯介至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各地深具影響。前言
“國境以南太陽以西”有什麼林少華
這部小說也許可以稱為((挪威的森林》(以下簡稱《挪》)的翻版或者續篇。《挪》是三十七歲的“我”對於青春時代同直子和綠子戀愛過程的回顧,而在《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以下簡稱《國境》)中,故事主要發生在主人公三十六那年。這一年是主人公“我”(初君)結婚第六年,已經有了兩個女兒,兩家酒吧開得紅紅火火,正是一般世人所說的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的中年男士。這時“直子”(島本)忽然出現了,依然那么美麗動人,那么嫻靜優雅,那么若即若離,於是浪漫發生了。而在同“我”度過一個刻骨銘心蕩神銷魂的夜晚之後,“直子”悄然離去,再無訊息……
不過,就寫作情況來說,《國境》同《挪》基本沒有直接關聯,有直接關聯的莫如說是《奇鳥行狀錄》。村上春樹結束三年旅歐生活回到日本不久便去了美國,從1992年2月住到1995年8月。前兩年半是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應邀在名校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Visitinglecturer),實際上更近似駐校作家。住處由學校提供,只偶爾給學日本文學的美國研究生講講日本現代文學作品,時間很充裕一加之環境幽靜,不需要同更多的人打交道,得以專心從事創作,用一年多一點時間寫出了《奇鳥行狀錄》第一部和第二部。寫完後他總覺得若干地方有欠諧調,於是讓夫人陽子看一遍談談感想——以往也經常這樣——結果夫人也不很滿意,說有趣固然有趣,但枝蔓太多,致使故事主幹有些亂,勸他修剪一下。隨即村上和夫人又看了好幾次,反覆討論,最後決定刪除三章,並根據夫人的建議以這三章為基礎構思另一個故事,這就是《國境》。“從過程來看,《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的誕生很大程度上恐怕同妻的suggestion(示意)有關……當然,若經過一段時間,即使沒有她的建議,我想我也會進行同樣的作業。或許多少有些反覆彎路,但到達的地點必然是同一地點。不過她的意見可能大幅削減了我獨自作業所需時間。具體說來,《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的主人公初君同《奇鳥行狀錄》的主人公岡田亨原本是同一人物。而且,《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第一章幾乎照搬了《奇鳥行狀錄》原來的第一章。”因此,將二者聯繫起來讀是饒有興味的。自然,作為故事完全是兩個故事。至少,《奇鳥行狀錄》是主人公的老婆有外遇,而《國境》是男主人公本人有外遇。
同村上其他小說相比,《國境》最明顯的特點是其中出現了家窿。村上創作之初就宣稱不寫家庭,不願意受包括家庭在內的所有“團體”的束縛,甚至為此而不要孩子,因為沒有孩子光夫妻兩人他認為是不能稱之為家庭的。但這部小說、僅僅這部小說寫了家庭,而且是相當完整的家庭,妻子直到最後也沒有離婚或者失蹤,屬於地地道道的日本式賢妻良母。小孩也有了,一大一小兩個女兒。“我每天早上開車把大女兒送去幼稚園,用車內音響裝置放兒歌兩人一起唱,然後回家同小女兒玩一會兒,再去就近租的小辦公室上班。周末四人去箱根別墅過夜。我們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可以說,這是一幅相當典型的中產階級“雅皮”生活場景。連岳父也登場了,並且是很不錯的岳父,借錢幫他開了酒吧,使他從一家不起眼的出版社的不起眼的教科書編輯變成了雇用三十多名員工的兩家酒吧的老闆,甚至勸他不妨及時風流: “我在你這個年齡也蠻風流著哩,所以不命令你不許有外遇。跟女兒的丈夫說這個未免離譜,但我以為適當玩玩反倒有好處,反倒息事寧人。適當化解那東西,可保家庭和睦,工作起來也能集中精力。所以,即使你在哪裡跟別的女人睡,我也不責怪你。”但要“我”記住不可找無聊女人,不可找糊塗女人,不可找太好的女人,並進一步提出三點注意事項:切不可給女人弄房子,回家時間最晚不超過半夜兩點,不可拿朋友作擋箭牌。如此言傳身教的岳父,在中國恐怕絕對找不出來,相反的倒比比皆是。村上把這個都寫了進去,應該說對家庭及其周邊寫得相當深入了。
不久,主人公果真“風流”了,不過這並非岳父開導的結果,也不是一般情況下的外遇,而是背景比較特殊的外遇,其中包含的兩個方面的問題,不妨認為是這部小說的主題。
首先是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問題。主人公的過去存在三個女子。一個是島本,當時她還是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兩人在一起聽了納特·金·科爾唱的《國境以南》。國小畢業後,因所上國中不同,兩人分開了。“不去見島本之後,我也經常懷念她。在整個青春期這一充滿困惑的痛苦的過程中,那溫馨的記憶不知給了我多少次鼓勵和慰藉。很長時間裡,我在自己心中為她保存了一塊特殊園地。就像在餐館最裡邊一張安靜的桌面上悄然豎起‘預定席’標牌一樣,我將那塊園地只留給了她一個人,儘管我推想再不可能見到她了。”由於當時兩人都還是國小生,交往不具有真正的性因素。第二個女子是“我”的高中同學泉。泉儘管“不會給我同島本一樣的東西”,也不怎么漂亮,但有一種自然打動人心的毫不矯情的東西。加之年齡的關係,同泉的交往明顯帶有性方面的需求。“我”對泉說:“不想做那種事不做也可以,可我無論如何都想看你的裸體,什麼也不穿地抱你,我需要這樣做,已經忍無可忍了!”實際上“我”也那樣做了。第三個女子是泉的表姐,第一次見面“我”就想和她睡。實際交往兩個月時間裡,“我同泉的表姐只管大幹特乾,幹得腦漿都像要融化了”——兩人只有性關係,雙方並不相愛,都沒有發展戀人關係的念頭。後來此事被泉知道了,兩人關係就此終止。島本、泉、泉的表姐,這三個女子構成了主人公的過去。無論“我”去哪裡,無論“我”做什麼,過去都如頭頂的一片雲一樣投下陰影。
島本在“我”三十六歲時驀然出現在他的酒吧里而又暫時消失之後,他這樣想道:
在別人看來,這或許是十全十美的人生,甚至在我自己眼裡有時都顯得十全十美。我滿腔熱情地致力於工作,獲得了相當多的收入。在青山擁有三室一廳住房,在箱根山中擁有不大的別墅,擁有寶馬和切諾基吉普,而且擁有堪稱完美的幸福的家庭。我愛妻子和女兒,我還要向人生尋求什麼呢?縱使妻子和女兒來我面前表示她們想成為更好的妻子和女兒、想更被我疼愛,希望我為此不客氣地指出下一步她們該怎么做,恐怕我也沒什麼好說的。我對她們確實沒有一點不滿,對家庭也沒有任何不滿,想不出比這更為舒適的生活。
然而在島本不露面之後,我不時覺得這裡活活成了沒有空氣的月球表面。
島本代表過去,或者說是主人公主要的過去。島本即“過去”的出現和某一段時間“不再露面”,使得主人公“十全十美”的現在、現在的處境成了“沒有空氣的月球表面”。“我”必須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在島本與妻之間——作出選擇,沒有中間,島本一再強調“我身上沒有中間性的東西”。一句話,非此即彼。而這樣的選擇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會碰到。在這個意義上,《國境》是與現在息息相關的、很有日常性和現實性的故事。這點也和作者的大部分作品有所不同。
然而,《國境》又很難說是以《挪》那樣的現實主義手法寫成的小說。下面就第二個方面探討一下:現實與虛幻的問題。寫《國境》期間,村上一直在考慮《雨月物語》裡面的故事。《雨月物語》是江戶時期上田秋成(1734l1809)寫的志怪小說,九篇故事中有六篇脫胎於《剪燈夜話》和《白蛇傳》等中國古代傳奇、話本,一個共通的特點是主人公自由遊走於陰陽兩界或者實境與幻境、自然與超自然之間。村上說,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在二者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恐怕是不可能的,也幾乎是沒有意義的。“作為我,想把那種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界線或者覺醒與非覺醒之間的界線不分明的作品世界以現代物語這一形式表現出來”。而《國境》便是收納這一主題的恰到好處的容器。在這部小說中,說到底“我”的過去只能通過“島本”這個喻體(metaphoric)才能呈現,只能通過這樣的非現實非正常的存在加以勾勒。村上在為收人《村上春樹全作品1990--2000~(講談社2003年版)的《國境》寫的後記(“解題”)中就此進一步寫道:
島本是實際存在的嗎?這應該是這部作品最重要的命題之一。她是否實際存在並非作者要在此給出具體答案的問題。在作品中島本當然存在。她活著、動著、說話、性交。她推動故事的發展。至於她是否實際存在,則是作者無法判斷或者沒資格判斷的問題。如果你覺得島本實際存在,她就實際存在於那裡,有血有肉,一口口呼吸。倘若你感到她根本不存在,那么她便不在那裡,她就純粹成了編織初君的一個精緻幻想。她實際存在與否,應該是由你和島本(或者對於你的島本式人物)之間決定的問題。作品這東西不過是凸顯個性的一個文本而已。
於是我們在《國境》中看到了虛實兩個島本:一個是十_歲時樨“我,,的手握了十秒的島本,一個是“我”二十八歲時在東京街頭緊隨不合的穿紅色風衣的仿佛島本的島本;一個是時隔二十三年忽然出現在酒吧里“笑得非常完美”的島本,一個是拉“我”去遠離東京的河邊灑下嬰兒骨灰的島本;一個是在箱根別墅同“我”長時間實實在在交合的島本,一個是翌日清晨在枕頭上留下腦形凹坑而蹤影皆無的島本。一句話,一個是此側現實世界中的島本,一個是“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的島本。而我就隨著兩個島本往來並迷失於現實和虛幻之間。其中有兩個典型的細節。一個是那個謎一樣的男人為了阻止他尾隨島本而給他的裝有十萬日元的信封后來從抽屜里不翼而飛;另一個是島本送給他的那張舊唱片隨著島本從箱根別墅的消失而無從找見。這愈發使得他無法融入現實,感覺上就好像被孤零零地拋到沒有生命跡象的乾裂的大地,紛至沓來的幻影將周圍所有色彩吮盡吸乾。不僅如此,主人公還對自己本身和自己置身其間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產牛虛幻之感:
極為籠統地說來,我們是對貪婪地吞噬了戰後一度風行的理想主義的、更為發達、更為複雜、更為練達的資本主義邏輯唱反調的人。然而我現在置身的世界已經成了由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邏輯所統領的世界。說一千道一萬,其實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被這一世界連頭帶尾吞了進去。在手握寶馬方向盤、耳聽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號燈的時間裡,我驀然浮起疑念: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準備好的場所按某人設計好的模式生活。我這個人究竟到何處為止是真正的自己,從哪裡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盤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不用說,這一連串的追問來自更大意義上的過去與現在的齟齷、現實與理想的錯位。這樣的追問只能進一步加深對自己、對自身處境和現實社會的幻滅感,激起從中逃離的欲望。那么逃去哪裡呢?逃去“國境以南太陽以西”那個虛幻的世界,而島本無疑是那個世界的化身——“島本,我的最大問題就在於自己缺少什麼,我這個人、我的人生空洞洞缺少什麼,失卻了什麼。缺的那部分總是如饑似渴。那部分老婆孩子都填補不了,能填補的這世上只你一人。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那部分充盈起來。充盈之後我才意識到:以前漫長的歲月中自已是何等飢餓何等乾渴。我再也不能重回那樣的世界。”換言之,主人公成長的過程就是力圖填補自己缺失部分的過程。他所真正傾心的女子也都首先具有這方面的功能。他和十二歲時的島本在一起,是為了彌補自己以至雙方的“不完整性”;他高中時代的戀人泉雖然長得不算怎么漂亮,但有一種自然打動人心的溫情;他當初對妻有紀子所以一見傾心,也並不是因為她長得漂亮,而是因為從其長相中明確感覺到了“為我自己準備的東西”。而最能填補他缺失部分即心靈空缺——在物質生活上他並不缺少什麼——的人當然仍是島本,只有島本才能使他徹底充盈起來。所以他才最後下決心同島本從頭開始,
“再不重回那樣的世界”。然而歸終他不得不重回那樣的世界。他和妻有紀子言歸於好的夜晚,妻問他想什麼,他說“想沙漠”。也就是說,重返原來的現實世界就是重返沙漠,因為“大家都活在那裡,真正活著的是沙漠”。如果不回沙漠,那就只能忍受孤獨,而他再不想孤獨,“再孤獨,還不如死了好”。很明顯,村上在這裡已不再欣賞和把玩孤獨了,而在尋求“國境以南太陽以西”而不得的情況下,在孤獨與沙漠之間選擇了沙漠,選擇了現實世界。他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後記(“解題”)中最後這樣寫道:
我本身當然不認為《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屬於“文學性退步”之作。我是在向《奇鳥行狀錄》那部超長小說攀登的途中作為間奏曲寫這部作品的,由此得以一一確認自己的心之居所,在此基礎上我才得以繼續向《奇鳥行狀錄》的頂峰攀登。在這個意義上,這部作品在我的人生當中(請允許我說得玄乎一點,即我的文學人生當中)自有其價值,有其固有的意味。
丁亥仲春晴日於窺海齋
時青島丁香流霞櫻花堆雪
精彩書摘
1我生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即二十世紀下半葉第一年第一個月第一個星期。說是有紀念性的日子也未嘗不可。這樣,我有了“初”這樣一個名字。不過除此之外,關於我的出生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父親是一家大證券公司的職員,母親是普通家庭主婦。父親曾因“學徒出陣”被送去新加坡,戰後在那裡的收容所關了一段時間。母親家的房子在戰爭最後那年遭到B-29的轟炸,化為灰燼。他們是被長期戰爭所損害的一代。
但我出生時,所謂戰爭餘波已經幾乎沒有了。住處一帶沒有戰火遺痕,占領軍的身影也見不到了。我們住在這和平的小鎮上由父親公司提供的住宅里。住宅是戰前建造的,舊是舊了些,但寬敞還是夠寬敞的。院子裡有高大的松樹,小水池和石燈籠都有。
我們居住的鎮,是十分典型的大都市郊外的中產階級居住地。那期間多少有些交往的同學,他們全都生活在較為整潔漂亮的獨門獨戶里,大小之差固然有之,但都有大門,有院子,院子裡都有樹。同學們的父親大半在公司工作,或是專業人士。母親做工的家庭非常少見。大部分人家都養貓養狗。至於住宿舍或公寓裡的人,當時我一個也不認識。後來雖然搬到了鄰鎮,但情形大同小異。所以,在去東京上大學之前,我一直以為一般人都系領帶去公司上班,都住著帶院子的獨門獨戶,都養貓養狗。無從想像——至少不伴隨實感——此外的
生活是什麼樣子。
每家通常有兩三個小孩。在我所生活的世界裡兩三個是平均數目。我可以在眼前推出少年時代和青春期結識的幾個朋友的模樣,但他們無一不是兩兄弟或三兄弟里的一員。不是兩兄弟即是三兄弟,不是三兄弟即是兩兄弟,簡直如刻板印刷一般。六七個小孩的家庭誠然少,只有一個小孩的就更少了。
不過我倒是無兄無弟只我自己。獨生子。少年時代的我始終為此有些自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自己可謂特殊存在,別人理直氣壯地擁有的東西自己卻沒有。
小時候,“獨生子”這句話最讓我受不了,每次聽到,我都不得不重新意識到自己的不足。這句話總是把指尖直接戳向我:你是不完整的!
獨生子受父母溺愛、體弱多病、極端任性——這在我居住的天地里乃是不可撼動的定論,乃是自然規律,一如山高則氣壓下降、母牛則產奶量多一樣。所以我非常不願意被人問起兄弟幾個。只消一聽無兄無弟,人們便條件反射般地這樣想道:這小子是獨生子,一定受父母溺愛、體弱多病、極端任性。而這種千篇一律的反應使我相當厭煩和受刺激。但真正使少年時代的我厭煩和受刺激的,是他們所說的完全屬實。不錯,事實上我也是個被溺愛的體弱多病的極端任性的少年。
我就讀的學校,無兄無弟的孩子的確罕有其人。國小六年時間我只遇上一個獨生子,所以對她(是的,是女孩JL)記得十分真切。我和她成了好朋友,兩人無話不談,說是息息相通也未嘗不可。我甚至對她懷有了愛情。
她姓島本,同是獨生子。由於出生不久便得了小兒麻痹,左腿有一點點跛,並且是轉校生(島本來我們班是五年級快結束的時候)。這樣,可以說她背負著很大的——大得與我無法相比的——精神壓力。但是,也正因為背負著格外大的壓力,她要比我堅強得多,自律得多,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叫苦示弱。不僅口頭上,臉上也是如此。即使事情令人不快,臉上也總是帶著微笑。甚至可以說越是事情令人不快,她越是面帶微笑。那微笑實在妙不可言,我從中得到了不少安慰和鼓勵。“沒關係的,”那微笑像是在說,“不怕的,忍一忍就過去了。”由於這個緣故,以後每想起島本的面容,便想起那微笑。
島本學習成績好,對別人大體公平而親切,所以在班上她常被人高看一眼。在這個意義上,雖說她也是獨生子,卻跟我大不一樣。不過若說她無條件地得到所有同學喜歡,那也未必。大家固然不欺負她不取笑她,但除了我,能稱為朋友的人在她是一個也沒有。
想必對他們來說,她是過於冷靜而又自律了,可能有人還視之為冷淡和傲慢。但是我可以感覺出島本在外表下潛伏的某種溫情和脆弱——如同藏貓貓的小孩子,儘管躲在深處,卻又希求遲早給人瞧見。有時我可以從她的話語和表情中一晃兒認出這樣的影子。
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島本不知轉了多少次校。她父親做什麼工作,我記不準確了。她倒是向我詳細說過一回,但正如對身邊大多數小孩一樣,我也對別人父親的職業沒什麼興趣。記得大約是銀行、稅務或公司破產法方面專業性質的工作。這次搬來住的房子雖說也是公司住宅,卻是座蠻大的洋房,四周圍著相當氣派的齊腰高的石牆,石牆上長著常綠樹籬,透過點點處處的間隙可以窺見院裡的草坪。
島本是個眉目清秀的高個子女孩,個頭同我不相上下,幾年後必定出落成十分引人注目的絕對漂亮的姑娘。但我遇見她的當時,她還沒獲得同其自身資質相稱的外觀。當時的她總好像有些地方還不夠諧調,因此多數人並不認為她的容貌有多大魅力。我猜想大概是因為在她身上大人應有的部分同仍然是孩子的部分未能協調發展的緣故,這種不均衡有時會使人陷入不安。
由於兩家離得近(她家距我家的的確確近在咫尺),最初一個月在教室里,她被安排坐在我旁邊。我將學校生活所必需知道的細則——講給她聽——教材、每星期的測驗、各門課用的文具、課程進度、掃除和午間供飯值班等等。一來由住處最近的學生給轉校生以最初的幫助是學校的基本方針,二來是因為她腿不好,老師從私人角度把我找去,叫我在一開始這段時間照顧一下島本。
就像一般初次見面的十一二歲異性孩子表現出的那樣,最初幾天我們的交談總有些彆扭發澀,但在得知對方也是獨生子之後,兩人的交談迅速變得生動融洽起來。無論對她還是對我,遇到自己以外的獨生子都是頭一遭。這樣,我們就獨生子是怎么回事談得相當投入,想說的話足有幾大堆。一見面——吊然算不上每天——兩人就一起從學校走路回家,而且這一公里路走得很慢(她腿不好只能慢走),邊走邊說這說那。說話之間,我們發現兩人的共同點相當不少。我們都喜歡看書,喜歡聽音樂,都最喜歡貓,都不擅長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感受。不能吃的食物都能列出長長一串,中意的科目都全然不覺得難受,討厭的科目學起來都深惡痛絕。如果說我和她之間有不同之處,那就是她遠比我有意識地努力保護自己。討厭的科目她也能用心學且取得很不錯的成績,而我則不是那樣。不喜歡的食物端上來她也能忍著全部吃下,而我則做不到。換個說法,她在自己周圍修築的防體比我的高得多牢固得多,可是要保護的東西都驚人地相似。
我很快習慣了同她單獨在一起。那是全新的體驗。同她在一起,我沒有同別的女孩子在一起時那種心神不定的感覺。我喜歡同她搭伴走路回家。島本輕輕拖著左腿行走,途中有時在公園長椅上休息一會兒,但我從未覺得這有什麼妨礙,反倒為多花時間感到快樂。
我們就這樣單獨在一起打發時間。記憶中周圍不曾有人為此奚落我們。當時倒沒怎么放在心上,但如今想來,覺得頗有點不可思議。因為那個年齡的孩子很喜歡拿要好的男女開心起鬨。大概是島本的為人所使然吧,我想。她身上有一種能引起別人輕度緊張的什麼,總之就是說她帶有一種“不能對此人開無聊玩笑”的氣氛。就連老師看上去有時都對她感到緊張。也可能同她腿有毛病不無關係。不管怎樣,大家都好像認為拿島本開玩笑是不太合適的,而這在結果上對我可謂求之不得。
島本由於腿不靈便,幾乎不參加體操課,郊遊或登山時也不來校,類似夏季游泳集訓的夏令營活動也不露面。開運動會的時候,她總顯出幾分局促不安。但除了這些場合,她過的是極為普通的國小生活。她幾乎不提自己的腿疾,在我記憶範圍內一次也不曾有過。即使在和她放學回家時,她也絕對沒說過例如“走得慢對不起”的話,臉上也無此表現。但我十分清楚,曉得她是介意自己的腿的,惟其介意才避免提及。她不大喜歡去別人家玩,因為必須在門口脫鞋。左右兩隻鞋的形狀和鞋底厚度多少有些不同——她不願意讓別人看到。大約是特殊定做的那種。我所以察覺,是因為發現她一到自己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鞋放進鞋箱。
島本家客廳里有個新型音響裝置,我為聽這個常去她家玩。音響裝置相當堂而皇之。不過她父親的唱片收藏卻不及音響的氣派,LP唱片頂多也就十五六張吧,而且多半是以初級聽眾為對象的輕古典音樂,但我還是左一遍右一遍反反覆覆聽這十五張唱片,至今都能真可謂真真切切巨細無遺地——記起。
照料唱片是島本的任務。她從護套里取出唱片,在不讓手指觸及細紋的情況下雙手將其放在唱片盤上,用小毛刷拂去唱針上的灰塵,慢慢置於唱片之上。唱片轉罷,用微型吸塵器吸一遍,拿毛布擦好,收進護套,放回架上原來的位置。她以極其專注的神情一絲不苟地進行父親教給她的這一系列作業,眯起眼睛,屏息斂氣。我總是坐在沙發上目不轉睛地注視她這一舉一動。唱片放回架上,島本這才沖我露出一如往常的微笑,而那時我每每這樣想:她照料的並非唱片,而大約是某個裝在玻璃瓶里的人的孱弱魂靈。
我家沒唱機也沒唱片,父母不是對音樂特別熱心的那一類型,所以我總是在自己房間裡,撲在塑膠殼AM收音機上聽音樂。從收音機里聽到的大多是搖滾一類。但島本家的輕古典音樂我也很快喜歡上了。那是“另一世界”的音樂。我為其吸引大概是因為島本屬於那“另一世界”。每星期有一兩次我和她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著她母親端來的紅茶,一邊聽羅西尼的序曲集、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和《培爾·金特》送走一個下午。她母親很歡迎我來玩,一來為剛剛轉校的女兒交上朋友感到欣喜,二來想必也是因為我規規矩矩而且總是衣著整潔這點合了她的心意。不過坦率地說,我對她母親卻總好像喜歡不來。倒不是說有什麼具體討厭的地方,雖然她待我一直很親切,但我總覺得其說話方式里多少有一種類似焦躁的東西,使得我心神不定。
她父親收集的唱片中我最愛聽的是李斯特鋼琴協奏曲。正面為號,反面為2號。愛聽的理由有兩點:一是唱片護套格外漂亮,二是我周圍的人裡邊聽過李斯特鋼琴協奏曲的一個也沒有,當然島本除外。這委實令我激動不已。我知曉了周圍任何人都不知曉的世界!這就好比惟獨我一個人被允許進入秘密的花園一樣。對我來說,聽李斯特的鋼琴協奏曲無疑是把自己推上了更高的人生階梯。
況且又是優美的音樂。起初聽起來似乎故弄玄虛、賣弄技巧,總體上有些雜亂無章,但聽過幾遍之後,那音樂開始在我的意識中一點點聚攏起來,恰如原本模糊的圖像逐漸成形。每當我閉目凝神之時,便可以看見其鏇律捲起若干漩渦。一個漩渦生成後,又派生出另一個漩渦,另一漩渦又同別的漩渦合在一起。那些漩渦——當然是現在才這樣想的——具有觀念的、抽象的性質。我很想把如此漩渦的存在設法講給島本聽,但那並非可以用日常語言向別人闡述的東西,要想準確表達必須使用種類更加不同的語言,而自己尚不知曉那種語言。並
且,我也不清楚自己所如此感覺到的是否具有說出口傳達給別人的價值。遺憾的是,演奏李斯特協奏曲的鋼琴手的名字已經忘了,我記得的只是色彩絢麗的護套和那唱片的重量。唱片沉甸甸的重得出奇,且厚敦敦的。
西方古典音樂以外,島本家的唱片架上還夾雜納特·“金”·科爾和平·克勞斯比的唱片。這兩張我也著實聽個沒完。克勞斯比那張是聖誕音樂唱片,我們聽起來卻不管聖誕不聖誕。至今都覺得不可思議:居然那么百聽不厭!
聖誕節臨近的十二月間的一天,我和島本坐在她家客廳沙發上像往常那樣聽唱片。她母親外出辦事,家中除我倆沒有別人。那是個彤雲密布、天色黯淡的冬日午後,太陽光仿佛在勉強穿過沉沉低垂的雲層時被削成了粉末。目力所及,一切都那么呆板遲鈍,沒有生機。薄暮時分,房間裡已黑得如暗夜一般。記得沒有開燈。惟有取暖爐的火苗紅暈暈地照出牆壁。納特·“金”·科爾在唱《裝相》(《PRKFEND》)。英文歌詞我當然完全聽不懂,對我們來說那不過類似一種咒語。但我們喜歡那首歌。翻來覆去聽的時間裡,開頭部分可以鸚鵡學舌地唱下來了:Pretendyouarehappywhenyou’reblue.Itisn’tveryhardtodo.
現在意思當然明白了:“痛苦的時候裝出幸福相,這不是那么難做到的事”。簡直就像她總是掛在臉上的迷人微笑。這的確不失為一種想法,但有時又是非常難以做到的。
島本穿一件圓領藍毛衣。她有好幾件藍毛衣。大概是她喜歡藍毛衣吧,或者因為藍毛衣適於配上學時穿的藏青色短大衣也未可知。白襯衫的領子從毛衣領口裡探出,下面是格子裙和白色棉織襪。質地柔軟的貼身毛衣告訴了我她那小小的胸部隆起。她把雙腿提上沙發,摺疊在腰下坐著。一隻胳膊搭在沙發背上,以注視遠方風景般的眼神傾聽音樂。
“噯,”她說,“聽說只有一個孩子的父母關係都不大好,可是真的?”我略微想了想,但弄不明白這種因果關係。“在哪裡聽說的?”
“一個人跟我說的,很早以前,說是因為關係不好所以只能有一個孩子。聽的時候傷心得不行。”
“哪裡。”我說。“你爸爸媽媽關係可好?”
我一下子答不上來。想都沒想過。“我家嘛,媽媽身體不怎么結實。”我說,“倒是不太清楚,聽說生孩子身體負擔很大很大,所以不行的。”
“沒想過有個兄弟該有多好?”
“沒有。”
“為什麼?為什麼沒想過?”
我拿起茶几上的唱片護套看。但房間太暗了,看不清套上印的字。我把護套重新放回茶几,用手腕揉了幾下眼睛。以前給母親同樣問過幾次,每次我的回答都既未使母親高興也沒讓母親難過。母親聽了我的回答後只是做出費解的神情,但那至少對我來說是非常坦率的、誠實的回答。
我的回答很長,但未能準確無誤表達自己的意思。歸根結蒂我想說的是:“這裡的我一直是在無兄無弟的環境中成長的,假如有個兄弟,我應該成為與現在不同的我。所以這裡的我如果盼望有個兄弟,我想那是違背自然的。”因此我覺得母親的提問總好像沒什麼意義。
我把那時的回答同樣向島本重複一遍。重複完,島本定定地注視著我的臉。她的表情里有一種撩動人心弦的東西。那東西——當然這是事後回想時才感覺到的——帶有肉慾意味,仿佛能把人心的薄膜一層層溫柔地剝離下去。至今我仍清晰記得她那伴隨著表情變化而細微地改變形狀的薄唇,記得那眸子深處一閃一滅的隱約光亮。那光亮令我想起在細細長長的房間盡頭搖曳不定的小小燭光。
“你說的,我好像能明白。”她用蠻帶大人氣的平靜的聲音說。
“真的?”
“嗯。”島本應道,“世上的事,有能挽回的有不能挽回的,我想。時間就是不能挽回的。到了這個地步,就再也不能挽回了啊。是這樣看的吧?”
我點點頭。
“一定時間過去後,好多好多事情都硬邦邦凝固了,就像水泥在鐵桶里變硬。這么一來,我們就再也不能回到老地方了。就是說你的意思是:你這堆水泥已經完全變硬了,除了現在的你再沒有別的你了,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