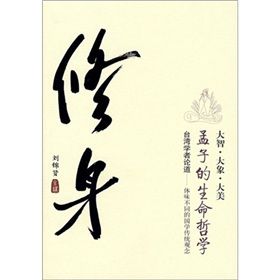作者簡介
劉錦賢,1953年生,台灣彰化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國文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中學中文教師,台北科技大學講師、副教授,現任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張橫渠思想研究》《儒家保生觀與成德之教》《易道之“懼以終始”論述》《莊子天人境界之道路》《眾生病則菩薩病》《康德美學析論》等。目錄
導論第一章心性內涵
性善之說與生之謂性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人皆可以為堯
舜 性之與反之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第二章修德要領
養心莫善於寡慾
養氣與知言
居移氣,養移體 求其放心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知命與立命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操心危,慮患深
仁在乎熟 豪傑自興
第三章價值評斷
義與利
王道與霸道
由仁義行與行仁義
執中與執一
天爵與人爵
大人與小人
大勇與小勇
狂狷與鄉原 養
志與養口體
所性與所樂
先聖后聖,其揆一也
第四章政治觀點
仁者無敵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與民同樂 富民而後能教民
任用賢才善士
樂天與畏天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君臣對等互動
善戰者服上刑
勞心與勞力
第五章處世態度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心繫濟世安民
天下溺,援之以道
不見召以為臣
說大人,則藐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
不以天下儉其親
相友以德,不可有挾
教亦多術 品鑑以論入
第六章人生理想結論
以大舜為盡倫之典範
以孔子集大成之聖格為歸趨
徵引書目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心性內涵性善之說與生之謂性
所謂“性”,專就天地萬物的個體說,而不就其整體說。任一個體,都有其存在的特質,因而能表現各種樣貌;個體存在的特質,或是其“存有”,便以“性”稱之。廣泛地說,物類莫不有其性,生物有之,無生物也有之。就哲學上對“性”的探索言,重點不放在植物以下之所謂“無情”者,而放在動物以上之所謂“有情”者,尤其是放在“人”這裡。人和其他動物有相似處,也有不同處。人固然有特殊的軀體結構和心智慧型力,而有別於其他動物;然而跟其他動物一樣,他也有飲食好色等生理的欲求及趨利避害等生物的本能。從同具動物性的欲求與本能上看,人和動物之間的差別並不大,不過人往往表現得更為精緻而已。那么人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區別在哪裡呢?就在人有道德意識,能從事道德實踐,這是其他動物所欠缺的。所以人存在的本質可以包括兩方面:一是形氣自然的存有,一是形上道德的存有。前者為人的動物性,這是人的“物性”;後者為人的道德性,這是人的“神性”。唯有從道德性看人,
才能真正把人和其他動物區別開來。
在孔子以前的古代文獻中,“性”字大抵指向自然存在的本質;自然存在的本質包括較低層次的本能、欲求及較高層次的氣質、天分。如《尚書?召誥》所謂“節性,惟日其邁”,是說要節制驕淫的欲求,才能使道德天天進步。《詩經?大雅?卷阿》所謂“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是說和樂平易的君子,讓你能滿足欲求,稱心如意。但這並不表示古人沒有道德意識,只是不從這裡說“性”而已。
《論語》中提到“性”字的只有兩個地方。其中之一見於《陽貨》2章孔子所說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歷來對“性相近”一語有不同的理解。程伊川說:“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二程遺書》第十八)他以為若從本原之義理上說性,每一個人都是相同的,不可說“相近”。因為說“相近”,內涵有所不同;這有所不同的“性”,只能從氣稟上說,不能從義理上說。王陽明說:“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陛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
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傳習錄?下》)他以為若從氣質上說性,則每一個人的性或剛或柔、或清或濁,差別很大,不能說彼此“相近”。所以孔子這裡所說的“性”,只能從義理上說,跟孟子所說“性善”的性同一指涉。從義理上說的性,每一個人都相同;陽明在這裡,是把“相近”解釋為“相同”。孟子說一個放失其良心的人,“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告子上》8章)。在這裡,“相近”是“相同”的意思,所以陽明對“性相近”的理解,並非無據。《論語》中“性”字另見於子貢所說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13章)在這裡,“性”與“天道”並稱,“天道”是形而上的,則“性”或許也是指形而上的義理之性,但不必然如此。不管孔子有言或無言,“天道”與從義理上說的“性”總是深奧難解,所以子貢說在這兩方面“不可得而聞”於孔子。然而從氣稟上說的“性”相當複雜,要通盤把握,也很不容易,則子貢“不可得而聞”之“性”,未嘗不可從這方面說。因為相關的章句太少,難以確定孔子言性的內涵。放寬來看,可以說孔子言性是義理、氣稟兩頭通的。
孔子所說的仁、義、禮等道德法則,都是從人內在真誠的道德心發出來的,可見道德心也是人的特質。孟子於是進一步說這能自發仁、義、禮等道德法則的道德心就是人的“性”。道德心是純善無惡的,所以說“性善”。孟子“道性善”,並不在否定人自然存在的本質,而是在通透人生價值的根源,使道德實踐有一形上的根據。孟子對於人有感官方面的生理欲求當然很清楚,但要人正視此一天生具備的道德本質,並將它體現出來,以表現人格的尊嚴。孟子說: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24章)
人的耳目對於美好聲色的喜愛,鼻口對於爽口香味的滿足,手足對於安樂舒適的需要,這些都是屬於其生理上的欲求,所以孟子首先承認這是性中所有之事。然而我們雖然有這些感官方面的需求,卻不一定能獲得相對的滿足,而會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也就是說在這裡有命存焉;命是人生的限制原則。因此講究修德的君子並不一味追求它,強調在這當中“有命焉”,而不說它是性。反之,仁在父子之間相互親愛,義在君臣之間的各盡其道,禮在賓主之間的往來恭敬,智對於賢者的深人了解,以及聖人對於天道的印證體會,這其中或有不能盡分處,或有不能透徹處,總難做得十全十美,也是有所限制的,所以孟子首先承認在這當中有命存焉。然而有德的君子體認到實踐這些德行是人的天職,唯有努力奉行天職,才能使心靈獲得快意滿足。也就是說仁義禮智等道德的實踐有其生命中內在的根源,所以說在這裡“有性焉”,而不說它是命。
與孟子同時的告子對性持傳統所謂自然存在之本質的看法,無法體會孟子“道性善”的真正用心及此一慧解在道德實踐上的價值,乃有與孟子對於人性觀點的論辯。在《孟子-告子上》前幾章孟子與告子的論辯中,雖然從純粹推理上看,孟子未必占上風,而告子也未必居下風;但是孟子對人性的洞見卻是告子覺察不到的。雖然如此,我們卻可以經由告子論性之言看出其對人性的觀點。告子說:
性,猶杞柳也;義,猶杯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杯椿。(《告子上》1章)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告子上》2章)
生之謂性。(《告子上》3章)
食、色,性也。(《告子上》4章)
性無善無不善也。(《告子上》6章)
在以上諸義中,“生之謂性”可以說是告子立說的總綱領,其他的論點,只是這一說法的輾轉引申。牟宗三先生說:“‘性’即是出生之生,是指一個體之有其存在而言。……‘生之謂性’意即:一個體存在時所本具之種種特性即被名日性。”
(《圓善論》,頁5~6)這裡所說的“個體存在”,乃是從生物學上看的自然生命之個體存在。告子所謂“生”,是就個體生命的存在說;?而其存在所本具的種種特質就是其性,所以說“生之謂性”。董仲舒說:“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這是告子“生之謂性”一語之詳說。所謂“如其生之自然之資”是說相應於那個體存在的自然資質;這自然資質就是個體存在的種種特質。從這個地方說性,不但異類之間不同,就是同類的不同個體之間也有所差別。然而自然生命有共同的生理需求,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食慾和色慾,所以告子言“食、色,性也”。食、色等欲求固然無善可言,也唯有在過甚其求而對己或對人造成傷害時才可說惡,所以純粹就食慾和色慾等生理需求本身來看,是道德地中性的,所以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既然只是以個體存在的自然資質看人性,則其中並無道德的成分,所以會把仁義等道德律則看成只是外在的行為規範,而可以被人認知。人們不能順其自然的資質,必須扭曲之,以符應外在的道德律則,才能表現道德的行為;猶如不能順著杞柳的枝條,必須加以人為的斫削,才能造成盛物的屈木容器。再者,人性固然可經由人為的造作表現善,當然也可以經由人為的造作表現惡;就好像瀠洄的流水一般,其向東流或向西流,初無定然,全看被引導向東方或被引導向西方而已。因此,若只從個體存在的自然資質看人性,則人性是中性的,而告子所說也是對的。
孟子經由親切的體證,確信仁義等道德法則是直接由人的真誠側怛之心發出來的,這真誠惻怛之心是人先天本來具備的特質;他就著這種特質以言性,所以說性善。孟子認為告子對人性的理解有所偏頗,想要扭轉之,於是對告子說: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杯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杯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杯椿,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乎!(《告子上》1章)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上》2章)
孟子認為依照告子以杞柳之造成杯椿以喻人性之造成仁義之說,將使天下人誤認為仁義不直接出乎人性而不看重它,甚至排斥它,這會造成對仁義莫大的傷害。再者,以湍水本來不一定要流向東或流向西,以喻人性本來不一定要表現善或表現惡,這樣作類比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果順著水性而不加干預,水是向下流去的;同樣,如果順著人性而不去攪亂,人是向善而趨的。對於原本低處地面的水如果拍擊它讓它濺起,可以高過人的額頭;對於原本低處山下的水,如果逼著它讓它逆流,也可以高居山上。這是情勢使然,不是水性原本如此。同樣的,順著人的天性,人的行為原本可以表現善;如果去攪亂他的天性,就會表現不善。告子與孟子都借水性以喻人性,兩人所說的好像都有道理,這是因為對人性採取不同的觀點。然而孟子心目中所認定之人性的道德性,卻是告子看不透的。
由此可知,在一個人生命的存在中,“自然之資”固然是其所本有,“仁義之心”也是其所本有,二者都是人天生而有的本質。告子說性,只是看到前者,未能肯定後者,因而有所偏頗;孟子說性,不但承認前者,更能肯定後者,所以完備周到。孟子已經看出人性的這兩個層面,不過尚未明顯地用不同的名稱標示出來而已。首先用不同的名稱將這兩種性明白標示出來的是張橫渠,他說: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誠明篇》)
以上所說,顯然本於孟子。“氣質之性”是就人的自然之資說,“天地之性”則就人的仁義之心說。“氣質之性”是隨著人的形軀而有的,“天地之性”則是先天本有的。“氣質之性”是說氣質本身這種性,或是從氣質方面所說的性。“天地之性”不是說天地本身之性,而是說與天地之精神同一之性,或是說從天地生化的源頭那兒來的性,這就是後來程子所說的“義理之性”。如是,以氣言的性與以理言的性便可作一顯明之對較。要讓天地之性存而不放,必須“善反”,也就是善於自我省察,以化去氣質的偏蔽。氣質的偏蔽既然是吾人所要對治的,所以“君子有弗性”。“弗性”就是孟子所說的“不謂之性”,不把它看做性;也就是說君子必以“天地之性”為人的真性。
君子對氣質之性“弗性”,只把天地之性或義理之性看做性;義理之性乃是就吾人純粹的道德心而說的,所以說“性善”。孟子所謂“性善”,是從價值判斷的源頭處言其善,這樣所說的善不與惡相對,乃是絕對的善,所以胡五峰說:“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又引其父胡安國的話說:“孟子道性善雲者,嘆美之辭,不與惡對也。”(《宋元學案?五峰學案》)性是成就天地鬼神的奧體,也是興發吾人德行的根源,最是純粹美好。這樣的純粹美好,固然不可說是惡,但也不是相對的善,所以說性善的善是“嘆美之辭”。牟宗三先生說:“孟子說性善,是就此道德心說吾人之性,那就是說,是以每人皆有的那能自發仁義之理的道德本心為吾人之本性,此本性亦可以說就是人所本有的‘內在的道德性’。”(《圓善論》,頁217)“道德心”是人的“本心”,本心“能自發仁義之理”,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孟子所說“性善”的“性”,就是人之“內在的道德性”。牟宗三先生又說:“孔子論仁,孟子論性,都是講道德的創造性。……德行之所以能純亦不已,是因為有一個超越的根據;這個超越的根據便是孟子所謂‘陛善’的‘性’。”(《中國哲學十九講》,頁431)“性善”之“性”是使德行純亦不已之“超越的根據”,所以說它是“道德的創造性”。“道德的創造性”不屬於“自然因果性”,而是屬於康德所說的“特種因果性”,也就是“意志的因果性”。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29章),就是從“意志的因果性”說的。
由此可知,孟子“性善”之說,本於孔子言仁,是就人的道德心以言性的;而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只是順著古來“性”字的用法,純就個體存在的自然資質而說性。二人言性所涉及的層面及其在人的道德實踐中之功能,迥然不同。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孟子以後的學者言性也有很多人采取告子的路線。荀子說:“性者,本始材朴也。”(《禮論》)性是個體原初的樸實材質,也就是個體的“自然之資”,它有好利、疾惡與耳目之欲、聲色之好等特質,人往往不加節制而流於惡,所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善是人為的造作,這與告子以扭曲人性來造成仁義的見解略同。董仲舒說:“性者,天質之朴也。”(《春秋繁露?實性》)性是人天生樸實的資質,也就是人的“自然之資”。他又說:“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