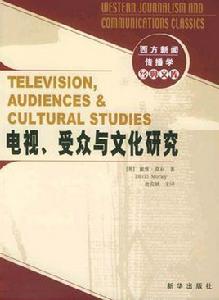人物經歷
求學期間:
達拉斯·斯麥茲( Dallas W. Smythe)1907年生於加拿大,侯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系受業,1928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1937年獲得博士學位。斯麥茲在學校里專心研究經濟史和理論史,他對政府工作報告和檔案很感興趣,認為它們提供了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的重要條件。美國政府對1890年經濟崩潰的聽證會文獻和有關交通行業的檔案,構成了他博士論文的基礎。畢業後的11年,斯麥茲一直在美國政府工作。在華盛頓的經歷使他獲得了套用社會科學的廣泛經驗。
初入社會:
1937年斯麥茲獲得博士學位後,先後到美國政府農業部、勞工部任政策分析員,使用並評估中央統計局的統計結果,同時,他開始與報紙和郵電等交通、通訊行業的工會打交道。在農業部和勞工部,他接觸到要求改良的進步黨人,包括政府公務員和工會領導人。與工人的合作使他對工人階級的狀況及其社會政治理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獲得了關於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行業壟斷巨頭的大量第一手資料,他親身感受到傳播行業勞動力變化的過程——由於新技術的影響,傳統上需要掌握特殊技能才能就業的無線電和電話工人的技術優勢日漸消失,他們開始感到非熟練工種對他們的職業衝擊。斯麥茲也親身體會到這些公司中激進的和保守的兩種工會之間在支持工人鬥爭方法上的分歧。
進入FCC:
1943年,斯麥茲被任命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的首席經濟學家,對廣播電視和電信政策發表建議和意見,直到1948年。美國的1934年《通訊法》將所有與電子傳播有關的行業都歸併FCC管理。斯麥茲去FCC講解傳播行業勞工關係爭議及其對策,並對電信費率提供諮詢建議。他希望,通過加入FCC,幫助這個獨立法規行政機構行使職能,影響FCC制訂和實施針對通訊和傳播壟斷的各項控制對策。他說,新政時期的FCC是一個可以服務於公共利益的地方。在FCC,斯麥茲指導了對廣播電視政策的研究。當時FCC正忙於分配電波頻率,斯麥茲參與了這項工作,並從商業利益集團捍衛私營者對廣播電視控制權的運動中獲得很大的教益,從而影響到他後來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他對媒介商品化的認識不能說與他這一段的經歷無關。任期即將結束時,他撰寫了《對常規廣播電視的經濟學研究》,還為FCC經典性的《廣播電視持照者的公共服務責任》(又稱“藍皮書”)撰稿。由於這些建議引起爭議,最終被束之高閣。
來到Illinois:
1948年,斯麥茲離開FCC,來到新成立的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創設了美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傳播學的博士班,因而可以被稱為傳播學的搖籃。許多知名學者曾在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逗留,包括著名傳播心理學家奧斯古德(Charles Osgood)、傳播批判學者格伯納(George Gerbner)、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席勒(Herbert Schiller)。斯麥茲在傳播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同時在商學系擔任經濟學教授。
斯麥茲的第一項研究檢驗了收看電視對家庭生活和閒暇時間的影響。在那個時期,電視剛剛進入美國人民的生活,正可以進行媒介介入前後的對照比較。斯麥茲採用的是實證研究方法,具體做法採用訪談法(用的是那個時代僅有的鋼絲錄音機)、日記法,和其他一些研究工具。雖然這一研究結果是供內部使用的,沒有公開發表過,但卻由此導致他指導美國教會組織對廣播電視影響進行的同類研究。在50年代初期,由於非美活動調查造成的肅殺氣氛,斯麥茲發現,只有教會內部還有足夠的言論自由。斯麥茲一直對公共廣播電視的問題有興趣。他將政治經濟學的知識用於對電子媒介的研究。他為美國教育廣播工作者聯合會(NAEB)擔任研究部主任,他的研究成果用於NAEB的院外活動和1950年末~1951年初FCC關於電視政策的聽證會舉證。那次,教育電視台和非商營電視台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1957年,他還作為加拿大皇家弗勒委員會的成員,對加拿大廣播電視的政策、內容和效果進行了研究。應該說,斯麥茲對傳播的研究,早期集中於廣播電視和電子傳播媒介。此時,他開始了對“客群商品理論”( audience commodity thesis)的研究。斯麥茲曾提到,他第一次正式提出這個思想是在1951年,他是在瓦薩(Vassar)學院消費者聯盟研究所的一次會議發言中提出的。當然,這一著名的思想經過多年的補充、發揮和完善。
回到故土:
1963年,斯麥茲全家做出了重大的決定——移居加拿大,回到他的家鄉薩斯喀徹溫省里賈納市。席勒接替了他在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教席。然而,1969年,席勒發表了著名的《大眾傳播與美帝國》一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激烈的爭議,校內的保守派對席勒施加了極大的壓力。於是,席勒也離開了。其後,斯麥茲的一個主要學生古拜克( Thomas Guback)完成了他對國際電影業作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出色博士論文,並繼承其導師衣缽,延續了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伊利諾伊大學的傳統。
斯麥茲回到加拿大後,在里賈納的薩斯喀徹溫大學任教。在里賈納的10年,斯麥茲繼續對客群商品問題的研究——他指出,客群是大眾傳播媒介的主要產品。1974年,他來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西蒙·弗雷澤( Simon Fraser)大學,與制度政治經濟學學者麥勒迪( William Melody)一道工作。此時,斯麥茲更加清晰地顯示出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特色,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電子傳播的政策、客群商品論及加拿大傳播業的依附狀況。他完成了主要學術著作——《依附之路:傳播、資本主義、意識和加拿大》(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1981),那是對決定加拿大傳播依附性的壟斷資本作辨證分析的經典之作。如今,西蒙·弗雷澤大學仍是加拿大傳播學理論研究、特別是對加拿大電子傳播研究方面的重要基地。
這段時期,斯麥茲參與加拿大政府和各種專業委員會的諮詢活動,出席關於傳播問題的各種聽證會,作為專家,他的研究常常導致媒介結構的改變。他還到處旅行。斯麥茲在美國的天普(Temple)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到過智利、中國、日本、英國和東歐國家。所到之處,他影響了一批學者。他的一個重大貢獻是開創了一個重要的傳播學派,培養了年輕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家,他的影響澤及幾代:包括稍後的席勒、他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最終,斯麥茲在西蒙·弗雷澤大學退休。1992年9月6日,他以85歲高齡去世。
兩度訪華:
斯邁思兩度訪華。
第一次是在“文革”期間,於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受加拿大藝術理事會資助訪問中國。通過觀察中國現實、訪問相關負責人、閱讀毛澤東的著作,並結合當時第三世界廣泛開展的現代化實踐以及美國現代化範式遭到的廣泛質疑,形成了他的報告《腳踏車之後是什麼》(After Bicycles, What?)。報告在他生前並未公開發表,他只是希望報告能作為來自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一位“家庭成員”的善意批評,因而通過外交渠道轉給了中國高層。此文的複印稿在西方批判傳播學界流傳甚廣。
第二次訪華則是再度向西方打開大門的1978年,來到開放伊始的上海。當時他敏銳地察覺到中國發展道路已經朝消費資本主義轉型。
學術貢獻
客群商品論:
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是商品化的社會。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由廣告費支持的大眾傳播媒介也自稱是商業媒介。那么,這種大眾媒介及其傳播商業所提供的商品究竟是什麼呢?
一般人認為,商業廣播電視的商品是標價出售的廣告時段,這是從銷售角度出發的;也有人認為,是電台播出的各種節目,這是從生產角度出發的。
但是,斯麥茲指出,廣告時段的價值是傳播產生的間接效果,而廣播電視節目則是“釣餌”性質的“免費午餐”,它們都不是廣播電視媒介生產的真正商品。早在1951年,他便提出,商營大眾傳播媒介的主要產品是客群的人力(注意力),由此奠定了其後他的客群商品理論。1977年他發表《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一文,標誌著客群商品理論的形成,引起了批判傳播學領域的熱烈辯論,並成為批判傳播學研究的一個主要分支。
根據斯麥茲對廣告驅動性大眾傳播商品形式的研究,節目在廣播電視中也許是有趣的,更經常是有用的部分;但大眾媒介生產的訊息、思想、形象、娛樂、言論和信息,卻不是它最重要的產品。它們都像20世紀出售啤酒的小店通常採用的方法一樣,是“免費午餐”這種“免費午餐”是用以吸引顧客登門飲酒的。以廣告費支持的電視媒介提供的“免費午餐”是喜劇、音樂、新聞、遊戲和戲劇,目的是引誘客群來到生產現場——電視機前。此時,測量客群的公司便能夠計算他們的數量多寡,並區分各色人等的類別,然後將這些數據出售給廣告者。媒介則根據“產品”(客群)的多寡和質量(年齡、性別、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標)的高低(也就是購買力的強弱)向廣告客戶收取費用。所以,媒介公司的使命其實是將客群集合併打包,以便出售。這便揭示了商業廣播電視的真正商品——儘管是臨時形成的商品——客群群體。它解釋了廣播電視時段具有價值的原因、廣告客戶和媒介公司之間的關係以及商業客群測量機構存在的理由,從而將媒介行業的本質牢牢地置於經濟基礎上。毫無疑問,這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具體運用。
這種與“常識”大相逕庭的觀點一經出現,有如空谷足音,立即引起了廣泛的注意,觸發了學者對客群的關注,並成為批判研究者研究媒介經濟流行的思路。
斯麥茲認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時間都是勞動時間。由此,他得出了下面在常人眼中看來更加驚人的結論:“免費午餐”的享用者不僅僅是消磨時光,他們還在工作——他們在創造價值。這種價值,最終是通過購買商品時付出的廣告附加費來實現的。其不公平處在於:客群在閒暇時間付出了勞動,為媒介創造了價值,但沒有得到經濟補償,反而需要承擔其經濟後果。這樣的觀點駭世驚俗;但這是對商業廣播電視、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美國的商業廣播電視獨特風景進行的極為醒目的分析。
然而,正如馬克思本人一樣,斯麥茲的分析也被批評為庸俗政治經濟學,批評者說他的觀點將意識形態降低為經濟基礎,同時,將能動的人降低為無生命的被動商品,是經濟決定論。一些持“積極客群”觀點的學者,特別是提出“使用—滿足”理論的學者,更是以大量的實證研究,竭力證實客群是主動參與媒介傳播和意義創造的生產者,而不是產品。
筆者認為,斯麥茲的“客群商品論”深刻地揭示了廣播電視媒介傳播的某種本質,但僅僅是一個方面——經濟的本質。儘管這種本質是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對傳播這種複雜的人類活動,學者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範式進行不同的解釋的。斯麥茲的學生和後繼者也發展了“客群商品論”。例如,有人提出,客群不僅僅是在工作,他們也在娛樂。他們在付出勞動(出場)和經濟(購買)代價的同時,也確實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特別是情感的慰藉,思想的交流,陪伴的作用等。
在諸多補充性的解釋中,莫斯考書中的“控制性商品”( cybernetic commodity)的概念最發人深省。莫斯考引證了米汗( Eileen R. Meehan)以接收率等信息服務機構的產品為中心的商品觀點。米翰認為,廣播電視生產的商品,並不是實際的客群(所謂客群的人頭數),而只是關於客群的信息(觀眾的多少、類別的構成、使用媒介的形態)。媒介與廣告客戶之間的交易,是通過收聽收視率行業進行的商品交換,而由這種交換過程產生的商品,是收聽收視率這種信息性、資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收聽收視率調查公司從事的,是這種信息的檢測過程。
傳播政治經濟學:
斯麥茲與加拿大傳播研究的先驅殷尼斯( Harold A. Innis)一樣,認為經濟制度和傳播體系之間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關係。傳播的流動對經濟的發展是關鍵的因素。傳播是各種經濟力量的核心。他“始終堅持,毫不動搖地傾全力於分析媒介制度及其與深層的經濟結構和社會體系的聯繫。”
斯麥茲堅信傳播在信息經濟社會中的核心地位,他提出,“傳播是世界所有矛盾聚集的焦點”
他認為,對社會過程,特別是對技術的考察,應該置於更大的政治經濟背景中。對傳播和媒介行為的考察,也應如此。傳播是重要然而常常被學者忽略的盲點,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架構中的盲點。此言既出,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中引起軒然大波,斯麥茲受到非難。特別是,斯麥茲還對傳播學研究有自己的獨特想法。
1954年,斯麥茲發表了《對傳播理論的觀察》( Some Observations on Communication Theory)一文。這篇文章是對傳播研究方法論的探討,1953年先是以義大利語發表在義大利刊物上,其後才以英文發表。在這篇文章中,他抨擊了傳播學研究中“邏輯實證科學理論的”方法,主張一種“制度歷史理論的”途徑,並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傳播學實證主義研究的權威人物克拉珀( Joseph Klapper)。
所謂“邏輯實證科學理論”是以自然科學的知識論和方法論來要求社會科學,用經驗觀察來建立有規律的理論體系,其要素是由反證的命題組成的。在早期,斯麥茲並不反對經驗調查的方法,他自己還進行過一些實證調查。但是,40年代以後,傳播學研究越來越多地採用政治學的民意調查方法,越來越趨向於行為主義的社會學、心理學,而放棄了歷史哲學等思辯性的研究方法和對社會制度的巨觀考察。隨著這種研究越來越趨向數量化和微觀化,斯麥茲便越來越反感“對所觀察的行為作簡約的、證偽的陳述,從而使智力活動的豐富性降低”這種經驗主義。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對理論和行為之間的辨證關係作廣闊的歷史分析,將其置於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較大框架中,進行批判、付諸實踐。面對來自“科學”的挑戰,他說:“在證實了我可以做邏輯實證科學理論式的‘科學’之後,我很高興地永遠拋棄了它”。
斯麥茲的後人繼續對行為主義方法進行批判。行為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研究至今仍是傳播學方法論的兩大主要分歧流派,儘管行為主義式的研究結論已經不像初期那樣簡單和絕對了。
主要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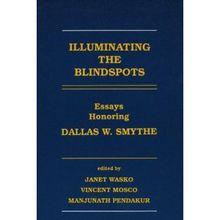 Dallas.W.Smythe
Dallas.W.Smythe《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Communications:Blind spot of Western Marxism)1977年。
《對傳播理論的觀察》(Some Observations on Communication Theory)1954年。
文章《腳踏車之後是什麼?》(After Bicycles, What?)1973年(中文版刊於《開放時代》,2014年第4期)。
《依附之路:傳播、資本主義、意識和加拿大》(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Capitalism,Consciousness,and Canada,1981)1974年。(中文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