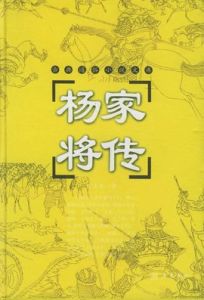概念
與通俗文學的關係
 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中國的通俗小說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話。但是,什麼是中國通俗小說,自古以來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直困擾著中國學術界,包括通俗小說的作者和研
究者。
什麼是通俗小說?在研究它之前,我們必須理順
 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對於文學,按經典的四分法分類,通常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各類中又可細分出許多樣式,而小說只是其中一大類別。對於通俗文學,並沒有統一的分類法,但多數學者對鄭振鐸先生從文體上進行分類的意見是趨於一致的。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將通俗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戲曲、講唱文學、遊戲文章等,這種分類法基本與四分法對應,可見通俗小說只是通俗文學中的一大類別而已。顯而易見,用通俗文學代指通俗小說,勢必擴大了通俗小說的內涵,使概念不夠周延,這是一種邏輯錯誤。
“通俗小說”這個術語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創造,早在明朝末年,中國的一位傑出的編輯家和通俗小說作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已正式使用了“通俗小說”一詞,距今將近360年的歷史。
各家陳述
什麼是通俗小說,自古以來就存在著各種說法,他們都試圖以最簡潔的文字對通俗小說作出解釋,這裡且摘錄部分有代表性或權威性的說法。
飾小說以乾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莊子·外物》
 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出,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桓潭《新論》
通才著出以百數,惟太史公為廣大,余皆叢殘小論,不能比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
——桓潭《新論》(引自《太平御覽》卷六二O)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亍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也。
——《漢書·藝文志》
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跡變泰之類。
——吳自牧《夢梁錄·小說講經史》
小說家者流,出於機戒之官,遂分百官記錄之司。由是有說者縱橫四海,馳騁百家。以上古隱奧之文章,為今日分明之議論。或曰演義、或謂合生、或稱舌耕……
——羅燁《醉翁談錄·舌耕敘引》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
——可一居士《醒世恆言·序》
小說者,乃坊間通俗小說,固非國史正綱,無過消遣於長夜永晝,或解悶於煩劇憂悉,以豁一時之情懷耳。
——酉陽野史《新刻續編三國志引》
小說者,別乎大言之也,其事為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小;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閒談,是以謂之說。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之正宗也。
——羅浮居士《蜃樓志·序》
雜說短記,不本經典者,概比小道,謂之小說,乃諸之雜家之言。
——瞿灝《風俗編》
 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以上摘錄是中國近代新小說產生前人們對“小說”的認識。從他們的言論中可以看出,有的
沒有有效地將文言小說與通俗小說區分開來,有的只是就通俗小說發展的某一階段(如說話、話本小說)而言,有的是只注意到通俗小說的某些功能(如通俗性、娛樂性)或世俗生活層面而言的,都還沒有將通俗小說的主要特徵表述出來。
清末民初之際,大量的西方小說被譯到中國來,促進了中國新小說的誕生,那么,早期的新小說派是如何認識“小說”的呢?
小說者,社會現象之反映也,人間生活狀態之描寫也。
——成之《小說叢話》
小說者,文學傾於美的方面之一種也。
——黃人《小說林·發刊詞》
小說者,文學中以娛樂的、促社會之發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
——覺我《余之小說觀》
小說之文,寓言八九,蜃樓海市,不必實事;鈎心鬥角,全憑匠心;俾讀者可以坐忘,可以臥遊,而勸懲可以其間也。
——焦木《小說月報》第三章第四號(1912)
說明
 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新小說派的觀點較古代學者的認識有所前進,尤其是“覺我”、“焦木”的觀點比較接近通俗小說的特徵,然而,他們並非是以通俗文化背景下研究通俗小說,因此這種認識就難免帶有一定模糊性,使我們很難判斷這些觀點有什麼錯誤,但又感到有失準確。繼新小說派之後,中國社會有過幾十年的大動盪,如內戰和日軍侵華等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沒有再對通俗小說的認識問題有過討論。
直至改革開放初期通俗小說再度崛起時,通俗小說評論家宋梧剛先生在1985年1月20日《羊城晚報》上發表文章,談到什麼是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應是以民間最喜愛的題材,以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法所寫的,目前還不為純文學家和理論家看重的小說。
這只是對鄭振鐸關於通俗文學界說的延伸,延伸過頭又引出幾分通俗小說的自卑和淒涼。
綜合以上所引論的關於通俗小說的種種說法,正說明要比較準確地把握通俗小說,或者給通俗小說下一個比較準確的定義,是很困難的。那么,是否可以給予一個更接近通俗小說特徵的定義呢?我以為這是有可能的。
通俗小說是個相對概念,若要較為準確地把握通俗小說,不能不與“純文學”小說從整體上作一番比較,有比較才有鑑別。
首先我們應看到,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既判然有別又非水火不容,這種既對峙又相容的態勢,使人們對兩種小說樣式的認識具有一定模糊性。上面所引用的一些觀點,足以說明這一點。
 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的區分,可從發展軌跡、創作方法、創作動機、價值取向上看出。從兩種小說的源流看,雖然共同發端於上古神話,通俗小說卻是沿著傳說——口傳歷史——市人小說——說話——話本小說——通俗小說一脈發展而趨於完善的,發展過程中通俗小說的文化積澱主要是世俗民眾的奇趣、俗趣。“純文學”小說是沿著先秦散文——志人、志怪——唐人傳奇——筆記小說、文言小說一脈發展而來,它的文化積澱形式主要表現為文人墨客的雅趣、奇趣。從創作方法上看,“純文學”小說選材具有寬廣性、典型性的特點,通俗小說則偏重於歷史和現實生活中偶見的、特殊的、曲折的、新奇的素材,選材面相對較窄,故而情節和人物多有似曾相識之感。“純文學”小說不屑於程式化,具有較強的創新精神,注重文字的精美,結構的精巧,內涵的深刻,而情節不構成它的本質特徵。也就是說,“純文學”小說不是靠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來媚悅讀者。通俗小說則往往是遵循傳統模式、情節密集、懸念迭起,富有濃厚的戲劇性色彩,娛樂消遣性表現得更為強烈。為增強傳播效果,通俗小說比較注重語言的通俗性,儘可能用村言俚語、淺近易懂的具有那個時代特徵的語言創作,但語言不構成它的本質特徵。從創作動機看,“純文學”小說追求審美趣味的雅致,蘊借含蓄地表達作者對人類、對社會乃至自然界的某些總是獨特而深刻的美學思考,因而“純文學”小說能表現出鮮明的美文學風貌。而通俗
小說主要是滿足和適應世俗大眾的精神文化消費需要,並不看重對個人性靈的抒發,故而作者常常為某種實利主義目的驅使,以作坊式的生產方式,編派一些富有傳奇性、趣味性的故事,因此通俗小說表現出厚重的商品屬性。從價值取向上看,“純文學”小說常常流溢出理性的美感,具有塑造人類靈魂、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的意義。而通俗小說有時能起到人生教科書的作用,但不具有向社會提供啟發性或隱喻性藝術形象的任務,它主要是弘揚以論理道德為中心的通俗文化和民族精神,表現人世間的道德美、人性美、世情美、風俗美。
通過對兩種小說樣式的對比,我們基本能看出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的重大差別,這兩種形態的小說是不能混淆的,有了這種差別,對“什麼是中國通俗小說”問題,就可以作出這樣的解答或界定:
通俗小說是用淺近易懂的語言和一定程式創作的,以較大密度的情節藝術地表現世俗大眾的審美理想和論理觀念,並以此為特徵服務於社會的一種文學樣式。
通俗小說語言的適俗性是通俗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徵,而不是本質特徵,僅從語言是白話文體或文言文體來識別小說的屬性是不科學的。例如現當代很多“純文學”小說是用白話文創作的,那歐化的句式或文不標點的冗長句子,則構成世俗大眾的接受障礙,可見白話文並非都是通俗的。古典通俗小說中絕大多數篇什是用淺近的文言創作的,語言、句式、風格都能適應世俗大眾的接受能力,雖是淺近的文言,並不產生接受障礙。仍具適俗性。語言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是個變數,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語言特徵,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用語習慣,不同的作家也常常表現出不同的語言風格。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符號也愈來愈趨精密和俗化,很多古典文學作品在當時是以俗語創作的,例如《詩經》、《世說新語》等,在我們今天看來,有的語言文字已變得古奧難懂,有的僅可會意而不能確解。因此,不能脫離語言的時代特徵、接受習慣去匡定通俗小說的屬性。
情節因素是通俗小說的本質特徵之一,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比通俗小說情節密度更大的文學樣式,也就是說通俗小說是靠豐富新奇大密度情節取悅讀者的。當然情節不是零件的組裝,而是要遵循通俗小說創作規律和主題的需要有機地集合在作品中,至於所創作的通俗小說是否為讀者所歡迎,則要看作家的藝術涵養和把“謊話編圓”的能力了。因此,那種心理時空、意識流、情節淡化等藝術手法是不適合通俗小說的創作的。
通俗小說的審美結構一般由題材、主題、情節等因素構成。從題材上看,通俗小說主要選取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絕少有超現實題材的作品,即使像《西遊記》這類超現實的神魔小說,也是表現的現實生活,並非本體意義的超現實主義小說。通俗小說的現實題材,著重於展示世俗大眾的生存狀態和社會矛盾,歷史題材雖是以古鑒今,但也要賦予一定的現實意義,兩種題材的選取都在於寄託世俗大眾的審美理想,如“大團圓”、善惡習有報等等。從主題上看,通俗小說主要是歌頌正義和善良,批判人世間的一切醜惡現象,好人雖飽受磨難歷盡坎坷,必有善報,壞人雖一時得逞,最終要遭受懲罰。通俗小說就是這樣頑強地表現著世俗社會千年不變的倫理觀念。因此,審美理想和道德觀念是通俗小說本質特徵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決定了通俗小說的美學風貌,後者決定著通俗小說的生存狀態。道德在社會歷史的整體運動中雖是一個獨立的範疇,然而它作為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統攝和決定作用,使作家在創作實踐中,他的倫理觀必然要在作品中表現出他的道德傾向,道德傾向就決定著通俗小說的生存狀態和價值選擇。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使許多通俗小說曾遭厄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所謂表現了“誨盜誨淫,傷風敗俗”,歷史的經驗應引起通俗小說作家的注意。道德是一種社會情感,主要表現在愛憎與是非的評判上。通俗小說對世俗社會“酒、色、財、氣”的過量描寫和渲染,失卻對“度”的把握,造成道德的傾斜,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很不利通俗小說的發展的。通俗小說對情節的依賴,主要是歷史上審美心理積澱而形成的。早在先秦時代諸侯王國宮廷里就有被稱為“瞽史”的殘障人士,他們是職業化的講述故事的人,與他們的職業相沿襲的有唐、宋時期的“說話”人,只不過後者將服務對象由宮廷轉向民間。為了吸引聽眾,滿足聽眾的期待心理,他們講述的故事必須有密集的情節,生動的語言,並且有一定的套路(模式)便於傳授“說話”技藝,由於歷史的積澱,使通俗小說比任何一種文學樣式更注重對情節因素的追求。
一般來說,通俗小說不向社會提供人生的哲學思考,而是以其通俗性、趣味性、娛樂性全方位多層次地為社會服務,高層次讀者可將通俗小說當作“成年人的童話”來消遣,工人、農民、市民也可在通俗小說營造的氛圍中做他的“白日夢”,從中尋求慰借和刺激,獲取心理平衡的愉悅。有一種觀點認為“通俗小說是可以雅俗共賞”的,例如白居易就愛用“一枝花”說話,宋仁宗還把民間說話藝人召進宮中,數學家華羅庚愛讀武俠小說等等,這些例子並不能證明“雅俗共賞”,他們對通俗小說的偏愛都是基於它的娛樂性、趣味性,並不在於獲取某種價值和力量。因此,“雅俗共賞”是一種假象,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且存而不議。
通過對通俗小說的簡單梳理,本文對中國通俗小說所作的解釋(或界定、定義),基本涵蓋了通俗小說的本質特徵,能有效地將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區分開來。我的解釋只是一家之言,歡迎並願意與學術界就此問題作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