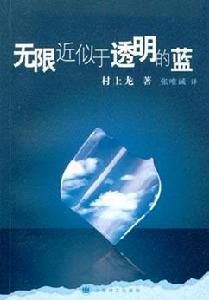 近似無限透明的藍
近似無限透明的藍由此開創了日本文壇的“透明族”流派。通過村上龍的作品,讀者在理解、透視、預測當代都市生活變化和所滋生的各種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將獲得深刻的啟發。
作者簡介
村上龍,日本小說家、電影導演。1952年2月生於長崎縣佐世保市。1972年就讀於武藏野美術大學。1976年發表的處女作《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被視為日本文學進入亞文化化的開端,獲第75屆芥川獎,引起日本社會震動,銷量高達350萬冊。1980年以《寄物櫃嬰兒》獲第3屆野間文藝新人獎。2000年以《共生蟲》獲第36屆谷崎潤一郎獎。重要作品另有小說《戰爭在海對岸開始》、《網球公子的憂鬱》、《69sixtynine》、《極端的愛與幻想》、《伊維薩》、《心醉神迷》、《斐濟的侏儒》、《五分鐘後的世界》、《音樂的海岸》、《第一夜第二夜最後一夜》、《希望之國的出埃及記》、《寂寞之國的殺人》、《最後的家族》,隨筆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戀愛永遠是未知的》等。自編自導的電影有《黃玉》。
主要內容
主人公阿龍和他的朋友們正值青春年華。日常生卻沉溺於搖滾、吸讀、群居和暴力。他們與基地的美軍士兵聚會混交,甘願做美軍士兵的“玩偶”。青春在墮落中消磨,生命變得毫無價值。他們是一群遠離故鄉的漂泊者,更是失去精神家園的孤獨兒。
這一切在幻覺與現實,喧囂與騷動的影像中被表現出來當他們厭倦這種像“飛蛾”和“蟑螂”一樣的齷齪生活時,回歸的意願就變得強烈起來。小說中描寫的麥爾告訴阿龍他將要回鄉的情節,阿龍回富山老家的段落,還有那叫“沖繩”的青年總是在提回沖繩去,阿龍在幻覺中描繪的那座城市、那座宮殿……
所有的人物都在尋找自己的歸宿,但他們回歸的真正家鄉在哪裡,正的精神家園在何處,這些無疑揭露了二戰後美軍對日本的占領。美軍基地長期存在,使日本社會矛盾重重。這樣的社會體制,正是作品中阿龍所幻覺的“黑色大鳥”,讓人感到恐怖。主人公只能在幻覺中尋找自我,只能在沾有自己鮮血的玻璃碎片中看到“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
書籍思想
村上龍24歲時寫就的成名作《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末尾,那個含有其自己影子的,在美軍駐紮基地旁吸毒、酗酒、群交、狂歡的青年,最後倒在了草地上,隔著腕脈劃傷的碎玻璃片,觀望到了近似無限透明的深藍天空。這一形象仿佛一個更為深遠的隱喻。如果說,需要一個意象來作為村上龍的代表的話,也許沒有比這一幕更為合適的了。
《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幾乎可以成為村上龍這個人的縮影,他一直秉持的觀念,他一路行來的歷程。玻璃一樣硬、能反光、邊緣鋒利,從建築得不合理的窗戶上保持著傾斜的平衡。你會擔心隨時會一地碎片劃出鮮血來。然而有時這些玻璃片又飄揚了起來,像樹葉,像少年們拿著玻璃在白粉牆上劃的痕。然後逃逸。然而村上龍靜靜的說了這些話,他並沒有逃逸——雖然很多東西真實得讓人想嘔吐。
將行為貫徹於寫作中,一如他最初的小說一樣,他的小說中充滿著自傳色彩。無非是偶爾轉換一個角度,然而《IBIZA》、《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無不真實得觸目。與獰厲的生活對視,給出平靜的敘述。就像小說中吞噬列酒、吸食毒品、冷冷的注視他人的青年一樣,村上龍並不激烈的給出沸騰澎湃的思緒,他只是敘述。
相比起樂於使用象徵手法、艱澀刻深的描述都市生活的安部公房,以西式長句和大量意識流字句來給出存在證據的大江健三郎,以及酷好雷蒙德·卡佛、運用寓言般的輕盈字句營造幻像的的村上春樹,村上龍的答案簡單而直接。血液、蟲子、酒杯、海洛因、性愛、死亡、痛苦,這些在他的筆下並非繁冗到足以成為符號,而是客觀單純的存在。相比起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文學大家般的自省意識,以及村上春樹的自我語境,村上龍冷靜得可怕。在藝術家的眼裡,生活永遠戲劇化紛繁。藝術家們的小說,永遠具有優雅飄忽的美感,不落地的音符。然而,村上龍直截了當的描述生活,在他那裡,粉飾只是偶爾為之,那些憤怒、哀傷、恐懼、揣測、逃避的過程,樁樁件件的細節,生活像一個多面形體一樣撲過來。而字,是口唇中吐出來的幻覺。生活壓榨著身體,而身體中還有著無數東西阻撓著你坦承真實。比如自尊心,比如虛榮心。接下來,就是痛苦的過程。空氣像玻璃一樣冷而平面的壓了下來。生命的喬飾被解去之後,生與死得以近距離對視,彼此呼吸相聞。這個時候,死亡、狂歡、激情、摧傷不再是一句戲語。它被擺到了桌面上。生活的對立面,觸手可及。作為一個話題談論,作為一個現實被接受。無論是《IBIZA》、《近乎無限透明的藍》、《寄物櫃嬰兒》,他都是直接、坦然,而又毫無造作的把毀滅和死亡的話題,放到紙面上來來敘述。
於是,我們可以說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是一個希圖醒世的思想家,我們可以說村上春樹是一個低回溫柔的爵士樂手,而村上龍,是一個偶爾瘋狂跳躍,偶爾冷酷平靜,完全只由自己來的,搖滾歌手。
必須說一下他和村上春樹。村上龍比村上春樹小3歲,卻早其3年成名。相比於村上春樹學生——爵士樂酒吧老闆——寫作者的角色轉換,村上龍要複雜得多。搖滾樂手、話劇、攝影,乃至電影。村上龍並沒有把對文本的深入挖掘和渴求作為自己的目標——和大江健三郎們不同——他是在許找著可以更直接表達自己對世界的思緒的方式和手段。村上春樹對虛無、世界的惡進行寓言化解構的時刻,村上龍在大張旗鼓、暴跳如雷的傾訴著他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這便是他的《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這一隨筆集的由來。一個平和優雅,節奏分明,一個激揚飛舞,快慢由心,而兩又各自深得西方文化的薰染,這也許是兩個村上文本的可資互相比較之處。
村上龍的腳牢牢踏在大地上,周圍是燈紅酒綠、鋼筋水泥的世界。欲望和焦躁如同粉碎的玻璃片一樣四處飛揚。他並不忌憚去描寫毀滅。很清晰的,在《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里,他用七章半來描寫了昏天黑地的地獄般狂歡,然後用半章來使男主角——他自己——在疲敝不堪的情況下躺倒在草地上,觀望幻像般的無限透明的藍色天空。這是他對世界的直面,以及對救贖的召喚。他嫻熟一切道理,對世界的惡和毀滅有著清晰的了解。而他的世界,亦如同這片粉碎的、鋒利的、帶有稜角的、沾有血跡的玻璃片:這上面凝固著痛楚、傷害、虛弱的影子,然而它帶有不可剝奪的真實,令我們善於自我暗示的心理未敢面對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