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履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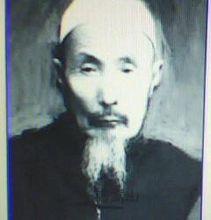 虎嵩山
虎嵩山  虎嵩山
虎嵩山 虎嵩山(1880--1955),回族。寧夏平遠(今同心)人。自幼從父學習伊斯蘭教經典。自幼從父學習伊斯蘭教經典、阿拉伯語和虎非耶門宦的宗教功修。後到海原縣拜王乃必阿訇為師。1924年赴麥加朝覲。精研《沙米》、《伊爾沙德》、《米什卡特·麥薩比哈》等經典及教法,歷時5年之久,從此學業大進。22歲時應聘為同心縣清真小寺阿訇。後接受伊赫瓦尼派創始人馬萬福倡導的“憑經立教”、“遵經革俗”的主張,遂不願繼承父業,脫離虎非耶門宦。在同心縣穆斯林中大力宣傳伊赫瓦尼派教義,提出一切言行皆以《古蘭經》和聖訓為準則,對不符合經訓的一些禮俗進行改革,聲望日著,成為寧夏及隴東地區伊赫瓦尼派知名阿訇。他博覽各種伊斯蘭經籍和漢文譯著,融會貫通,富有獨立見解。通曉阿拉伯語、波斯語及語法、修辭,對《古蘭經》學、聖訓學、凱拉姆學、教法學、蘇菲主義、邏輯學等均有較深造詣。1924年經上海赴麥加朝覲,翌年歸國後即在湖南常德縣應聘為開學阿訇。1927年回原籍提倡回民新式教育,主張學經兼學漢文化,聯合各界推動回民教育的發展,並對清真寺經堂教育的內容、方法實行改革。1937年在寧夏吳忠創辦中阿講習所,從事伊斯蘭教經典的研究和講學,並自任所長;後改名為吳忠中阿師範學校,任副校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提出“國家興亡,穆民有責”,既愛教又愛國的主張,積極發動穆斯林參加抗日活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主張穆斯林內部應消除教派分歧,各行其是,團結一致,共同建設新中國。他曾任中國回民文化促進委員會委員、甘肅省政協委員、寧夏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政協副主席等職。1927年後,曾任寧夏中阿講習所所長、中阿師範學校副校長。建國後,任甘肅平涼專署民委委員、甘肅省第一屆政協委員、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政協副主席。長期從事伊斯蘭經典著作的講學與研究。對《古蘭經》、聖訓、教法、俯仰學和曆法等深有研究。1955年逝世於平涼,葬於原籍。
人物生平
家世
 前排左一為虎嵩山
前排左一為虎嵩山 虎嵩山1880年生於同心縣半個城,父親是同心縣“虎非耶”門宦的一位“海里凡”,人稱“虎爺老人家”,四十歲時曾就學於蘭州“虎非耶”門宦的涼州莊老人家門下,四十五歲回同心設立道堂,傳授“虎非耶”教規,民眾皈依者日眾。據說,虎嵩山出生時,適逢涼州莊老人家從蘭州來到他家作客,便給他取了一個宗教名字,叫“賽爾敦丁"(意即宗教的幸福),並告訴他父親說:“這孩子將來一定是‘虎非耶’道統的繼承人。”他父親聽了自然十分歡喜,而且就從此遵照涼州莊老人家的祝願,一心想把兒子培養成為自己未來的接班人。
求學
 前排中間為虎嵩山
前排中間為虎嵩山 1897年,虎嵩山已經18歲了,他父親把讓位給兒子的宿願,公開告訴了他的教民。由於虎嵩山資質聰穎,儀表端莊,尤其對宗教知識的學習,成績最為突出,因此“虎非耶”門宦的民眾聽到他將要繼任第二代“海里凡”時,當然皆大歡喜,一致表示熱烈擁護。可是他們沒想到,這位年輕的虎嵩山對他父親的宗教言行越來越感到懷疑和厭煩。這時虎嵩山已拜其他著名阿訇為師,並學到了他父親所不知道的宗教知識。於是他決心同父親分道揚鑣,另訪名師,繼續鑽研伊斯蘭教的各門學問。
就在這年農曆九月,虎嵩山投學於在海原縣濫泥溝清真寺開學的汪乃必阿訇(甘肅臨夏人)門下,用心攻讀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並對伊斯蘭教的各大經典進行了全面認真的學習和研究,宗教知識有了很大長進,能夠獨立閱讀深奧難懂的經典。這時,甘肅馬萬福阿訇(又稱果園哈吉)所倡導的“依赫瓦尼”派學說,已在甘肅、青海一帶廣為流傳,這對當時的汪乃必阿訇和他的高足虎嵩山有很大啟發。師徒二人為了積極回響“依赫瓦尼”學說,專門學習和討論了被“依赫瓦尼”奉為正統教典的《沙米》、《伊勒沙德》和《米實卡替》三部經典。
傳教
1902年,虎嵩山已從汪乃必門下畢業,回到了同心縣故鄉。這時,他只有21歲,由於才德出眾,便受聘到同心縣城清真小寺當了教長。從此開始,他是第一個在寧夏公開宣傳“依赫瓦尼”學說的人。傳教初期,他曾受到反對派的歧視和壓制,甚至遭到人身攻擊和迫害,但他百折不撓、艱苦奮鬥,經過近十年的努力,終於使“依赫瓦尼”學說不僅在同心打下了穩固的基礎,而且在寧夏黃河兩岸和甘肅一些地區的穆斯林中影響也越來越大。
當時,“依赫瓦尼”活動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它的學說和主張易被一些好學的中青年阿訇所接受。因此“依赫瓦尼”在寧夏不到30年時間,就傳遍各地,而且顯得生氣勃勃,每到宗教場合都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氣氛,無論是阿訇或民眾見面時都相互緊握雙手,彼此稱道:“依赫瓦尼”(兄弟),以示親愛團結。他們在儀表上最重視留鬍鬚,在教義上強調遵照《古蘭經》、《聖訓》的規定辦事。
革新
虎嵩山在寧夏宣傳“伊赫瓦尼”學說時,曾沿襲了甘肅馬萬福的“憑經立教”的主張,並針對寧夏穆斯林傳統的宗教活動中一些不符合《古蘭經》、《聖訓》規定的做法進行了批判與改革。按照他的解釋,中國內地的穆斯林長期同漢族雜居,無論是文化或生活習慣,都受到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婚、喪、祭祀等禮儀,幾乎完全抄襲了漢族的繁文縟節。據說這不僅是背離正統教義的行為,而且更加重了穆斯林民眾的經濟負擔和不應有的宗教義務。因此他在宣傳“依赫瓦尼”學說時,就提出了“遵經革俗”的口號。
“遵經革俗”
關於“遵經革俗”的內容,虎嵩山是依據上述經典的理論指導,概括地提出以下幾個方面:
一、反對給念《古蘭經》的人出“烏支勒”(代價)。根據“依赫瓦尼”派的解釋,所謂“烏支勒”就是穆斯林為了祭祀亡人或祈福祛災時,邀請阿訇誦讀《古蘭經》的某些篇章,誦讀結束,由主人散給阿訇現金若干,同時還要設宴招待一番。按照虎嵩山的意見,類似這樣的做法,如果雙方不是出於絕對自願,而是迫於人情世故,不得不乾,那么這種行為就變成了買賣交易。他按照伊斯蘭教的正統理論說明,這是一種接受“烏支勒”的犯罪行為。因為《古蘭經》是命人行好、止人乾歹的最高準則,不能依靠誦讀《古蘭經》謀取代價。《古蘭經》里真主曾經說過:“你們不要用我的啟示換取一些代價。”(2:41)又說:“隱瞞經典,並以它換取一點代價的那些人,他們肚裡吃的就是火焰。”(6:174)所以,“烏支勒”是那時“依赫瓦尼”遵經革俗的重大內容之一。虎嵩山後來在他編寫的《穆民三字經》中就批評“烏支勒”是錯誤的。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是“依赫瓦尼”同其他教派長期爭論的重點。後來,“依赫瓦尼”派中甚至有人竟把“烏支勒”說成是“依教求食”的罪過。但相反的,也有人把“依赫瓦尼”簡單地貶低為“吃了不念,念了不吃”的新興教。
 虎嵩山
虎嵩山 二、反對鋪張浪費的宗教儀式。過去寧夏各地的穆斯林對於亡人的葬禮和祭祀,曾實行一套既繁鎖又浪費的宗教儀式。從死人彌留之際,直到死後的一周年,死主家請客念經,多達十次以上,加上發給家屬親友的孝布以及送葬散錢等花費,僅在一個亡人身上,有時會造成傾家蕩產的危險局面。虎嵩山在宣傳“依赫瓦尼”教義時,嚴厲地批評和制止這些違背教義的錯誤做法,他曾指出這些陳規陋習本是來自中國佛教的影響,年長日久就演變成了穆斯林的宗教活動。這不僅是來世的罪行,而且又是今世的不幸。他為了反對在祭祀亡人中大搞鋪張浪費,曾引經據典地勸告穆斯林民眾,要按正統的教道辦事,因為《古蘭經》中真主說:“他們信主又行善的那些人,我只給他們課派力所能及的。”(7:42)他還引證穆聖的教導:“你們為自己和亡人舍散,即便是一口水也可以,如果這也辦不到,那就由自己念一段《古蘭經》;如果對《古蘭經》什麼也不懂,那就央求真主的恕饒和慈憫,因為真主已許約要答應你們。”虎嵩山就是根據這些《古蘭經》和《聖訓》,批判了當時錯誤的祭祀活動。他曾譏笑那些為聖人舉行祭祀的人說:“聖人逝世後他的親屬和輔土們都沒有祭祀過聖人,難道他們不比我們熱愛聖人嗎?”據說他為了禁止不合教義的風俗習慣,曾在同心掀起了一場民眾性的“破孝”運動。雖然他的號召遭到了部分穆斯林的反對,但終於取得了勝利。而且從那以後,即使反對他的教派也逐漸改變了大行戴孝的不良風氣。
三、反對門宦制度。虎嵩山對寧夏伊斯蘭教內形成的門宦制度,曾經作過深入的調查和了解。在寧夏伊斯蘭教的門宦中,能夠成為教派的主要有“哲合忍耶”、“虎非耶”和“格底林耶”三派。至於分散到全區各地的道堂和“拱北”,大半都是從這三個教派中分化出來的小道門。
虎嵩山對所有的“門宦”、“道堂”、“拱北”,一律加以排斥。他認為,他們的宗教理論和宗教活動不完全符合伊斯蘭教的正統學說,認為門宦制度是18世紀中亞的“蘇非”派傳入中國後才逐漸形成的。蘇非派是一種神秘主義集團,創始於11世紀的阿拉伯國家。它把伊斯蘭教的善功分為“禮乘” (設勒爾替)、“道乘” (托勒格替)、“真乘”(哈給格替)三個截然不同的修煉階段。
根據蘇非派的說法,“禮乘”是入世的宗教活動,“道乘”是出世的宗教活動,“真乘”是超脫為與真主合而為一的修煉階段,而蘇非派最重視的是“道乘”和“真乘”。但在寧夏,除“嘎底林耶”外,“哲赫林耶”和“虎非耶”一般只是傳授“道乘”,按照當地穆斯林的說法就叫做辦“托勒格替”。據說辦托勒格替的人,第一要親受道祖(繼承道統的人)的指點,第二要緊跟道祖勤修苦練。因此凡有傳授“托勒格替”的地方,就必然要建立道堂,道祖死後又必然要修建拱北。同時被指定的繼承人又成為新的道祖,所以,這就是門宦制度產生的歷史根源。
虎嵩山原來反對門宦制度的原因是:
一方面他發現門宦制度本身存在很多陋習,特別是他通過父親所主持的“虎非耶”門宦,感到其中不合教義的地方很多,首先門宦的主要精神是要做到脫離紅塵,清高無染,而他父親作為教徒的榜樣,只能是閉目打坐,不理現世。其實這恰恰和伊斯蘭教的原則背道而馳。因為《古蘭經》上明明講道:“當禮拜完畢的時候,你們就散布在大地上,去尋求安拉的百恩。”(62:10)這就說明,伊斯蘭教反對人們脫離紅塵,鼓勵人們重視現世。
其次,作為門宦的領袖一定要有“奇蹟”,據說他父親也曾有過這樣的傳說,後來經他證明,全是無中生有的捏造。另外,為了迷惑民眾,說能“預卜吉凶”,“妙手回春”等等,都是故弄虛玄的手段。虎嵩山為了進一步弄清門宦的來龍去脈,曾用心研究了一部叫做《麥克圖巴特》的經典。這是中亞布哈拉的艾哈默德·蘭巴尼寫的,他是乃格什板頂耶的第七輩道祖,被稱為穆聖逝世後第二個千年的“穆占底德”(新興人物),他的道統被“哲赫林耶”和“虎非耶”所公認。
但是蘭巴尼在他的著作中,對蘇非派歷來的主張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反對把“禮乘”、道乘”、“真乘”分為三個階段。他認為,如果把“禮乘”的功課(念、禮、齋、課、朝和倫理道德)做到家了,那么“道乘”和“真乘”也就寓於其中了。他以不說謊話做了一個比喻:有人開始不想說謊,這就是“禮乘”;以後成了絕不說謊,這就是“道乘”;最後成了不會說謊,這就是“真乘”。他的意思是,所謂“三乘”是一個整體,只是程度上略有差別而已。
按照他的論述,真正的蘇非派應該注重“禮乘”,要力行主命和聖行,他反對那些獨善其身的修道土;他認為顯示“奇蹟”是荒誕不經之談;他還斥責那些所謂進入“真乘”而表現狂顛的人為道德敗壞者。虎嵩山一直作為反對門宦的理論根據,就是依靠蘭巴尼的《麥克圖巴特》這部被公認為是正統派的經典。後來所有任教的“依赫瓦尼”阿訇都把這本經典作為反對門宦的有力武器。按照虎嵩山的意見,每個門宦都有其不同的發展歷史過程,但總的情況是,在門宦發展的初期,其中不少領導人都具有較多的宗教知識,而生活也能克勤克儉,清貧自守。但是,到了後來,由於經濟地位的變化,使原來超世脫俗的作風,逐漸被當地的習慣勢力所代替。
1899年虎嵩山的父親去世了,繼承道統的人是洪壽林,按照傳統規矩,“虎非耶”門宦的教民很快就給他父親修建了“拱北”和亭子。後來,虎嵩山為了破除人們對他父親的迷信,在一個夜間,自己帶人把“拱北”和亭子全部拆毀了。據說這件事對於各派門宦震動很大。他們怕的是將來發生連鎖反應,會給各個門宦帶來不利。因此,事過不久,虎嵩山就被一門宦領袖下令綁送固原縣府關押。禁閉數月後,經虎嵩山的親友具保釋放了。此後,他為了避免同反對派發生正面衝突,只好放棄了宗教職業,改做縫紉生意,並為了替自己改行進行辯護,曾宣傳伊斯蘭教曆代聖人都是勞動為生,傳教只是他們的義務,並非謀生手段。他經營縫紉業不到三年,在穆斯林民眾的懇求下又恢復了教長工作。從此開始,虎嵩山一直從事於宗教事業,其活動範圍之廣,影響之深,非一般阿訇所能比。
評價
現將他的活動經過舉其重要者略述如下:
熱愛祖國
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虎嵩山的早期思想和當地一般阿訇一樣,對於國家的觀念是比較模糊的。其原因是,解放前回民在政治上一直處於被壓迫、被歧視的地位,尤其經過滿清王朝的血腥鎮壓,回族人民對過去的統治者,長期存在著對抗情緒。由於這個緣故,回民的阿訇,每講到中國穆斯林同清朝的關係時說是處於“交戰國” (達魯里哈勒比)的地位。辛亥革命之後,一些阿訇卻只強調中國穆斯林對宗教所承擔的各項義務,而對國家的義務,卻從來不置一詞。
 虎嵩山
虎嵩山 1925年虎嵩山去麥加朝覲。他沿途發現中國人由於國弱民窮,處處受到外國人的歧視,不管是回民漢民,遭遇完全一樣。他從此認識到,沒有富強的祖國,就沒有個人的自由,宗教也不例外,所以他的觀念改變了。他重新肯定,中國穆斯林是全國人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看了一些有關西北民族矛盾的史書,發現歷史上的民族壓迫,是當時的官府造成的,不是各族人民之間固有的仇恨。他認為,過去有些阿訇為了反對清政府的民族挑撥政策,卻把祖國說成是穆斯林的“交戰國”。這是牽強附會、自絕於人的荒謬言論。
他回國後在上海受聘到湖南常德清真寺擔任教長。這時他除了專修漢文外,還特別關心國內外大事,對於“五四”運動的新思潮也深受感動,因而愛國思想就越來越強烈了。
1927年他回到家鄉後在各寺任教期間,在宣傳教義的同時,儘量向穆斯林民眾講說國內外大事。據說1927年,他在鎮戍(即今同心縣)縣城下馬關清真寺當教長時,曾與本縣回民知名人士白道然合作,在清真寺內附設“鎮戍縣回民自治公會”一處,目的是想把包括阿訇在內的回民知識分子組織起來,進行愛國教育,反對軍閥割據,實現祖國統一。但是,不久他受聘他往,白道然因公外出,“公會”也就自行流產了。
1938年,正值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開展,這年虎嵩山受靈武回民上層人士李鳳藻等人的聘請,擔任吳忠中阿師範學校校長。該校招考的學生,是有一定阿文和漢文基礎的回民青年,另外還設有宗教研究班,招考的阿訇都是比較出名的教長。當時,國民黨的消極抗戰,使國土喪失將近一半,敵人的飛機在後方狂轟亂炸,就連偏僻的寧夏也不得倖免。這時,為了配合全民抗戰,虎嵩山就依靠這個寧夏穆斯林的最高學府進行了各種抗日救國活動。他規定每天早晨禮拜結束,讓全體阿訇和學生都要參加升旗儀式。當時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他不可能理解國家政權的性質,但他只是出於一片熱愛祖國的赤誠,利用升旗儀式的機會,和教師們輪流宣傳抗日救國的重大意義,揭露敵人燒殺擄掠的罪行。他指導學生每七天出一次牆報,舉行一次講演會,內容都以抗日救國為中心。他自己利用聚禮日講話(瓦爾茲)的機會,引用《古蘭》、《聖訓》,動員穆斯林民眾要為抗日救國做出貢獻。當時最令人感動的是,他親自用阿拉伯文寫了一篇反對日本侵略的祈禱詞,加上漢譯,用尺五見方的白紙石印成宣傳品,分發各清真寺。他要求各寺教長,在每七天的“聚禮”拜前高聲朗讀,最後大家一起共念“阿敏”。
虎嵩山作為一個宗教人士,他不僅維護宗教信仰,而且真心熱愛祖國。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講話口口不離“國家興亡,穆民有責”這句話。他常引證“愛護祖國是屬於信仰的一部分”這段聖訓,嚴厲地批評那些“愛教不愛國”的人,氣憤地說他們不僅是國家的敗類,而且也是伊斯蘭教的偽信者。
興辦回民學校
 虎嵩山
虎嵩山 提倡阿訇學習漢文。虎嵩山在西北不同於一般阿訇,他除了宣傳宗教外,還大力提倡興辦回民學校,以期普及回民的文化教育。過去西北回民由於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加上阿訇的片面宣傳,使一般回民只讓孩子念經(阿文),不讓讀書(漢文),怕的是讀書以後思想被漢族同化。但是虎嵩山卻不是這樣想的,他認為過去西北回漢矛盾,是少數人挑撥起來的,正因為回民不讀書,文化落後,回漢之間思想不能夠溝通,以致互相猜疑,發生誤會和衝突。有鑒於此,所以他自擔任教長以後,一方面努力學習漢文,一方面勸說回民設立學校,他還批評了過去回民念經不讀書的害處。因此1932年在省城成立的“寧夏私立中阿學校”,1938年在吳忠成立的“中阿師範”,都和他的積極倡導是分不開的。另外他在同心、固原等地曾動員民眾辦了幾處國小。
虎嵩山除了提倡發展回民教育外,對清真寺的經堂教育也提出了改革意見,認為過去的經堂學生(寧夏叫做“滿拉”),只學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培養出來的阿訇,既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又不能確切地闡述宗教教義。尤其經堂教育中,對阿文、波斯文的口譯,錯誤很多。比如阿文辭彙的“伊里替法台”應該譯做“注意”,但經堂語卻譯成“少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他經常宣傳,必須在經堂教育中添授漢文,造就中阿兼通的宗教人材。然而他的宣傳遭到了種種阻礙。據說同心有位很有聲望的周教長,對他的提倡漢文,改革經堂教育,進行諷刺打趣,說什麼穆聖和他以後的“海里凡”都沒有讀過漢文,但宗教卻被他們傳遍了世界。吳忠有位著名的張阿訇,聽了他的演講以後便輕蔑地對人說:“虎嵩山原來不是阿訇,而是一個念書人。”但他對別人的誹謗謾罵,一概置之不理,他任勞任怨,堅持自己的主張,並在他任教的清真寺內一直給“滿拉”教授漢文。他經常對年輕的阿訇介紹自己學習漢文的好處,說他原來閱讀阿文經典,很容易領會其精神,主要是藉助於漢文書籍的相輔相成,尤其通過閱讀漢譯經典,對於研究宗教教義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虎嵩山在提倡回民教育、改良經堂教育方面,確實做出了很大成績,而且在西北伊斯蘭教的發展與變化中起了主要作用。直到解放後,在寧夏、甘肅參加政府工作和擁護黨的領導的宗教人士中,許多漢文阿文兼備的阿訇,都是出自他的門下。
編譯宗教常識讀物
 虎嵩山
虎嵩山 修訂阿、波文法基礎課本。虎嵩山在西北伊斯蘭界可算是一位博學多才的經學家。人稱他精通八大“爾林”(學問)。所謂八大“爾林”即指阿文的詞法、句法、修辭、教律、認主、邏輯、蘇非和《古蘭》注釋等八門學問。這本來是對過去才學出眾的阿訇慣用的讚美詞,但對虎嵩山來說這的確是受之無愧的。除此而外,他對《聖訓》和阿、波文詩詞以及漢文都曾刻苦鑽研,具有較高的水平。據說他從前在吳忠中阿師範附設的“宗教研究班"招收的是一批阿、波文成績優良的中年教長,他所主講的課程都是歷來認為深奧難懂、無人問津的冷門,如《魯哈白央》的詩篇等等。有些阿訇把他神化為無師自通的“胎里會”,特別“門宦”方面的人,說他剛一生下即受到“涼州莊老人家”的點化,心竅早已頓開。虎嵩山對這種無稽之談感到十分厭惡,他曾多次向人介紹自己青年時代的學習經驗:第一是勤學強記,第二是善於自修,第三是廣泛閱讀,第四是深鑽一門,最後做到觸類旁通。
虎嵩山著有一本《穆民三字經讀本》,內容主要是伊斯蘭教的基本常識,包括信仰,主命、聖行以及日常的宗教活動等部分。因為說理能深入淺出,文章又合口押韻,所以很受初習宗教教義者歡迎。他同蘇盛華合譯的《拜功之理》,內容是闡述“禮拜”儀節的內在含義,屬於蘇菲學的理論範疇。以上二書曾在1940年前後出版。他所編寫的兩冊《阿文文法基礎課本》和一本《波斯文法精華》都是對原有的讀本重新加以修訂。編者在自序中說“固有文法初階,或散漫,或無群,或言文蕪雜,甚至以訛傳訛,皓首弗辨”,所以他編寫的目的是“非有簡明易學之文法基礎為捷徑不可”。對於修訂部分,他把原來用阿、波兩文注釋的地方全改寫成單一的阿文,並用漢文詳加說明,而對原來缺陷的“字根”、“動詞"等,有的則作了校正,有的則加以補充,又在每一段落附有表格,分類有條不紊,使初學者一目了然。以上經他修訂的這兩種文法基礎,在當時的阿文和波文文法教材中可以算是最新穎而完善的本子,所以出版以後就很快銷行西北各地 (解放前北平《月華出版社》也曾代銷) 。
反對固步自封
緊跟時代前進。虎嵩山為了伊斯蘭教的發揚光大,一生孜孜不倦,認真研究有關宗教的各種問題,希望伊斯蘭教對於國家的統一富強做出應有的貢獻。但他感到不幸的是,絕大部分宗教人士,因為不讀漢文,不了解當前世界形勢,對於宗教知識囿於抱殘守缺,不能全面理解其含義,因此在宣傳教義時往往作出了不太確切的解釋和論斷,例如:
(一)關於動物的圖像問題。過去一般阿訇根據經典上的說法,穆斯林不能製做或陳設動物的圖像,否則就是犯大罪。依此類推,照相也不例外。其理由是:製做或陳設動物圖像原是多神教徒的迷信活動,所以信仰一神教的穆斯林就必須嚴加禁止。在西北有些回民家庭至今屋裡不許張貼印有人物和動物的圖像;甚至有人不肯給自己或家裡人照相。大約自從西北地方有了照相設備以後,穆斯林能不能照相,就成為大家議論的問題。當時一般阿訇的說法是,穆斯林不能照相。後來到了虎嵩山擔任教長的時代,這一問題才有了與前不同的解釋。他認為照相和照鏡子是一個道理,都是把自己的影子通過機械反映出來,為什麼照鏡子受到宗教鼓勵,照相卻被反對,這豈不是咄咄怪事?他對這一問題做了明確的講解,他說在穆聖傳教時期,正是多神教盛行的時代,當時崇拜神像就包括動物一類的模型,因此當時為了徹底清除崇拜偶像的流毒,禁止一切動物圖像是符合當時情況的;但是現在社會進步了,人的思想也隨著起了變化,今天穆斯林家裡擺著圖相誰也不會懷疑這是崇拜偶像。他經常說伊斯蘭教既然是講真理的那就要實事求是,千萬不要固執成見。
(二)有關文娛活動的問題。據說《聖訓》中有段話是:“凡是玩耍都是大罪。”這段聖訓,長期以來被中國阿訇作為一根棍子,對一切文娛活動不問內容好壞,一律打倒。解放前在西北地區的穆斯林,不但不允許從事文娛工作,甚至觀看演出也要受到批評。許多穆斯林儘管認為這樣做不完全合乎情理,但怕違犯教法不敢提出反對意見。後來虎嵩山在“吳忠師範學校”和“阿訇研究班”擔任校長時,有次在公開講話中批判了原來對這段《聖訓》的曲解。他說:“‘玩耍’這個詞的含義是一種對社會有害無益的遊戲,有人為了玩耍而浪費光陰,浪費錢財,損害身體,妨礙社會秩序,這就是犯大罪的行為。而昨天晚上我們的學生看了電影,據說是中國和日本打仗的片子;還有我們要提倡學生打球,這些對人的思想和身體都有好處,這當然不是‘大罪’。但有些阿訇持反對意見,說這就是‘玩耍’,是犯大罪行為;還說打球等於踢了‘哈散’和‘胡賽尼’的頭(這二人是被敵人殺害的穆罕默德的外孫),這些話實在荒唐!”
(三)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問題。虎嵩山對自然科學,只要弄清道理,就馬上公開宣傳。他曾講了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事,就引起了靈武縣一位馬教長的駁斥,給他寫信說:“《古蘭經》上說是‘太陽行在它的穩定之處’,並沒有說‘地球圍繞太陽’。”但是虎嵩山根據其它經典注釋,說《古蘭經》上的話明明說的是太陽自轉,並沒有繞地公轉的意思。他經常提醒穆斯林民眾說:“如果我們要反對自然科學,那就連衣、食、住、行都不能講了。”
關於虎嵩山的全部經歷,因無現成的文字記載,很難作出全面的了解與論述。從總的發展情況來看,他從早期的一個單純的宗教人士,逐步變成一個非常開明的、具有一定進步思想的愛國人士,這在西北回民的阿訇中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後來在他的後半生,為了民族之間的團結和回民內部的團結,他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雖然博覽伊斯蘭教的有關著作,但對中國儒家的學說一直是推崇備至,他的目的是想把伊斯蘭教的教義同儒家的許多思想緊密結合起來,以作為加強回,漢人民團結的紐帶。對於回民內部的團結,他為了消除教派隔閡,自己主動帶頭同其他教派取得聯繫,在教派不同的觀點上他要求互相容讓。他常對穆斯林民眾說:“中國的穆斯林信的是一個真主、一個聖人、一本《古蘭經》和一個伊瑪目(哈乃斐),既然在這些根本問題上沒有大的分歧,那為什麼要在次要的問題上各持己見,互相攻訐,以致分歧愈演愈深呢?這樣的結果是,使各派穆斯林都違背了真主的教導,因為《古蘭經》上說:‘你們一起堅持真主的繩索,不要分離。’這段《古蘭經》對堅持教派成見的人應該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劑。”
 虎嵩山墓碑
虎嵩山墓碑 虎嵩山的以上生平事跡,只是依據別人口述,經過整理而寫成的,其中掛一漏萬的地方,自然在所難免。特別是從1947年到他逝世的這8年中,由於他曾受聘到甘肅的臨夏、平涼等地擔任教長,所以目前在寧夏一時很難知道他在這一時期的活動情況。正因為如此,這篇文章就只能為探討虎嵩山的歷史而提供一些線索,並不是對他的全部歷史所作的研究成果和論述。
作品一覽
著有《波文之源》、《月論釋難》、《拜功之理》、《阿文教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