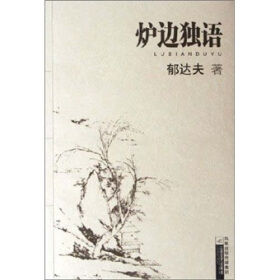背景簡介
郁達夫在日本留學十年。從1914年考入東京舊制“一高”預科,到1922年東京帝大經濟學科畢業,他不僅耳濡目染了匯集東西方文化、五光十色的“大正文化”,同時也飽嘗了海外遊子受歧視的辛酸和孤獨的痛苦。他的早期作品是這種社會背景下的產物,作者通過表現主人公的壓抑感到遺憾和病態心理,表現出了一種渴望獲得個性解放的願望,喊出“五四”前後中國青年的苦悶之聲,呼籲社會尊重人的價值。郁達夫感傷情調的積極意味
這種積極的意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郁達夫的頹廢以及這種頹廢的具體表現——性苦悶,不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的。這種頹廢和性苦悶,是當時青年的普遍心態,郁達夫則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現了這種“時代病”,從而將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到了歷史與社會面前,所以,具有積極性。第二,郁達夫的感傷、頹廢包含著對封建舊道德的自覺的挑戰。正如郭沫若在《郁達夫》中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要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相關資料
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勢後的我這零餘者,教我能夠做些什麼?郁達夫:《寫完了〈蔦蘿集〉的最後一篇》,見《蔦蘿集》,上海:泰東書局。
郁達夫有意或無意之間,用了19世紀俄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意象——“零餘者”(SuperfluousMan)。這個名詞首見於屠格涅夫的小說《零餘者的日記》,該作品也是一針見血,刻繪出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心情:他們和政治脫了節,對於社會現實(農奴)有沉重的罪惡感,但他們能做些什麼?大多數的人在沙龍里喝酒,談黑格爾,也是同樣地自暴自棄,頹廢度日,後來,終於有些年輕知識分子掙出了“零餘者”的牢籠,要改變政治和社會現實,於是變成了“虛無黨”的恐怖分子,或參加所謂“人民主義”(Populism)運動,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早期的列寧,就深受這種氣氛的影響。
郁達夫的自我懺悔,反映出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相似的現象。郁達夫和所有其他的知識分子,皆困擾於同一個問題:人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到底能夠做些什麼?
回顧歷史上的中國知識分子,這種“疏離”的現象,並不完全存在,因為“學而優則仕”,考試制度為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搭好了一座溝通政治與社會的橋樑。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問題,不是“能做些什麼”,而是“怎樣做”。在平常時期,他們常彷徨於“忠孝難兩全”的困境;在非常時期,他們徘徊於“仕與不仕”的選擇。五代的馮道,可以從容不迫地事十主,而宋末的文天祥,卻以遺臣盡前朝,為“正氣”而死。知識分子必須在社會上“做些事情”,對國家文化盡責,這是中國兩千年來的傳統,所以才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名句。西方各國,也有這樣的傳統,法國“文人”至今仍不離薩特所謂的“Engagement”(承擔精神),對人生如此,對社會文化更是如此。
20世紀的中國,政治上動盪不安,早期軍閥割據,使得大部分知識分子與政治脫了節,“五四”後大批文人由北京湧入上海,大半也是這個原因。於是,在十里洋場,租界仍未撤除的上海,這些文人能夠做些什麼?古代受了教育幾乎就等於可以做官,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後,知識分子已不再有制度上的橋樑,於是,教育非但沒有帶來“權力”,卻使受過教育的人感到“割勢”,其所割之“勢”,豈非中國兩千年傳統所遺留下來的政治之“勢”?
從事文學寫作,對於古代的士大夫階級,是一種業餘的消遣,或是在異族統治下不得已之舉(如元朝之戲曲小說),但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寫作不但成了“正業”,而且成了知識分子僅有的少數職業之一。知識分子當然可以教書,也有不少“文人”在大學裡兼教職,但學院畢竟是一座象牙塔,適值多事之秋,不少“悲天憫人”之士,不願意逃避在書堆里,而且,正逢“五四”思潮鼎盛之時,不少人想以小說、雜文來改革社會風氣,介紹西方文化的新潮流。魯迅由廈門、廣州跑回上海,棄教鞭而從筆桿,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許多自暴自棄、自哀自慚的外表遮蔽下,也藏有不少為知識分子應有的職責所困擾的“有心人”,郁達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酗酒、玩女人、性變態,大部分是自相誇飾的幌子,他頹廢的面具,蓋不住一顆赤誠之心,在上面提到的同一篇短文中,他又寫道:我若要辭絕虛偽的罪惡,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寫出來。世人若罵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認的,世人若罵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認的,罵我無恥,罵我發牢騷,都不要緊,我只求世人不說我對自家的思想取虛偽的態度就對了,我只求世人能夠了解我內心的苦悶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