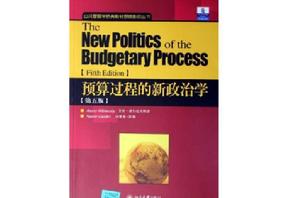生平與著述
威爾達夫斯基的漸進預算理論主導美國政府預算研究領域近30年,其登峰造極的學術生涯引人入境。
威爾達夫斯基的學說著作涵蓋兩大領域:公共政策與政府預算,其中重要學說-漸進預算,從政策分析、漸進主義到建構了三組比較模式將漸進預算帶入美國政府財政上實務的運用。
威爾達夫斯基是俄羅斯猶太后裔,於1930年出生在紐約。他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區長大,並在魯克林區學院(Brooklyn College)完成大學學業。威爾達夫斯基取得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後,隨即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任教,直到其終年。在柏克萊,維達夫斯基曾出任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系系主任,以及公共政策研究學院的創院院長。曾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一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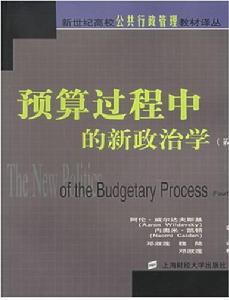 艾侖·威爾達夫斯基
艾侖·威爾達夫斯基威爾達夫斯基是林德布羅姆(Charles. Lindblom)受業弟子中最知名的學者,他的漸進預算(Incremental Budgeting)理論曾經主導美國政府預算研究領域長達二十年,此一理論即是承襲林德布羅姆的漸進主義理論。在耶魯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恩師林德布羅姆對維達夫斯基照顧有加。例如,維達夫斯基在攻讀博士班期間也擔任助教(T.A., Teaching Assistant)的工作,往往在周三中午下課未用午餐即趕來參加午餐討論會,每次均由林德布羅姆所長親自為門生準備三明治與咖啡,恩師之情傳為佳話,將維達夫斯基稱之為林德布羅姆的“嫡傳大弟子”,是一點都不為過。
威爾達夫斯基的理論建構
威爾達夫斯基的學說著作涵蓋兩大領域:公共政策與政府預算。
政策分析所要解決的問題應當在政府的能力範圍之內。如果超出能力範圍必將導致政策失敗;與其讓政府政策失敗,實不如“在目標上作策略性的撤退”(strategic retreat on objectives),來得符合實際。他說:“設計的年代已經過去,執行的年代也已經過去,而修正目標的時代已經來臨”。於是,威爾達夫斯基提出了組織安全的運作規則:如果組織的運作要被視為運作成功,他一定去追求可以控制的目標,來取代那些不能控制和獲知的目標。
威爾達夫斯基(1961)直接指出:預算決策的過程是赤裸裸的政治談判,並非根據成本效益分析所作的理性考慮。換句話說,他認為規範性的預算理論在民主國家是行不通的,民主國家存在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利益衝突,預算在本質上的政治性難以抹煞,經濟學的原則在政治現實中只能妥協。就此層面來分析,林德布羅姆與威爾達夫斯基均是倡導“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the liberal democracy)份子,他們主張“互動”,而且是“市場互動”來幫助人類解決問題。 在威爾達夫斯基看來,政策分析的工作是在探討政策設計、問題界定、與偏好形成三者之間互動影響關係的過程。政策分析的範圍和標準,不應該狹隘的根植在經濟學的效用標準(utilitarian norm)或效率分析(efficiency analysis)的概念上,而應該深層考慮兩種不同的概念:一是利益的調和(interest reconciliation):問題應如何建構,讓持有不同價值偏好的黨派被說服去調和各自的意志,使達成同意的結果。二是方案的慎慮(deliberation):一個方案的推出不僅要考慮目標,更要研究可能性;既要說明可欲的,也要注重可行的,更讓參與方案者彼此切磋商討,開拓知識的領域,並且學會預期行動的長期後果,以改善本身的視野。
政策分析的學者主要工作除了應該具有分析的能力,還要考慮行動的面向;不僅成為分析家,也要扮演推薦者,更要懂得權力的運作。因此,政策分析所發掘的問題是要決策者能夠處理的問題,在“知識與權力共享”的情形下,考慮目標與手段的連鎖關係。身為一位政策分析家,應該了解政策分析是“規約”的工作,隨時注意“應然”層面與“說服”的運用,把政策的可行性是為該項政策優劣的檢定標準。
政策建構的兩種模式
| 模式一 | VS | 模式二 |
| 資源 resources | versus | 目標 objectives |
| 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 | versus | 知識思考 intellectual cogitation |
| 教條 dogma | versus | 懷疑主義 skepticism |
“資源VS目標”模式
威爾達夫斯基的論點而言,時下的政策分析家不是注意資源的分配,就是考慮目標的追求,很少將兩者關係同時兼顧,任何分析的工作應將“可欲的”和“可行的”相提並論,政策的過程不僅應該注意目標的設定,更應考慮組織的誘因(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後者是政策分析應致力處理的永久問題。
威爾達夫斯基指出政策分析就是發現問題癥結之所在,研擬政策方案,建立衡量標準(criteria),並依據這些標準,權衡政策方案之利弊得失。政策分析與政策規劃的意義其實是相通的。兩者都包含兩項主要活動:一是診斷(Diagnosis),其目的在於了解問題癥結之所在,此階段的工作是找出問題的肇因,確立政策目標:另一是處方(Prescription),乃是透過政策分析程式,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
他指出「在目標上策略的撤退」(strategic retreat on objectives)應是未來政策的轉移方向。政策永久是它本身的起源(policy as its own cause),任何政策的誕生,與其說來自外來的環境,不如說是來自內部引發的動力。
“社會互動VS知識思考”模式
林德布羅姆在《政治與市場》(Politics and Markets,1977)一書中,他認為在人類社會有兩種社會控制,一是權威體系,講究的是教條灌輸,命令服從;另一個是利伯維爾場,強調的是廣告倡導、自由交易、遊說勸導等。
威爾達夫斯基承續林德布羅姆的架構,闡釋在多元競爭的制度里,政策的設計形式上是經由個人心智的深思熟慮的結果,實際上是社會互動的產品。動機雖是政策的基礎,但結果則是非預期的;智慧蘊含在互動之中。
威爾達夫斯基引用上述社會互動與知識思考的模式,配合政府體制與經濟發展政策的運作,提出了經濟發展的合作-拘束模式(cooperative-consent model)與衝突-合意模式(conflict-consent model)。前者認為機關組織往往相互衝突,因此需要受拘束,始可達成合作、共赴事功的境界;經濟發展一如官僚規劃,強調的是層級節制、協調、一致性;後者主張組織機關可經由和議方式解決彼此的歧見,不必刻意要求各單位相互一致,而應該尊重他們各自的差異,經濟發展遵從政治互動的原理,著重競爭、衝突、交易、和市場的運作。
“教條VS懷疑主義”模式
威爾達夫斯基認為市場和競爭性的政治體系,深具高度的懷疑色彩(highly skeptical),此特性雖可激揚人類的計算與批評能力,卻無法提供成員遵守“競賽規則”的有力論證,容易造成分崩離析的後果。為了使體制能夠延續下去,應該建立大眾對社會互動的正當性、合法性產生互信的基礎。威爾達夫斯基指出:懷疑主義需要依賴教條。在自我意識的社會中敬重的懷疑主義,要奠基在教條的基礎上。而政策分析的主要工作,便是在教條與懷疑主義之間,何者應開放批評與何者不應被批評之間劃一道界線。
懷疑主義和教條彼此對恃與張力之下,政策分析人員的主要工作,就是將張力予以內化。因為從事政策評估時,要想使評估能夠落實與套用,必須顧及目前組織權力運作的現況,於是與其找外來的專家評論,實不如由組織自己內部來進行評估。威爾達夫斯基認為一個理想的組織就是自我評估的組織(self-evaluating organization)。任何組織都不喜歡評估,認為評估是針對其任務、人力、權力進行種種挑戰。在這不友善的氣氛中,評估人員的地位編制、爭取支持、學習與他人共處都是重要的課程。評估的問題始終是個組織的問題,必須使知識與權力結合,科學懷疑與社會信賴調和,分析完美性和政治可行性結合,政策評估才有可能做到“向權力說真理”。
從漸進主義到漸進預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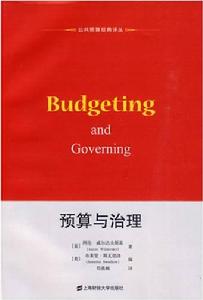 艾侖·威爾達夫斯基
艾侖·威爾達夫斯基漸進主義( Incrementalism)源自於西蒙的有限理性決策模型,在林德布羅姆的開拓之下成為政策分析的主流模型。威爾達夫斯基則是在林德布羅姆建構的理論基礎上,將此理念引入到行政預算的設計當中。
公共預算理論分為描述性的(descriptive)與規範性的(normative)兩類(Rubin, 1990:179)。曾有學者(例如 V.O.Key)試圖建立一套規範性的政府預算理論但卻未能如願。1964年威爾達夫斯基在《預算過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Budgetary Process)一書中提出了政府預算中最具影響力的描述性理論,這就是“漸進預算理論”。隨後的幾十年來成為政府預算之研究典範。
在預算過程中,政府預算是行政首長、官僚人員、民意代表和各個利益團體等預算參與者反覆協商調適的過程,在漸進的預算策略下,所有參與者都將獲益,預算決策過程的利害衝突可減到最低。而決策的結果表現在政府編列當年度預算要求時,往往以前一年度的預算規模作為基礎,再加上小幅的成長,基本上,行政部門每年度所要爭取的即是“增量”(increment)部分。
基本上,政府預算之“漸進主義”是建立在相關預算參與者在預算過程中所引發互動的三個假設上:
(一)預算角色的區別(Compartmentalization of budget role):預算過程中的參與者,大多數對預算採取一個有限的觀點,行政部門試圖增加預算,相對的,管理與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則扮演著減少行政部門要求的角色,國會議員則希望增加對選區選民的支出,以利將來競選連任,參與者在過程中期望對其個別預算項目採取策略行動,並影響預算增量的規模。
(二)行政部門的的基礎(Agency’s base):行政部門以過去支出標準作為基礎,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預算過程中,政黨為了擺脫行政部門計畫方案廣泛瑣碎的評估,經常忽略了預算基礎並著重在預算增量之上,因此很少對行政部門所提出之計畫案作全面性的審議,實務上亦難以逐一評估。
(三)穩定性(Stability):預算結果通常是穩定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撥款過程排除對預算清楚(占撥款總額的絕大部分)的審議,二是因為不同的預算的循環過程中,參與者經常是固定而無太大的變動,更使得預算過程中的協商與策略行動,也保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威爾達夫斯基首先將政府預算視為“政治過程”,試圖以“漸進主義”作為政府預算的分析模型,並認為以“漸進預算”來描述政府預算的形成與發展是相當適合的。
其主要理由為:
–政府預算是逐漸發展的,而且去年的預算撥款是決定今年預算的內容與多寡的主要因素,政府預算的大部份是往年決策下的產物。
–行政部門之預算編制過程中,通常是以去年的預算範圍作為基礎,很少注意或未曾積極重新考慮現有計畫方案之價值,而只是作有限度的增加或減少,而預算之審議也只是特別注意既定增加或減少的範圍。
–行政部門欲建立本身之預算基礎,並試圖擴充,但是行政部門是以“漸進”的方式逐步增加預算基礎。而立法部門預知行政部門將要做出超額的預算要求,因此就會對行政部門所提之要求作“漸進”的削減。換言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各自運用策略行動以達到本身的預算目標。
威爾達夫斯基極力主張要將政策分析融入預算過程的真實世界,並倡議預算局(Bureau of the Budget)應要求每一個執行單位有重大的預算計畫或預算的變更時,必須附上“政策分析備忘錄”,對預算變更的政策原因作出交代。
威爾達夫斯基認為,將政策分析與預算籌編的結合,必須由單位主管與政策分析專家先針對重大政策議題與法案來研究設定執行的時間表(也許六個月至數年),一旦某一研究分析的結果獲得主管單位的認可,即可將政策建議轉化為當年度的預算計畫,而政策研究分析的備忘錄也可以使預算項目編列更具說服力,以獲得國會及民眾較大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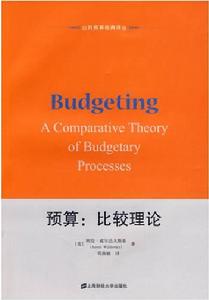 艾侖·威爾達夫斯基
艾侖·威爾達夫斯基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前期,在林德布羅姆與威爾達夫斯基的倡導之下,漸進主義的概念開始興盛並成為政府制定公共預算的分析模型之一。1960年代後期之後,公共預算研究的學者以實際的數據來驗證公共預算的制定是否符合漸進主義的原則。這些研究結論雖不盡相同,但是漸進主義的分析模型,顯然成為公共預算研究的主要趨勢。
具體而言,威爾達夫斯基認為,政府預算是行政首長、官僚人員、民意代表和各個利益團體等預算參與者反覆協商調適的整個過程。政府預算書的內容具又高度的複雜性(complexity),而過程又充滿政治妥協與調適。
概言之,政府預算具有下列特質:
經驗的(experiential):處理龐大預算數字最容易的方法就是靠過去的經驗。
簡化的(simplified):預算項目如此繁複,國會往往傾向於採用簡化的方法來決定預算,省略審視固定支出或既有法定計畫,而將觀察重點放在新增計畫。
滿意的(satisfying):通常預算資源分配的決策官員會儘可能滿足各方需求,讓每一位預算參與者都有收穫(那怕只是小贏),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與反彈。
漸進的(incremental):上述情形推演的結果,使得決定今年度預算內容與額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上一年度的預算基礎(base),通常計畫支出的提案者會以漸進的方式,每年逐步擴充對於預算資源的需求,而資源分配的決策者,也對提出來的預算案做出漸進式的刪減或修改。
評論
貢獻
威爾達夫斯提出預算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產物,預算過程實際上乃是紀錄不同黨派、政治團體與代表間的衝突、妥協、協商的過程。
威爾達夫斯提出要在組織的能力範圍之內去解決政策問題,而不是超越其能力範圍。1950年代以後管理信息系統之所以失敗,在於它不自量力想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他主張現在是修正目標的時候,與其讓政府政策失敗,不如“在目標作策略性的轍退” 來的符合實際。
威爾達夫斯基認為身為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學者,考慮的是政策分析如何與社會的多元、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相結合,並非相異疏離。因此,所謂的分析與思考只能看成寓意於社會互動之中,進一步幫助人們去學習與啟蒙,培養出公民性。
威爾達夫斯基認為政策分析的工作,不僅在改善政策的活動,也應在促進人民道德發展的責任,培養社會更多的人具有“公民歸屬感”(citizenship)的積極態度(citizenship),大致可以包括:
個人的自由:讓人民有採取獨立行動的能力,懂得分析分析任何行動方案的利弊得失,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偏好與價值。
彼此的互惠:有“與人共享”的意願,能夠了解別人的利益,以互動、妥協、交易方式,促進社會的互賴與和諧。
學習的能力:不斷的檢討與改變政策的能力。了解任何政策問題既是人為的,必有其易誤性(fallibility),因此任何人、制度的可貴之處在坦承、學習、與改正錯誤。
威爾達夫斯基認為政府預算的決策過程,也是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預算政治的參與者一樣具有有限理性和多元化的特徵,他將漸進主義與政府預算的決策過程連結在一起,主張以漸進的模型來描述政府資源的配置過程,為政治預算的理論累積和研究成果,創下不可磨滅的貢獻。
局限
反對者對於漸進預算理論的描述和規範能力都持著保留態度,他們不但懷疑“預算決策的過程和結果實際上是漸進的”說法,也反擊“預算決策應該是漸進增加的”建議。許多學者認為,“漸進”的定義和“增量”的定義都模糊不清。例如,究竟改變的幅度必須在多少百分比之內才符合“漸進”的定義呢?如果改變額度雖小,但卻是刪除預算的負面改變,並非正向的成長,是否也符合“漸進”的定義呢?這兩個問題令人困擾。
漸進預算的實證解釋力高低,與所分析的數據的類別有很大的關係。“漸進預算”可能適合描述與解釋某一類的公共支出,未必適用整個預算的過程及結果。其次,數據層次的高低,也可能影響漸進預算理論的適用性。例如在“機關”的層次進行驗證時,漸進理論獲得支持,但在機關下分析各“計畫”層次的預算數據,發現不規則的年度預算變化,而且沒有呈現逐漸增加的穩定成長趨勢。
有些批評者認為,即使漸進預算的理論很成功描述大部分預算決策行為與結果,它沒有解釋如何(how)和何時(when)政府預算會產生不規則的變化,這些偏離漸進預算的決策過程與結果,比漸進預算行為更重要、更有研究價值。
威爾達夫斯基的漸進預算的概念在過去幾十年廣為公共行政學者引用,不論是歐美各國甚至開發中國家來說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威爾達夫斯基的得意門生凱丹(Naomi Caiden)與懷特(Joseph White)在1995年共同主編了《預算、政策與政治:對威爾達夫斯基的追思》( Budgeting , Policy, Politics:An Appreciation of Aaron Wildavsky)一書紀念這位大師,他們在前言中有兩段話,足堪回味:
“除了學者風範之外,威爾達夫斯基的人格特質將被人懷念。他對人總是如此的敦厚與體貼。他的誠懇與不虛偽,始終如一”;
“經由他的著作、專業行動與生命,威爾達夫斯基觸動了、也影響無數的朋友、合作夥伴、同事、學生、研究者、實務界及其他相關人士。他是如此慷慨地與大家分享觀念(idea)、時間(time)、資源(resources)、功勞(attribution)和鼓勵(encouragement)”。
由此可見,大師的做人和做學問同樣綻放耀眼的光芒。雖然,在各國政府財政每況愈下呈現困窘情形,漸進預算的色彩逐漸淡化,卻無損於威爾達夫斯基做為當代行政學界大師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