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武歆於1962年出生於山東省。一級作家。在天津作協從事專業創作。2004年曾在魯迅文學院第三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習結業。
作品風格
 武歆
武歆武歆創作的長篇小說《樹雨》是一部用現代眼光,通過兒子的視角,來想像、揣摩、猜測、探尋父母各自曲折的人生經歷以及他們五十年怪異而又神奇的婚姻生活的長篇小說。小說在跳躍性地講述中,借用與父母一生密切相關的“樹”和“雨”,在隱喻和暗示中,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多面性與複雜性,展現了人類頑強的生命意識。
武歆是一位很優秀的小說家。
作品集
| 《兩個人的車站》 | 《私事》 | 《諾言》 | 《幸福的女人》 | 《大春的河》 |
| 《尋找磨刀人》 | 《筆劃》 | 《酒精夜》 | 《一九四九年的婚姻》 | 《君子碑》 |
| 《紅馬甲》 | 《黑白女人》 | 《無腳的小瑋》 | 《喜妹》 | 《我愛北京天安門》 |
| 《梨園陳釀》 | 《小灰的經驗》 | 《門衛》 | 《鳥巢》 | 《中國象棋》 |
| 《大火》 | 《白鞋》 | 《用什麼來揭開秘密》 | 《懸掛鎖頭的門》 | 《枝岈關》 |
| 《手機的故事》 | 《唇紅》 | 《馬秀英的戀愛史》 | 《突如其來的火車》 | 《老鄭的部落格》 |
談創作
1、無聲的拷問
武歆去了兩次安徽省。第一次基本上是在市、縣間穿梭,是一次有組織有安排的民間採訪,那一次採訪的收穫是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和若干散文;第二次完全是在大別山,住了十天的時間。其實原本去大別山,是受邀做另外一件事情的,但那件事情過於紛繁和複雜,搞得我昏頭漲腦,最後也沒有做成,但是沒想到卻誕生了這部中篇小說《枝岈關》。
說起來令人可笑,在沒去大別山之前,大別山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座山——一座完全能呈現在我的視野之內的山。當武歆在與一位老鄉做此交流時,那位老鄉把手高高的舉起來,朝天空中有力地揮舞著,居高臨下地大聲對我說,這連綿起伏的全是大別山。望著他那神態和手勢,武歆明白在他的眼裡,這天下就是大別山。武歆與這位老鄉巨大的視角差異,就像一條落差很大的河流,當即在我的內心深處奔騰起來。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武歆接觸了一座座山峰,也接觸了一個個大別山人。在與他們的聊天中,武歆發現了他們有的是過去紅軍和赤衛隊的後代,也有的是白匪和土匪的後代,他們的父輩曾在這片大山中,為了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觀,將子彈射向對方,把大刀砍向對方。但是現在,這些後人們相處得特別融洽,他們是生意上的好夥伴,是酒桌上的好朋友,開飯店、開商店,做買賣,每個人都在忙著賺錢,都在忙著點鈔票,當說起父輩們過去的交鋒、過去的仇恨、過去的死亡,還有過去的殘酷時,他們的臉上都帶著輕鬆的笑容。那一天的晚上,武歆失眠了,僅僅是為了他們的笑容。
武歆生活中是一個溫和的人,武歆不贊同爭鬥,也不贊同血腥,當然武歆也不贊同這些大別山人因為過去父輩們的原因,現在劍拔弩張、怒目相對,但武歆總是為他們的笑容而感到不安,一種無法言說的不安,這樣的不安一直伴隨我離開大別山。也正是這樣的原因,我覺得應該為這種“不安”說點什麼,寫點什麼,但我沒有馬上動筆,一直在思考。
 《枝岈關》中的男女主角
《枝岈關》中的男女主角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個人,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遺忘——忘掉過去的不幸、忘掉過去的艱難,忘掉過去的被損害,忘掉過去的歷史。是的,武歆說應該往前看,但往前看,並不意味著過去的消亡。“過去”,是一個背景,是一雙眼睛,離去的越遙遠,它升得越高,它把我們看得越清楚,我們現在的一切,都會在“過去”的審視之下。
《枝岈關》小說,是武歆在離開大別山的一年多以後開始動筆的。武歆感到一種莫名的躁動,外面不時的響起鞭炮聲,電視裡鶯歌燕舞,到處都是問好聲,都是發財的祝願,但是武歆卻再次想到了那些“笑容”。《枝岈關》這篇小說,武歆寫得很快,三天就寫完了,平均一天一萬字,但也是武歆寫得最累的一篇小說。當他寫到那位16歲的赤衛軍小戰士被捆綁著遊街、最後死在棍棒下時,武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淚流滿面。這是他寫小說以來,惟一的一次為小說里的人物而流淚,而且哭得那樣不可收拾。是的,他們還是孩子,在當年紅軍長征的隊伍里,就有許多這樣的孩子——“紅小鬼”,就是這些孩子的犧牲,支撐起了共和國的大廈。中國革命早期的輝煌的歷史,可以說,就是由這些孩子們譜寫的。
2、悲泣的解答
 大別山地圖
大別山地圖當“敘述革命”遭遇讀者的冷遇之後,堅持現實主義創作的“底層寫作”隆重登場,過去我們爭論了許久的“怎么寫”和“寫什麼”,又做了一次大規模地切換,當然也引起了許多人的評判,一時間各種觀點和議論撲天蓋地。武歆不是一個喜歡發表宣言的人,他只認定寫作需要耐心,需要抒寫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在耐心中完成真誠的敘述。在過去和現在,武歆一直堅信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
武歆的《我愛北京天安門》,源於一位朋友的感嘆。有一天的夜晚,那位朋友給我打來電話,他語調沉重地對武歆說,他的妹妹好長時間不理他了,至於什麼原因,他不知道,為此他特別痛苦,因為他只有這一個妹妹。朋友還跟我感嘆,現在最不好處的關係,就是親情的關係。說完,他放下了電話。當時正是冬季,窗外刮著大風,我再也無法入睡,想了許多。
由於市場經濟帶來的諸多影響之一,就是人與人關係的淡遠,當然也包括親情的疏遠和陌生。母女打官司,父子成仇人,兄弟姐妹之間為了遺產在法庭上唇槍舌劍,成為原告與被告……這樣的事情現在太多了,我們已經見多不怪。中國傳統的最為人們看重的親情關係,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遭遇強烈地信任危機和嚴厲地拷問,無論是責難方還是委屈方——“原告”和“被告”——都應該冷靜下來,好好的想一想。
創作作品
 作品《我愛北京天安門》
作品《我愛北京天安門》天津作家武歆在《中國象棋》《當代》2006年6期)里講了一個關於謎語的故事。在這個虛構的謎語故事被講述的同時,小說的藝術魅力也成了一個謎。在敘述學的視野下,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揭示這篇小說的魅力之謎。
第一,小說敘述視角的選擇。小說講述的是鉚焊車間的怪人楚小棋的故事。可是,在小說中,主人公楚小棋是被看的,是沉默的、沒有發言權的。小說通過敘述者“自己”的眼睛和楚小棋周圍人的眼睛來看楚小棋,讀者只能從敘述者的敘述視角中不斷進行猜測,不斷回味和咀嚼。
在敘述視角的選擇上,小說採取第三人稱的限知敘述。敘述者明了在楚小棋身上發生的一切故事,包括他的爺爺楚老棋和爸爸楚大棋的故事,也明了楚小棋的工友們對他的評價和種種猜測,可就是不了解楚小棋的為人和想法。而且,對於知道楚小棋想法的高明康和楚大棋的行為和想法也一無所知。和其他工友一樣,敘述者是故事內的人物,是鉚焊車間中不了解楚小棋人群中一員。正因為敘述視角的限制,讀者看到的只能是一些表象,而這正是謎語的最佳講述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隱含的作者不可能坐視敘述者由於限知敘述所表現出的對謎底的無知,在小說末尾忍不住跳出來說話:“高明康禁不住說了一句,原來是這樣呀……”高明康知道了謎底,讀者也能有所體悟。
第二,空白點的設定和文本的插入。楚小棋是一個謎語,他的貌醜、棋藝和美妻構成了三個謎面。車間主任高明康是一個軟硬不吃的人,而楚小棋用什麼打動高明康,和他的關係突然之間親近起來。楚小棋為突然之間再也不下棋。車間裡的人們掛著徹悟的神情說:“原來是這樣呀”,究竟指的是什麼?
在這篇小說里有太多的空白點。空白點被填充的過程就是解讀謎語、猜測謎底的過程。在小說中,作者通過空白點的設定製造撲朔迷離的閱讀效果。似乎又漫不經心地通過文本的插入來提供提示謎底的蛛絲馬跡。比如將楚老棋點撥軍閥的故事,楚大棋開衣櫃找棋盒的故事的插入,看似很隨意,其實都是獨具匠心。楚小棋死了,關於他謎語只有通過這些插入的文本來揭示。
可以說,小說中空白點的設定關乎謎面,文本的插入關乎謎底,兩者相得益彰,意味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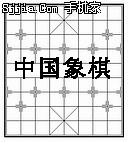 武歆《中國象棋》
武歆《中國象棋》第三,“中國象棋”的隱喻和對謎底的猜測。工人們對楚小棋和高明康的談話內容作了猜測,認為他們在講故事,而不是在談論象棋,因為他們並沒有互相過招。但是,高明康在楚小棋死後看到了他的爸爸楚大棋,看到了他的柜子,看到了樟木棋盒後,突然之間徹悟了。不但棋藝突飛猛進,而且演唱起京劇來聲情並茂。由此,我們可以猜想楚小棋講的故事肯定和象棋和關。因為,象棋就是楚小棋。同時,象棋也是楚老棋和楚大棋。
理解了楚小棋和他的故事,自然也能把握中國象棋的精髓所在。而對楚小棋的了解,完全可以從楚老棋的故事和楚大棋的用心中見出。楚大棋教楚小棋“目的就是為了繼承楚家優良傳統,長大後能成為他爺爺那樣的高手”。而楚小棋的確是做到了,他把高明康點撥明白了。
楚小棋的故事就是中國象棋的故事。所以說,這篇小說的謎底就是它的題目――中國象棋。
社會評價
 武歆《幸福女人》
武歆《幸福女人》武歆的小說敘事的方法通常就是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全知全能。另一種是受限制的觀察。如今,還流行另一種寫法,就是讓兩個以上的人物去描述同一個故事,共同完成一次完整的敘述,不過,更多的情形是,作家通過這樣的描述讓故事呈現出更多的主題側面,在分裂與聚攏間達成某種張力,這樣的寫法多見於長篇小說。
讀者回到前兩種敘述方法。一個固定的視角究竟如何在小說里發揮作用,並能夠不露痕跡地完成一次艱難的敘述,這是對小說家對故事的控制能力的極大考驗。武歆的中篇小說《天車》(《中國作家》2005年第七期)是一個值得剖析的文本。這篇小說的核心人物是一個叫李美玲的年輕女性,故事的場景集中在一部天車的操作間裡。這個狹窄的空間裡發生的故事,卻是由一雙“看不透”的眼睛來觀察描述的,這是一種讓人著急、也極具難度的寫作策略。“小何”雖然是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但作為李美玲的學徒,他對人生世事的了解更加稀少。高高在上的天車裡,小何本人毫無製造故事的能力,而且他也看不透那裡發生的一切,但一點一點,他單純得有點犯傻的眼睛,為我們完成了一次有序的描述。李美玲被車間主任“羅主任”霸占,電工馬福海求愛無功而返,男女工人通過巴結李美玲而謀求在“羅主任”權力棒下的生存空間。故事稍一延伸,老到的讀者輕易即可看穿其實質內容,於是小說里的敘述人“小何”的看不透本身,倒成了閱讀者感興趣的要素。
 作品《樹雨》
作品《樹雨》武歆始終讓敘述者小何的眼睛停留在恍惚、懵懂和略有所悟的交叉中。借著這雙沒有穿透能力的眼睛,去穿透故事的外殼,展現一個更加複雜的人生世界。李美玲和羅主任的故事如果直接去講述,很可能就是一則平庸不過的誹聞,正是小何這雙看不透的眼睛,和我們一起忽略了鐵定發生的事實,天車裡發生的一切沒有一次得到直接呈現,而因此生髮出的種種傳聞、議論、反應,讓故事擁有了小說性。於是,與其說敘述人“小何”在向我們講述故事,不如說他是在把故事背後生長著的枝杈一點一點道出。於是,一個發生在工廠里的男女故事,變成了一個關於生存和為了生存人們如何掙扎、努力和付出的人生主題。這就是敘述技巧的作用,看不透的魅力在於可以保持單純,又呈現複雜。當然,就《天車》本身而言,武歆太過注重控制,連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也借小何的懵懂半露半掩,使故事始終在一種情調和張力下推進,缺少必要的轉折和高潮。他還應當嘗試適度放量。
每一篇小說的寫作都是一次艱難的跳躍,姿態、分寸、力度、平衡,動作的專業化和連貫性都會受到考驗。這也正是武歆小說寫作的誘人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