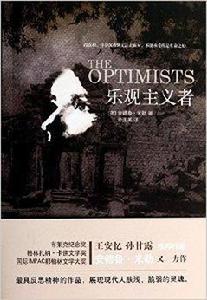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介紹
最具反思精神的作品,展現現代人膚淺、脆弱的靈魂。一段真相,並非沉重到無法去面對,不能承受的是生命之輕。
安德魯·米勒又一力作!
《樂觀主義者》講述了一個攝影記者克萊姆在目睹了盧安達慘案後,如何療傷的過程,表達了反對暴力、反對屠殺的積極思想。 克萊姆是一名攝影記者,剛從盧安達一次糟糕的派遣任務回到倫敦。在那裡,他目睹了一起發生在前比利時殖民地一座教堂的大屠殺後。全書開始時就很漂亮,克萊姆退化到一種類似道德發燒的狀態,在倫敦街頭遊蕩,他孤寂,無自治力又充滿侵略性,對慘象的回憶有痛苦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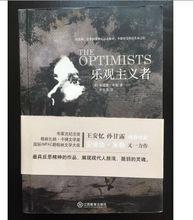 樂觀主義者
樂觀主義者作者介紹
作者:(英)安德魯·米勒 譯者:孫亞英
安德魯·米勒(Andrew Miller),英國著名小說家,1960年生於英國布里斯托。
他曾於1991年在東安格利亞大學學習創意寫作,1995在蘭開斯特大學發表了論述批評性寫作與創意寫作的博士論文。
他發表第一部小說的《無極之痛》(INGENIOUS PAIN)獲得了三個文學大獎,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Literary Award,英國作家D.H.勞倫斯、E.M.福斯特、格雷厄姆·格林都是該獎獲得者)。目前這部小說已經被翻譯成36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跋
文摘
N教堂大屠殺發生後,克萊姆·格拉斯飛回了倫敦。他把靴子和旅行箱中的衣物一股腦兒扔進一隻黑色的垃圾袋裡,提到一樓,丟進庭園裡的一個垃圾箱,回到家中,死命地搓洗雙手。第二天早晨,他聽到沿街收垃圾的清潔工的叫喊聲。後來,朝外看時,發現一溜空垃圾桶整齊地靠欄桿排放著。他躺在地板上,瞅著光影在天花板上移動,似乎在兩種想法之間迷失了方向。整個白天就這樣過去了,晚上就這樣過去了,整整一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他都開始有點數不清日子了。
正值五月,天氣雖說尚在暮春,但已是夏日氣象。街道兩旁的樹木枝繁葉茂,滿眼濃綠,纖塵不染。到了傍晚時分,車流緩緩前移,緊閉的車窗內,音樂聲震耳欲聾。孩子們放學了,有的在大街上大聲爭論著什麼,有的對著牆踢皮球,有的唱著祖母哼過的兒歌:“蘋果樹陰下,男友與我說悄悄話……”
隔壁房子裡住著幾個吸毒的人,經常開著攜帶型收音機,在凌晨時分發出鬼哭狼嚎般的聲音,如同快要被拽進地獄一般。偶爾,他們也會向窗外擲出東西。克萊姆回家兩周后,隔壁樓上一扇窗戶里拋下了一隻十升裝油漆桶,桶身被摔裂了,人行道上、陰溝里大約有兩平方米的地方都鋪上了紫色的油漆,厚度有兩三厘米。在陽光的照射下,油漆的表面結上了一層硬痂,但底下依然是濕的。很快,人行道上出現了紫色的腳印,逐漸變淺,甚至還出現了一串串紫色的狗腳印,繞電線桿一圈後,朝著哈羅路的方向逐漸消失了。
那些吸毒的人鬧得可歡了。他們聚在家門口的台階上,哈哈大笑,揮動著手裡的瓶子,如同凱旋的叛軍。一星期後,他們又拋出了一桶橙色的油漆,留下了一攤偌大的碎蛋黃。
克萊姆的杜馬克相機包就靠門口放著,裡頭有尼康相機、徠佧相機、數據線、閃光燈、鏡頭,還有二三十卷膠捲。看著紫色人行道上的煎蛋黃,他琢磨著如何捕捉這一畫面。這一反應,無它,完全是下意識的,屬於職業習慣。相機暫時就擱在包里吧,等有了精力再決定如何處置。隱隱地,克萊姆似乎看到。自己將相機送回金斯利的店裡變賣。徠佧相機會值很大一筆錢,他的老夥計尼康相機也還值些錢,大概能抵一個月的租金吧。
月底的一個午後,那些吸毒的傢伙被驅逐出去了。先是開來了兩輛警車,接著市議會的工作人員也趕來了,還帶來了鋼柵欄,開始將那棟房屋封鎖起來。他們在木門上包上鐵皮,窗戶圍上了鋼條。在屋前的欄桿邊,他們留下了一小堆個人物品——一隻睡袋、一個電吹風、幾枝塑膠花和一根拐杖。那些吸毒者,尤其是其中幾個女的,大吼大叫,還揮舞著拳頭。克萊姆從二樓的視窗瞧著,對這些人所表現出來的激情不由得感到佩服。他尋思著,他們是否明白這種激情毫無意義,或許,這種毫無意義才正是其激情的根源。一切準備停當,市議會的工作人員離開了,警察也爬上了警車。那些遭到驅逐的吸毒者還在狂亂地揮舞著拳頭,但終於三三兩兩地,前往教區各大收容所,以及外賣酒店。一些當地人站在外面,時有笑聲響起。
傍晚時分,克萊姆下樓來到大街上,格羅夫此時近乎死寂。他瞥了那所房子一眼,然後蹲下身子,手指滑過殘留的油漆。現在油漆的表面摸上去有點像指甲油,滑溜溜、硬邦邦的,稍稍有點起伏,但幾近平坦了。接著,在油膜的邊緣,在油漆與淺灰色鋪路石的交接處,他發現了一張稍顯模糊卻又十分精緻的樹葉輪廓。借著打火機火苗發出的光亮,克萊姆發現,那兒還有別的樹葉,散布在周圍。枯葉精緻的葉脈半遮半掩著,像躲在餐巾紙下的畫面。克萊姆很想知道這些影像是如何在這兒留存下來的,如何經受住去年的秋雨、去年的秋日陽光、成千上萬行人步伐的重量、腐敗物質散發出的能量,還有石頭的微量吸收的。克萊姆研究著,直到打火機燙得沒法再使用了。他想起了福克斯·塔爾博特那張用紙基負片法拍攝的樹葉,一張舉世驚嘆的照片:紙基負片法一詞本身源自希臘語“美”一詞。克萊姆雙膝著地。在他前面,那幢鋼條圍著的房屋在路燈下熠熠生輝。克萊姆低下頭。現在會發生點什麼事兒嗎?是可以撒手不管的事兒嗎?這就跟盼望得一場小病差不多。他咬了咬牙,摸了摸乾澀的雙眼。在他身後,在兩輛停靠著的小汽車之間,有兩個小孩子在偷偷地瞅著他,並開始咯咯地笑了起來。克萊姆費力地站起身來,上樓,回到公寓,又一次在起居室的地毯上躺了下來。
夜幕降臨後不久,書桌上的電話響起,鈴聲響過五次後,答錄機接起了電話。克萊姆錄下的提示說他出國了。電話機嘟了兩聲。對方停頓了一下,其間,克萊姆仿佛聽到了海鳥的叫聲,隨後是他父親的聲音:“是我。你回家後給我打個電話好嗎?”再次停頓了一下,接著是“謝謝”。P3-6
後記
N大屠殺以1994年發生在盧安達的暴行為藍本,有大量的文字記載可循。不過,本小說並不是描述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的,亦無此意。讀者如欲重溫盧安達發生的一切,可以閱讀費爾乾·凱恩(Fergal Keane)的《血的季節——盧安達之旅》(Season of Blood)或菲利浦·古雷維奇(Philip GourevitCh)同樣影響甚巨的《我想告訴你明天我們和家人將一同遇害》(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m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弗蘭克·西爾弗曼在多倫多引用的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的詩歌為《夢歌一》(Dream song 1)。克萊姆在西爾弗曼有關大屠殺的文章中讀到的詩句摘自同一詩人的《夢歌二九》(Dream song 29)。
作者心懷感激,鳴謝巴伐利亞的瓦爾德貝爾塔別墅和托斯卡納的桑塔·馬達來納基金會,連續幾個夏天,在前者風暴不息和後者宜人的氣候中,作者完成了本書的大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