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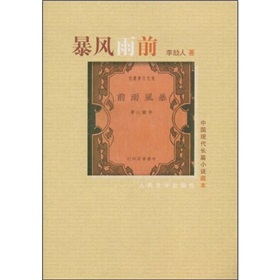 暴風雨前
暴風雨前《暴風雨前》的作者李劼人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一生留有五、六百萬字的著作和譯作。他的大河小說三部曲《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已經成為傳世之作。李劼人先生被他的同學郭沫若稱為“中國的左拉” ,他的三部曲被郭沫若譽為“小說的近代史”。 李先生從1935年起寫了三個連續性的長篇《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第一部),描寫辛亥革命前的社會生活。這三部小說都以作者的故鄉四川為背景。
目錄
第一部分新潮和舊浪
第二部分 下蓮池畔
第三部分 歧途上的羊
第四部分 暴風雨前
第五部分 運動會
前言
我國的長篇小說創作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作為現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則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受中外文學互動影響而產生的。五四時期的文化啟蒙運動使小說這個古老的文學樣式在華夏大地上從“稗官野史”升級到與詩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從茶餘飯後的消遣娛樂變為作家和讀者表現人生、看取社會的重要手段,在語言與形式上也經歷了由文言章回體到現代形態的蛻變。
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始,在白話短篇小說發展興盛的基礎上,長篇小說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達到創作的高峰,出現了巴金、老舍、茅盾、張恨水、李劼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駱駝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瀾》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體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社會生活和國民的生存狀態,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篇章。
為了系統展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成就,我們新編了這套“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藏本”系列圖書,選收1919至1949年間創作的有代表性的優秀長篇,為讀者相對完整地閱讀並珍藏這一時段的長篇小說提供一套優質的讀本。
精彩書摘
第一部分 新潮和舊浪
一
太平的成都城,老實說來,從李短褡褡、藍大順造反,以及石達開被土司所賣,捆綁在綠呢四人官轎中,抬到科甲巷口四大監門前殺頭以後,就是庚子年八國聯軍進北京,第二年余蠻子在川北起事,其聳動人心的程度,恐怕都不及這次事變的大罷?
全城二十幾將近三十萬人,誰不知道北門外的紅燈教鬧得多凶!
就連極其不愛管閒事,從早起來,只知道打掃、挑水、上街買小東西的暑襪街郝公館的打雜老龍,也不免時時刻刻在廚房中說到這件事。
他拿手背把野草般的鬍子順著右邊一抹道:“……你們看嘛!七七四十九天,道法一練成,八九萬人,轟一聲就殺進城來!那時,……”
正在切肉絲預備上飯的廚子駱師,又看了他一眼道:“那時又咱個呢?”
“咱個?……”他兩眼一瞪,伸出右手,仿佛就是一把削鐵如泥的鋼刀,連連做著殺人的姿勢道:“那就大開紅山,砍瓜切菜般殺將起來!先殺洋人,後殺官,殺到收租吃飯的紳糧!……”
駱師哈哈一笑道:“都殺完,只剩下你一個倒瓜不精的現世寶!”
他頗為莊嚴地搖了搖頭道:“莫亂說!剩下的人多哩!都是窮人。窮人便翻了身了。……大師兄身登九五!二師兄官封一字平肩王!窮人們都做官!……”
駱師把站在旁邊聽得入神的小跟班高升映了一眼道:“小高,別的窮人們都要做官了。我哩,不消說是光祿寺大夫,老龍哩,不消說是道台是見缸倒①。你呢?像你這個標緻小伙子,……依我的意思,封你去當太監。……哈哈!……”
高升紅著臉,把眼睛一眨道:“你老子才當太監!”
駱師笑道:“太監果然不好,連那話兒都要脫了。這樣好了,封你當相公,前後都有好處,對不對?”
“你爺爺才是相公!你龜兒,老不正經,總愛跟人家開玩笑!你看,老子總有一天端菜時,整你龜兒一個冤枉,你才曉得老子的厲害哩!”
老龍並不管他們說笑,依然正正經經地在說:“……豈止大師兄的法力高,能夠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就是廖觀音也了得!……”
高升忙說:“著!不錯!我也聽說來,有個廖觀音。說是生得很好看,果真的嗎?”
鬍子又是那么一抹,並把眼睛一鼓道:“你曉得,怎么會叫廖觀音呢?就是說生得活像觀音菩薩一樣!……我不是說她生得好,我只說她的法力。她會畫符。有一個人從幾丈高的崖上滾下來,把腦殼跌破了,腦髓都流了出來。幾個人把他抬到廖觀音跟前,哪個敢相信這人還救得活?你看她不慌不忙,端一碗清水,畫一道符,含水一口,向那人噴去,只說了聲:呀呀呸!那人立刻就好了,跳起來,一趟子就跑了幾里路。你看,這法力該大呀!”
伺候姨太太的李嫂,提著小木桶進來取熱水,向高升道:“老爺在會客,大高二爺又有事,你卻虱在這裡不出去!”
駱師道:“還捨得出去?遭老龍的廖觀音迷得連春秀都不擺在心上了!”
李嫂一面舀熱水,一面說道:“龍大爺又在講說紅燈教嗎?我問你,紅燈教到底啥時候才進城來?”
“七七四十九天,道法一練成,就要殺進城來了!”
“你聽見哪個說的,這樣真確?”
“你到街上去聽聽看,哪一條街,哪一家茶鋪里,不是這么在說?我還誑了你嗎?告訴你,我正巴不得他們早點進城!紅燈教法力無邊,一殺進城,就是我們窮人翻身的日子!你不要把龍大爺看走眼了,以後還不是要做幾天官的!”
李嫂哈哈大笑,笑得連瓢都拿不起了:“你不要做夢!就作興紗帽滿天飛,也飛不到你瓜娃子頭上來呀!”
駱師把切的東西在案頭上全預備好了,拿抹布揩著手道:“你不要這樣說,他現在不已是道台了嗎?”
“見缸倒是不是?……如今是倒抬,再一升,怕不是喊踩左踩右的順抬啦!①……哈哈!說得真笑人!”
老龍依然馬著臉,將他兩人瞅著道:“別個是正經話,你們總不信,到那一天,你們看,做官的總不止我一個人!”
駱師也正正經經地說道:“我倒告訴你一句好話!廚房裡頭,沒有外人,聽憑你打胡亂說幾句,不要緊。若在外頭,也這樣說,你緊防著些,老爺曉得,不把你飯碗砸了,你來問我!李大娘,大家看點情面,莫把他這些瓜話傳到上頭去啦!”
“這還待你說?哪個不曉得龍大爺是倒瓜不精的,若把他的渾話傳了上去,不就造了孽了?不過,人多嘴雜,像他這樣見人就信口開河,難免不有討好的人,當作奇聞故事,拿到上頭去講的。”
駱師道:“你指的是不是那個人?”
“倒不一定指她。公館大了,就難說話,誰信得過誰?就像春秀,不是我指門路,她能投到這地方來嗎?你們看見的,來時是啥子鬼相,現在是啥樣子。偏偏恩將仇報,專門尖嘴磨舌說我的壞話。看來,現在世道真壞了,當不得好人!我倒望紅燈教殺進城來,把這一起忘恩負義的東西,千刀萬剮地整倒注①!”
春秀的聲音早在過道門口喊了起來:“李大娘!姨太太問你提的熱水,提到哪兒去了!……也是啦!一進廚房,就是半天!……人家等著你在!”
她鏇走鏇答應“就來”,走到廚房門口,仍不免要站住把春秀咒罵幾句,才登登登地飛走了去。
郝公館的廚房裡,談的是紅燈教,郝公館的客廳里,不也正談的紅燈教嗎?
郝達三同他的兒子又三在客廳里所會的客,並不是尋常來往的熟客,而是一個初來乍見的少年。看樣子,不過二十五六歲,比又三隻大得五歲的光景。他的裝束很是別致:一件新縫的竹青洋緞夾袍子,衣領有一寸多高,袖口小到三寸,腰身不過五寸,緊緊地繃在身上;袍子上罩了件青條紋呢的短背心,也帶了條高領,而且是對襟的。更惹人眼睛的,第一是夾袍下面露了對青洋緞的散腳褲管,第二是褲管下面更露出一雙黑牛皮的朝元鞋。
褲管而不用帶子扎住,任其散在腳脛上,毫無收束,已覺得不順眼睛;至以牛皮做成朝元鞋子,又是一層薄皮底,公然穿出來拜客,更是見所未見。
加上一顆光頭,而髮辮又結得甚緊,又沒有蓄劉海,鼻樑上架了副時興的鴿蛋式鋼邊近視眼鏡。設若不因葛寰中大為誇獎了幾次,說是一個了不得的新人物,學通中外,才貫古今,我們實應該刮目相視的話,郝達三真會將他看成一個不知禮節的浮薄少年,而將拿起官場架子來對不住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