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方軍在一次論壇上作講演
方軍在一次論壇上作講演方軍是1954年生於北京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70年在首鋼當鉚工,1973年,參軍在鐵道兵六師汽車營服役,並在部隊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從部隊復員回到北京。
1984年在日本《讀賣新聞》北京分社當日本記者助手,繼到日本駐華大使館領事部工作。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
1990年在北京一家報社任記者,1991年後赴日本留學,曾在日本兩所大學學習社會學和經濟統計學, 1997年3月回國。12月發表了處女作成名作《我認識的鬼子兵》,之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多篇。
199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2002年自願離開工作崗位,專門從事寫作。2003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退。
兼任北京社會科學院中日關係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為北京社會科學院中日關係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系人民網(日本版)日本問題專家。
採訪記錄
欲揭“長沙會戰”面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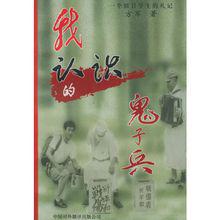 《我認識的鬼子兵》封面。
《我認識的鬼子兵》封面。抗日戰爭中,長沙會戰非常慘烈,2011年正計畫到長沙採訪親歷過長沙會戰的人。方軍曾在廣州採訪到三位曾經參加長沙會戰的原中國政府軍老軍官。
他目前最大的願望是,長沙能有單位與他聯繫,請這三位曾經在長沙地區與侵華日軍血戰的老軍官故地重遊。
“在抗日戰爭中第一次長沙會戰,中國軍隊消滅侵華日軍3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國軍隊殲滅侵華日軍4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侵華日軍5萬人。”幾年來,方軍一直在忙著採訪那些親歷過抗日戰爭的老人,並將他們稱作親歷抗戰的最後一批人。為採訪這些人,方軍赴日本,到緬甸,走遍了全國各地,耗費了無數的財力和精力,成了中國作協為數不多的現代抗戰文學作家。 爭分奪秒“搶救”“最後一批人”
使更多人了解抗戰史
採訪10 種人:1979年,方軍從部隊復員回到北京。次年,他開始了4年的夜大日語學習,畢業後,在日本《讀賣新聞》北京分社給日本記者當秘書,1991年赴日本留學,一邊打工掙學費,一邊採訪當年的侵華日軍老兵。回國後,方軍寫了他的成名作《我認識的鬼子兵》,引起轟動。在他48歲時被安排自願離開工作崗位,專門從事寫作。真實地記錄這一段歷史,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是方軍的夙願。
 爭分奪秒填補抗戰口述
爭分奪秒填補抗戰口述他執著地追趕訪采寫“最後一批人”。他把自己採訪的 人圈定為 10 種人:老八路新四軍,國民黨抗戰將士,東北聯軍,侵華日軍老兵,被強擄的勞工,被日軍強擄為性奴隸的所謂慰安婦,戰爭細菌戰受害者,愛國華僑,日軍子女、國軍子女,美軍飛虎隊等。 方軍把這10種與抗戰有關的人,稱為親歷抗戰的最後一批人。方軍採訪他們寫成的書,就叫《1931-1945親曆日本侵華戰爭的最後一批人》,現已出到第三冊。 搶救史料:在方軍的寫作中,兩個關鍵字使用頻率很高。其一是“搶救”。他說:當年的戰爭見證人大都垂垂老矣,平均年齡在80歲以上,“今天他同我談話,也許明天就只有照片了,如果我不去採訪記錄,活在他們心中的那段記憶就不復存在了。誇張地說,歷史的一頁就這么翻過去了。”因此,方軍以一種爭分奪秒“搶救”史料的心態進行採訪寫作。面對那么多需要記錄的人,方軍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壓力。他說,我每天都在寫,可還是追不上,很多該去采寫的人因為精力與條件有限不得不放棄了。一次,有人約他去訪29軍敢死隊隊員楊雲峰,就因為花銷問題,他沒有積極回響,不久後楊雲峰就去世後,使他後悔不迭。其二是“口述史”。方軍多次提到:在“博物館學”里有三個名詞:人證、物證、口述史。方軍對“口述史”情有獨鍾,少年時代,有兩部歷史叢書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部是《紅旗飄飄》,一部是《星火燎原》,共有幾十本,數百親歷者親口講述,記錄了中國革命進程中整整一個時代人的命運和思想。抗日戰爭也是一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鴻篇巨製,方軍認為,他寫的兩本書都是抗日戰爭的口述史,“我填補了兩個空白,一是讓中國人了解了老鬼子;二是告訴大家當年的抗戰老兵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
 方軍在台兒莊地區採訪
方軍在台兒莊地區採訪10年中,方軍的足跡遍及全國甚至延伸到國外,一共採訪了300百多人,受訪者的年齡跨度從66歲到105歲,都是當年抗日戰爭的親歷者、倖存者。從《我認識的鬼子兵》到《最後一批人》,到已經殺青的另兩部記述親歷抗日戰爭老人故事的書稿《戰爭最後的證言者》和《戰禍的記憶》,方軍這些年所寫的,全部都是抗日戰爭紀實文學。方家灰白的牆壁上,貼滿了他採訪抗戰人物的照片、通信地址、電話號碼、採訪寫作計畫和一些單頁的書信。地上、桌上和書架上都分門別類地放滿了各種抗戰資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他為所採訪過的300多人建立的檔案。
方軍認為,每個日本人都具有雙重性,他既可能殺人放火,也可能搖動櫻花,關鍵是要限制罪惡的產生。他採訪了很多普通的日本老兵,他們在回顧戰爭狀態下犯罪的經歷,面對我的採訪,他們懺悔,謝罪。所以,每一個普通人只要給他一個狀態,他就可以產生什麼樣的能量。”
策劃抗戰老兵盧溝橋重聚
2007年7月7日,親歷過“七七事變”的國民革命軍29軍9名老兵,在時隔70年之後重登盧溝橋。他們在盧溝橋上,列隊報數,舉手敬禮,緬懷戰友,引起了廣泛關注。
 方軍舉牌者與當年29軍將士
方軍舉牌者與當年29軍將士他發起和策劃抗戰老兵重聚盧溝橋活動。作為一名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退伍軍人,他覺的這是義務。
方軍父親兄弟三人都是冀中軍區的八路軍,呂正操將軍的部下。叔父在與侵華日軍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戰鬥中犧牲了。伯父是八路軍區長,但不幸被漢奸出賣,可他在敵人面前威武不屈。這是他不遺餘力宣傳抗戰老兵的重要動機和原因之一。
他與這些八九十歲的抗戰老兵結下了不解之緣。多年來,他已採訪過數百位親歷過抗日戰爭的人,並為此耗費了無數的財力和精力,但他從未退縮過,後悔過。 他說“就是一生當個最窮的作家,也要把追訪抗戰最後一批人的事堅定不移地做下去!”
用自己住房的租金支撐追訪行程
 在採訪中
在採訪中方軍有很多賺錢的機會,但他都不假思索地放棄了。他一直四處奔波採訪親歷抗日戰爭的老人,根本無暇他顧。一次在昆明採訪中,他得知當年在緬甸,對日作戰中,國民黨軍200師少校軍官張家福把犧牲的戴安瀾將軍一直背回國內,他為這樣的軍人而感動。於是很快辦手續去緬甸採訪,花三個星期重走了200師當年撤退的全程路線。
採訪數百位“最後一批人”,需要大量的經費支持,由此耗盡了方軍幾乎所有的財力。採訪參加台兒莊戰役的敢死隊隊長仵德厚時,他向所在單位申請了3年,一直得不到支持,後來只得自費去採訪。方軍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在北京這個大都市裡,生活拮据可想而知。那方軍採訪的費用從哪裡來呢?他笑了笑說有辦法:他把自己比較寬敞的住房租出去了,然後租住小房。用上海淞滬抗戰館沈建中館長的話說:“方軍的家,那就是家徒四壁。”
方軍的家倒很像抗戰展覽室。一幅銅製的盧溝橋照片,放在屋裡的醒目位置:橋上堆有國民黨29軍抗擊日軍的沙袋,侵華日軍舉著他們的太陽旗趾高氣揚地從橋上通過……方軍幾乎天天看到這個鏡頭。這張由侵華日軍在1937年7月拍攝的照片,天天提醒他該思考什麼,該做什麼。方軍在家裡收集著與抗戰有關的資料,思考著與抗戰有關的問題,記錄著抗戰時期有價值的點點滴滴,仿佛跟窗外喧囂的都市隔著一個世界。他說,每天看到屋裡的這些東西,他便忘了窗外的世界。這些得來不易的“人證、物證、口述史”資料每時每刻都在激勵著他,勇敢地走下去。就是一生當個最窮的作家,也要把追訪抗戰最後一批人的事堅定不移地做下去!
促成“鬼子兵”盧溝橋下跪謝罪
 91歲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向中國人民謝罪
91歲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向中國人民謝罪在日本留學時,方軍一邊讀書,一邊打工。一天,他在一個工廠里打工,一名叫小林勇的老頭問他是哪裡人,方軍回答從北京來的。小林勇說,他l938年在北平,當時他們是占領軍。
這是方軍遇見的第一個侵華日軍。後來,小林勇又給方軍介紹了一些侵華日軍老兵。經歷6年的千辛萬苦和艱難曲折的採訪,方軍先後採訪了20多位原侵華日軍老兵。這些侵華的老兵有的也反思到自己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也懺悔也認罪,有時也有意或無意地向方軍講一些他們過去在中國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1997年12月,《我認識的鬼子兵》出版,成為當年10大暢銷書之一,得了四項國家級大獎,且出了繁體版和日文版,還名列被盜版書的首位。
方軍恨“鬼子”,可侵華日軍老兵還就認方軍。《我認識的鬼子兵》出版後,不少侵華日軍老兵給他寫信,表示懺悔之意。有些侵華日軍老兵來中國謝罪,就住在方軍家裡,方軍還陪同他們去謝罪。這些謝罪行動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在盧溝橋下跪”了。
2005年5月19日,91歲的日本侵華老兵本多立太郎在盧溝橋下跪謝罪。 當時,正是日本個別領導人無視自己的承諾,一而再、再而三地供奉靖國神社,中日關係再一次陷入緊張狀態之際,老兵一跪,意味深長。
而促使本多來中國下跪謝罪的,正是方軍。方軍與本多結識8年,通信200多封。此次本多來北京就住在他家,本來已說好第二天要去盧溝橋下跪了,可是本多的態度有了反覆:“明天我不能下跪謝罪了。我91歲了,無所謂。可我還有子孫呀!我應該為他們考慮。”怎么辦?方軍靈機一動,把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照片放在桌上。看到這張照片後,本多次日在盧溝橋如期下跪謝罪。 2005年5月19日,新華社將91歲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下跪北京盧溝橋的照片傳遍中國。
方軍還與6個侵華日軍老兵保持通信聯繫,十多年收存的侵華日軍老兵的來信就有300多封。這些信大多是以謝罪、反思為主的。
![方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方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img/b/2c2/nBnauM3X0YTN1UjM5cDMyM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AzL1E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