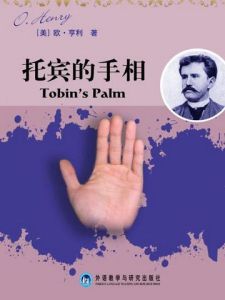內容概要
托賓因為女友凱蒂·馬霍納的失蹤心灰意冷。與朋友在尼羅河邊散步時,托賓遇到埃及手相師,手相師預言一個深色皮膚的男人和一個淺色皮膚的女人會給托賓帶來麻煩,而一個長著歪鼻子、名字中有“O”這個字母的男人則能給他帶來好運。在回去的船上,托賓果然先後遇到一個黑鬼和一個金髮碧眼的白皮膚女子,他僅有的一美元六十五分被偷,帽子也掉進了水裡,手相師的預言似乎一一應驗。最後托賓找到一個歪鼻子的男人,這人名字中沒有“O”,但是托賓相信此人就是會給他帶來好運的人。就在托賓逐漸對這位所謂的幸運星失望時,對方卻在無意中透露家裡新女傭的名字,正是托賓的女友凱蒂·馬霍納。
譯文
有一天,我和托賓倆往科尼去,一來是我們有四元錢可花,二來是托賓正心煩,要消消遣。原來,他的女朋友卡蒂·馬霍納三個月前從北愛爾蘭的斯萊戈郡到美國來,誰知卻失蹤了。她身上帶著自己的兩百元積蓄,還有托賓賣掉在博格尚諾繼承的一所漂亮小房子和豬所得一百元。托賓接到過一封信,說她已經動身上他這兒來,可是從那以後就杳無音訊,更沒見過卡蒂·馬霍納。托賓在報上登了廣告,但就是沒找到這姑娘 。
這樣我和托賓便同去科尼,以為換換環境,吃吃香噴噴的玉米花,他的情緒會好起來。誰知托賓是個死腦瓜子,橫豎開不了竅。聽到人叫賣氣球,他咬牙切齒;看到電影,他便開口罵; 邀他喝一盅他還會幹,但他見了檸檬水會嗤之以鼻;;見到給人拍照的來了他就想動手揍人。
於是,我帶他走鋪木板的小道①少惹事生非。走到一個六八見方的小棚子邊,托賓站住了,眼神恢復了正常。
他說: “只有這地方稱我心。尼羅河來的相命師本領大②,我請他們看看手相,看命里注定究竟會如何。”
托賓相信預兆,還有稀奇古怪的東西,什麼黑貓③啦,預測吉凶的數字啦,還有報紙上登的天氣預報④啦,他都莫名其妙地當真。
我們走進相命師雞籠似的小棚子裡,只見裡面掛著紅布,還有像鐵路樞紐般線路縱橫交錯的掌紋圖,很有令人莫測高深之感。門上的招牌寫著: 埃及女手相大師佐佐。裡面坐著個胖女人,身穿紅短褂,短褂上繡著歪歪斜斜的字和小動物。托賓給她一角錢,攤開了手掌。他那手跟拉車運貨的馬的蹄子差不多。女手相大師抓起來細看著,想瞧瞧托賓登門是不是為一顆寶石讓青蛙吞到肚裡了,或者是掉了鞋樣。
這位佐佐大師說道: “老弟,從你的手相來看呢——”
托賓打斷了她的話: “你看的不是我的腳。漂亮固然算不上,手總還是手。”
女大師說: “從手相看你從小到大不是一帆風順。往後還有災。這根婚姻線——喲,是石頭碰傷了還是怎么的? 線上顯得是動了姻緣。為了女朋友你已經遭到了挫折。”
“她這是在說卡蒂·馬霍納。”托賓把頭偏過來對我一個人說,但聲音不輕。
手相師又說: “有個人你總忘不了,又傷心,又著急。從紋路上看,是個女的,名字里有個字母是K,還有個是M⑤。”
“喲喲! 聽見了嗎?”托賓對我說。
手相師往下又道: “遇見一個黑皮膚的男人和一個輕浮相的女人你得小心,這兩個人會叫你遭災。不出多少日子你會行水路,要破財。有一條掌紋使你時來運轉。你要遇上一個人,他會帶你交好運。這人長著個彎鼻子,你見了能認出來。”
“他的名字手相上看得出嗎? 遇上了他帶我交好運,知道名字好讓我跟他打招呼。”托賓問道。
手相師若有所思說: “手相上看不出名字怎么拼,但是看得出名字很長,當中必有字母O。相看完了。再見。別把門堵住了。”
“這女的真神!”托賓邊上碼頭邊說。
擠過碼頭的門時,一個黑人手裡的雪茄菸燙了托賓的耳朵,鬧出了亂子。托賓在他脖子上使勁來了一拳,在場的女人一個個尖叫起來。我見勢不妙,沒等警察趕到,便把托賓一把拉開。這傢伙興起的時候有得好瞧!
坐上往回開的船以後,托賓聽到有人叫賣名牌啤酒。這時他知道了剛才的錯,很想喝杯啤酒,可是伸手往口袋裡一摸,發覺口袋空了。剛才有人在混亂中掏走了他的零錢。我們只好不喝,坐到長凳上,聽甲板上的南歐人彈琴。要說這一趟出遊有什麼收穫,那就是托賓又遇上了倒霉事,比原來更喪氣,更無精打采。
船上有個年輕女人靠在欄桿上坐著,憑一身穿著的費用夠得上坐高檔紅汽車,頭髮的顏色像沒抽過煙的海泡石菸斗。托賓從她身邊過時無意中踢到了她的腳。平常他喝了酒對女人也是彬彬有禮,這一次更是,想抓起帽子表示道歉。可是他倒把帽子碰掉了,又遇上風,帽子吹落到水裡。
托賓走回來後坐下了。我留心看著他,他老兄遇上的倒霉事已經太多。如果讓倒霉事慪急了,見到穿漂亮衣服的人他真會抬腿踢,還會搶過船來開。
托賓坐了一會兒,突然抓住我的一隻手,興奮地說: “約翰,你看我們現在怎么啦? 我們不是在走水路嗎?”
“走水路也別興奮,船再過十分鐘就靠岸了。”我說。
“你瞧,瞧那坐在凳上的輕浮相女人。還有那燙了我的耳朵的黑人,你沒忘吧? 我不是丟了錢嗎? 有一元六角五分呢!”
我以為他只是在數他遭的難,像許多人那樣,發作起來有個藉口,便好言勸道,別把這些事看得太認真。
“得啦,”托賓說,“預言家就是有天才,通了神的人說話就是靈,你長著耳朵還聽不進。那手相師看了我的巴掌說什麼你忘啦? 眼見著都應驗了。她說‘遇見一個黑皮膚的男人和一個輕浮相的女人你得當心,這兩個人會叫你遭災。’你就忘了那黑人? 雖說我也揍了一拳,讓他遭了報應。我帽子吹到水裡去要怪那黃頭髮的女人,你說說看,這種女人不輕浮誰輕浮? 出了射擊場以後放在我衣服里的一元六角五分錢又是到哪兒去了?”
托賓說得頭頭是道,似乎當真有人能未卜先知,但我認為,這些事無論誰到科尼都可能遇上,不能說是手相師靈驗。
托賓起身滿甲板地走,用發紅的小眼睛細細打量船上的乘客。我問他這是為什麼。托賓心裡想的事你不知道,除非他幹了出來。
他說: “告訴你吧,從我手相上看,我能遇上救星,我這就在找。我要找著那個能使我時來運轉的彎鼻子人。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救。你這輩子哪兒見過該下地獄的人長著直鼻子的,約翰?”
船九點三十分靠岸,我們下了船,從二十二大街進城,托賓沒戴帽子。
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我看到一個人站在氣燈下路面高的地方望著月亮。他個子高,衣著講究,嘴裡叼著一根雪茄。我還發現他的鼻子從鼻樑往下拐了兩個彎,就像蛇爬行時身體擺動著一樣。托賓這時也看見了。我聽見他呼吸聲很響,如同一匹剛卸鞍的馬,直噴鼻息。他直向那人走去。我也跟著他走。
“你好!”托賓對那人說。那人善交際,拿出根雪茄,也還禮問好。
托賓說: “請問你尊姓大名,讓我們看看是長是短。也許我們有必要跟你結識結識。”
那人很有禮貌地說: “我名叫弗里登豪斯曼,就是馬克西默斯·格·弗里登豪斯曼。”
“長短倒對上了,”托賓說,“這么長的名字拼起來是不是用得著一個字母O呢?”
“那沒有。”那人說。 “你就寫進一個O不行嗎?”托賓問道,心急了。
“如果你從心底里不喜歡外國拼法,那么悉聽尊便,在倒數第二個音節加上一個O未嘗不可。”長彎鼻子的人說。
“這就行啦。”托賓說,“我們倆一個叫約翰·默倫,一個叫丹尼爾·托賓。”
“幸會,幸會!”那人說著一鞠躬,“想來兩位不會在十字路口舉行拼寫比賽,那么請問,剛才說這么多話究竟有何貴幹呢?”
“就為你有兩個特點與埃及手相師替我看相時講的一模一樣。”托賓答道,開始講他的緣由,“我遇上個黑人,倒了霉,坐船又碰到了個黃頭髮女人蹺起腳,又沒好事,還破了一元六角五分的財,都應了手相師的話。她說只有你能消災,讓我時來運轉。”
那人不再吸菸,看著我,問道: “你看他說的是不是這么回事? 你們倆該不一樣吧? 我看你的模樣像是在照看他。”
“是這回事。”我對他說,“而且我朋友的手相上注定要遇上你這么個人,你跟手相師說的沒兩樣,就像左馬蹄跟右馬蹄沒兩樣。要是有兩樣,丹尼爾的手相上也許還是看得出來,那誰能說?”
“你們倆是一起的。很高興見到了兩位。”長彎鼻子的人說著往街兩頭望,盼望有警察來,“再見吧!”
說完他把煙塞進嘴裡,橫過馬路快步便走。但托賓緊跟到了他身邊,我也跟到了他另一邊。
“乾什麼?”他馬上在人行道上站定了,把帽子往後一推,“你們還要跟著我?”他提高嗓門,嚷道,“告訴你們吧,見到兩位十分榮幸,可是我不想再跟兩位打交道。我現在要回家。”
“那行,回家就回家吧。”托賓說,靠到了他衣袖上,“我就在你們家門口等,到明天早上你總還得出來。我遇上了黑人跟那黃頭髮女人,又破了一元六角五分的財,倒了霉,除霉氣非你不行。”
“這真是莫名其妙!”那人轉身對我說,他認為我是兩個瘋子中神志清醒些的,“請你帶他回家好嗎?”
我對他道: “先生,你不知道,丹尼爾·托賓現在精神正常,平常也正常。是這么回事: 大概他多喝了兩盅,興奮了,又理不清思路,便有一點點糊塗。他就想脫掉手相師說的倒霉氣,也沒做出什麼越軌違法的事來。我這就向你詳細說說。”接著我把手相師怎么怎么相命,他的特徵與從手相上看出的救星怎么怎么相合,都告訴了他。最後我說,“現在你總該明白我在這齣戲裡唱的什麼角了吧。我已經說得清楚,我是托賓的朋友。當有錢人的朋友容易,有便宜占。做窮人的朋友也不難,他們會對你千恩萬謝,還可以在報上登個照片,讓人看到你一手提著一箱煤,一手抱著個孤兒站在一家人家門前。但是當天生傻瓜的真朋友就難,要有幾手當朋友的本領。我現在當的就是這種朋友。我知道我伸出手看手相看不出好命,條條紋路注定了要乾為難的事。沒錯,全紐約就數你的鼻子最彎,我還是不相信算命的人就那么靈,能看出你可以讓人時來運轉。不過呢,你的特點與丹尼爾手相上看出的一點沒差,所以我想幫他試試看,除非是他知道了你真辦不到。”
那人聽完以後便馬上笑起來,靠在牆角上放聲打哈哈。笑過以後手往我和托賓背上一拍,接著又抓住我們的手臂,一邊一個。
他說: “誤會,誤會! 我哪能料到會遇到這種湊巧事? 差一點就對不起兩位了。離這兒沒幾步有家咖啡館,裡面舒服得很,去聊聊各人的個性最合適。我們就喝上一杯,邊喝邊談有沒有絕對的可能或不可能的問題。”
說著,他領我和托賓進了一家咖啡館的後廳,要了幾杯,把錢放在桌上。他看著我和托賓時的神態,仿佛他是我們的兄長。他還請我們抽菸。
“兩位還不知道,”命中注定相逢的人說,“我乾的那一行就是所謂‘動筆桿子’。今天晚上我出門尋找人的個性和上天遵循的永恆。你們見到我時,我正在思考明媚的月亮與路的關係。明月照馬路的暫時現象很有詩意,很美,雖然月亮只是一個萬古不變、沒有情感、不停運動的物體。當然,各人的看法不會相同,在文人眼裡,條件是顛倒過來的。我很想寫一本書,解釋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千奇百怪的事。”
“那你可以把我寫進去,”托賓迫不及待地問,“你會把我寫進書里嗎?”
“我不會,”那人答道,“因為你上不了封面。現在還不行。至多我只能個人喜歡你,摧毀出版界限制的時間還不成熟。你的事見諸文字會絕妙。這份高興只好歸我一人獨享。但是兩位,我謝謝你們,我真心感謝你們。”
“你越講越叫我憋不住了!”托賓開口了,在桌上當地一拳,還吹鬍子瞪眼睛,“你長著個彎鼻子,本來彎鼻子會讓我時來運轉,可是你給人的好處像大鼓響,聽得見摸不著。你口口聲聲書呀書,有什麼用? 只是吹過縫的風,會嗚嗚叫。這樣看來,看手相不頂用,靈驗了的只有那黑人,黃頭髮女人,還有——”
那高個子打斷了他: “別瞎鬧! 你別讓相命那玩意兒迷了心竅。我的鼻子只能幹它分內的事。來,把杯子倒滿,談人的個性得邊喝邊談,一本正經只談不喝,人的個性談不起勁。”
我覺得這動筆桿子的人沒有白相逢。我和托賓讓人算準,已身無分文,但這個人高高興興,把三人的賬全付了。托賓卻只悶聲喝著,很不痛快,眼都發紅。
最後我們出了咖啡店,在人行道上站了站,這時已是夜晚十一點。那人說他得回家,邀我和托賓送他一程。過了兩個路口後,我們到了一條小街,這裡有一片磚房,屋前有高坪台和鐵護欄。那人走到一所磚房前停住了腳,抬頭一望頂層視窗已沒有了燈光。
“這就是寒舍,”他說道,“看樣子我太太已經就寢。恕我冒昧,兩位不嫌棄就請進。想請兩位就座地下室,我們吃上一頓,也好提提神。有美味冷雞,乾酪,還有一兩瓶酒。歡迎兩位來進餐,你們陪我一程,十分感謝。”
我和托賓已經餓了,同時也覺得吃一頓並不能算昧良心的事,便都沒推辭。托賓不過還是迷信他那一套,認為喝上幾盅,吃上一頓冷餐,也應驗了手相上注定的交好運。
“請下階梯,”長著彎鼻子的人說,“我先從上邊門進,再領兩位。廚房裡新請了位姑娘,我去叫她燒壺咖啡,讓兩位喝了再走。卡蒂·馬霍納是才來三個月的新手,咖啡燒得倒挺好吃。請進吧,我去叫她伺候兩位。”
注釋
①美國有鋪木板的散步小道,多在海邊。
②尼羅河被視為埃及的象徵,而埃及當時出名相命師。
③美國作家艾倫·坡寫過一篇題為《黑貓》的小說,小說中的黑貓受主人虐待而死,後顯身報復,使主人遭大火家破人亡。
④當時天氣預報準確率低,可能由於這個原因,作者將天氣預報與迷信活動相提並論。
⑤卡蒂·馬霍納的英文拼寫為Katie Mah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