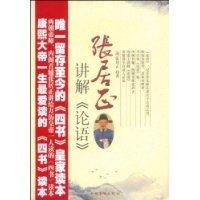相關參數:
作者:(明)張居正
出版社:中國華僑出版社
ISBN:9787802228092
內容簡介
《張居正講解〈論語〉》主要講了《張居正講解四書》(原名《四書直解》)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張居正連同翰林院講官等人專門寫給當時的小萬曆皇帝朱翊鈞(明神宗)一人讀的。該書曾在明朝年間得到刻印,根據記載,“1651年張居正所注《四書》再次付梓,題《張閣老直解》。吳偉業在為這部書所作的序中談到張居正給孩提時的萬曆皇帝當老師時,充滿羨慕之情。”(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明崇禎四年進士,官左庶子。弘光朝,任少詹事。人清順治時,官國子監祭酒,以母喪告假歸里。)
康熙年間,內閣學士徐乾學(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崑山(今屬江蘇)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又將此書翻刻。該刻本至今在民間依舊有流傳,可見該書當時影響之大。徐乾學評道:“蓋朱注以翼四書,直解有所以翼注。”
康熙帝在讀此書後如此說道:“朕閱張居正尚書四書直解,義俱精實,無泛設之詞,可為法也。”
作者簡介
張居正,漢族,字叔大,少名白圭,號太岳,諡號“文忠”,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內閣首輔,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張居正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廣巡撫顧轔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練幾年,才未中舉。16歲中了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歲中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時與高拱並為宰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曆初年,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當時明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前後主政10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萬曆十年(1582年)卒,贈上柱國,諡文忠。死後不久即被宦官張誠及守舊官僚所攻訐,抄其家;至天啟時方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岳集》、《書經直解》等。
目錄
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日第二十
序言
《張居正講解四書》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張居正連同翰林院講官等人專門寫給當時的小萬曆皇帝朱翊鈞(明神宗)一人讀的。
該書曾在明朝年間得到刻印,根據記載,“1651年張居正所注《四書》再次付梓,題《張閣老直解》。吳偉業在為這部書所做的序中談到張居正給孩提時的萬曆皇帝當老師時,充滿羨慕之情”。(註:倫德貝克:《首輔張居正和中國早期的耶穌會士》,第5頁;戴維·E·芒傑羅:《耶穌會士翻譯<四書>》,第14頁。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明崇禎四年進士,官左庶子。弘光朝,任少詹事。人清順治時,官國子監祭酒,以母喪告假歸里。)
康熙年間,內閣學士徐乾學(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崑山(今屬江蘇)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又將此書翻刻。該刻本至今在民間依舊有流傳,可見該書當時影響之大。
康熙帝在讀此書後如此說道:“朕閱張居正尚書四書直解,義俱精實,無泛設之詞,可為法也。”
張居正,漢族,字叔大,少名白圭,號太岳,諡號“文忠”,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明代最優秀的首輔,最好的政治家。
嘉靖四年(]525年),當張居正在荊州江陵(今屬湖北)的一位秀才家裡呱呱墜地的時候,其先祖的餘蔭對他早已不能關懷庇護,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文摘
學而第一
【原文】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譯文】孔子說:學習修養自己和福國利民的學問,又能夠適時地實行,豈不是很令人欣喜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從遠方來,豈不是很快樂嗎?當自己的道德學問有成就時,即使旁人不知道,心裡也沒有絲毫怨恨,這不正是一個君子的,風範嗎?
【張居正講解】學,是仿效。凡致知力行,皆仿效聖賢之所為,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是溫習。說,是喜悅。孔子說道:“人之為學,常苦其難而不悅者,以其學之不熟,而未見意趣也。若既學矣,又能時時溫習而不間斷其功,則所學者熟,義殫浹洽,中心喜好,而其進自不能已矣,所以說不亦說乎!”
朋,是朋友。樂,是歡樂。夫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將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夫然則吾德不孤,斯道有傳,得英才而教育之,自然情意宣暢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說不亦樂乎!
慍,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的人。夫以善及人,固為可樂,苟以人或不見知,而遂有不樂焉,則猶有近名之累,其德未完,未足以為君子也。是以雖名譽不著而人不知我,亦惟處之泰然,略無一毫含怒之意。如此則其心純乎為己,而不求人知,其學誠在於內,而不願乎外,識趣廣大,志向高明,蓋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說不亦君子乎!夫學,由說以進于樂,而至於能為君子,則希賢希聖,學之能事畢矣!
【原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仁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譯文】有子說:“孝順父母,順從兄長,而喜好觸犯上級,這樣的人是很少見的。不喜好觸犯上級,而喜好悖逆亂世的人是沒有的。君子專心致力於根本的事務,根本建立了,治國做人的原則也就有了。孝順父母、順從兄長,這就是做人的根本啊!”
【張居正講解】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叫作孝;善事兄長,叫作弟。犯,是乾犯。鮮,是少。作亂,是悖逆爭斗的事。有子說:“天下的人莫不有父母兄長,則莫不有孝弟的良心。人惟不能孝弟,則其心不和不順,小而犯上,大而作亂,無所不至矣。若使他平昔為人,於父母則能孝,盡得為子的道理,於兄長則能弟,盡得卑幼的道理,則心裡常是和順,而所為自然循禮,若說他敢去乾犯那在上的人,這樣事斷然少矣。”夫犯上,是不順之小者,且不肯為,卻乃好為悖逆爭鬥大不順的事,天下豈有是理哉!夫人能孝弟而自不為非如此,可以見孝弟之當務矣。
務,是專力。本,是根本。為仁,是行仁。有子又說:“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若徒務其末,則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所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切要處專用其力。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處之各當,道理自然發生,譬如樹木一般。”根本牢固,則枝葉未有不茂盛者。本之當務如此。則吾所謂孝弟也者,乃是行仁之本與。蓋仁具於心,只是側怛慈愛的道理,施之愛親敬長,固是此心推之仁民愛物,亦是此心,人能孝弟,則親吾之親,可以及人之親,長吾之長,可以及人之長,至於撫安萬民,養育萬物,都從此充拓出來,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則行仁之本,豈有外於孝弟乎!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孝經》孔子說:“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有若之言,其有得於孔子之訓歟?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鮮仁矣。”
【譯文】孔子說:“花言巧語,裝出和顏悅色的樣子,這種人的仁德就很少了。”
【張居正講解】巧,是好。令,是善。鮮字,解作少字。仁,是心之德。孔子說:“辭氣容色,皆心之符,最可以觀人。那有德的人,辭色自無不正。若乃善為甘美之辭,遷就是非,便佞阿諛,而使聽之者喜,這便是巧言。務為卑諂之色,柔順側媚,迎合人意,而使見之者悅,這便是令色。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蓋仁乃本心之德,心存,則仁孝也。今徒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心馳於外,而天理之斫喪者多矣,豈不鮮仁矣乎!然孔子所謂鮮仁,特言其喪德於己耳。若究其害,則又足以喪人之德。蓋人之常情,莫不喜於順己,彼巧言令色之人,最能逢迎取悅,阿徇取容,人之聽其言,見其貌者,未有不喜而近之者也。既喜之而不覺其奸,由是變亂是非,中傷善類,以至覆人之邦家者,往往有之矣!夫以堯舜至聖,尚畏夫巧言令色之孔壬。況其他乎!用人者不可不察也。
【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譯文】曾子說:“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為別人辦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誠實可信了呢?老師傳授給我的學業是不是勤於實習,內化於心了呢?”
【張居正講解】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參。省,是省察。忠,是盡心的意思。信,是誠實。傳,是傳授。習,是習熟。曾子說:“我於一日之間,常以三件事省察己身。三者維何?凡人自己謀事,未有不盡其心者,至於為他人謀,便苟且粗略,而不肯盡心,是不忠也。我嘗自省,為人謀事,或亦有不盡其心者乎?交友之道,貴於信,若徒面交,而不以實心相與,是不信也。我嘗自省,與朋友交,或亦有虛情假意,而不信於人者乎?受業於師,便當習熟於己,若徒面聽,而不肯著實學習,是負師之教也。我嘗自省,受之於師者,或亦有因循怠惰,而不加學習者乎?以此三者,自省察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蓋未嘗敢以一日而少懈也。”蓋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其用功之密如此。然古之帝王,若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成湯之日新又新,檢身不及,亦此心也,此學也。故《大學》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從事於聖學者,可不知所務哉!
【原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譯文】孔子說:“治理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就要嚴謹認真地辦理國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誠實無欺,節約財政開支而又愛護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誤農時。”
【張居正講解】道,是治。乘,是兵車。四馬駕一車,叫作一乘。千乘之國,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的大國。時,是農功問暇之時。孔子說:“千乘的人國,事務繁難,人民眾多,不易治也。”若欲治之,其要道有五件,其一要敬事。蓋人君日有萬幾,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一時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須兢兢業業,事無大小,皆極其敬慎,不敢有怠忽之心,則所處皆當,而自無有於敗事矣。其一要信。蓋信者,人君之大寶,若賞罰不信,則人不服從,號令不信,則人難遵守。必須誠實不貳,凡一言一動都要內外相孚,始終一致,而足以取信於人,則人皆用情,而自不至於欺罔矣。其一要節用。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用若不節,豈能常盈。必須量人為出,加意撙節。凡奢侈的用度,冗濫的廩祿,不急的興作,無名的賞賜都裁省了。只是用其所當用,則財常有餘,而不至於匱乏矣。其一要愛人。蓋君者,民之父母,不能愛人,何以使眾。必須視之如傷,保之如子,凡鰥寡孤獨、窮苦無依的,水旱災傷、饑寒失所的,都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則人心愛戴,而仰上如父母矣。其一要使民以時。蓋國家有造作建設,興師動眾的事,固不免於使民,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妨民之業,而竭民之力矣。必待那農事已畢之後,才役使他,不誤他的耕種,不礙他的收成,則務本之民,皆得以盡力于田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這五者都是治國的要道,若能體而行之,則四海之廣,兆民之眾,治之無難,豈特千乘之國而已哉!為人君者,所當深念也。
【原文】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譯文】孔子說:“弟子們在家要孝順父母;出門在外,要尊敬長輩,要謹言慎行,恪守誠信,要博愛民眾,親近那些有仁德的人。這樣躬行實踐之後,還有餘力的話,就再去學習六藝。”
【張居正講解】弟子,是指凡為弟為子的說。謹,是行的有常。信,是言的有實。泛字,解作廣字。眾,是眾人。親,是親近。仁,是仁厚有德的人。餘力,是余剩的工夫。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孔子教人說:“但凡為人弟為人子的,入在家庭之內,要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要善事兄長以盡其弟。凡行一件事,必慎始慎終,而行之有常。凡說一句話,必由中達外,而發之信實。於那尋常的眾人都一體愛之,不要有憎嫌忌刻之心。於那有德的仁人卻更加親厚,務資其薰陶切磋之益。這六件,是身心切要的工夫。學者須要著實用力,而不可少有一時之懈。若六事之外,尚有餘力,則學夫《詩》、《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為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未有餘力,固不暇為此,既有餘工,則又不可不博求廣覽,以為修德之助也。先德行而後文藝,弟子之職,當如此矣。然孔子此言,雖泛為弟子者說,要之上下皆通。古之帝王,自為世子時,而問安視膳,入學讓齒,以至前後左右,莫非正人,禮樂詩書,皆有正業,亦不過孝弟、謹信、愛眾、親仁與夫學文之事也。至其習與性成,而元良之德具,萬邦之貞,由此出矣。孔子之言,豈非萬世之明訓哉!
【原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日未學,吾必謂之學也。”
【譯文】子夏說:“一個人,能以敬重賢人之心,來替代愛好美色的心,侍奉父母能盡心盡力,服事君主時貢獻心智不余其力,和朋友交往,能做到誠信不欺,這樣的人,縱使他謙虛地說沒有讀過書,我也必定認為他很有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