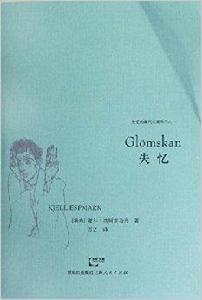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失憶的年代:失憶》編輯推薦:知識分子小說,意識流的精彩演繹。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會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失憶的年代》7卷本第一卷。2012年10月中譯本首次面市中國。莫言、蘇童、余華、閻連科、遲子建、陳思和等眾多中名家力推作品。連任17屆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會主席的學院派作家的十年力作,卡夫卡式手法,加繆般洞見。
作者簡介
作者:(瑞典)謝爾·埃斯普馬克 譯者:萬之
謝爾·埃斯普馬克,1930年生,瑞典詩人、小說家、文學史家,是瑞典學院院士、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會主席17年。他關注人類共同的命運,以及文字或詩歌的力量。他的詩歌富含生命力,又充滿張力。出版有十一本詩集,曾獲得包括“薛克文學批評獎”和“貝爾曼詩獎”,最近獲得的是“凱格倫獎”以及“九人團大獎”。
後記
譯者後記
多年前瑞典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先生就向我推薦過埃斯普馬克的這部長篇系列著作《失憶的年代》,認為值得翻譯,介紹給中文讀者,但我遲至今年才有時間完成第一部《失憶》。
翻譯一部文學作品的過程,和一般閱讀過程不同,需要字斟句酌,自然也是對作品加深理解的過程,更是文學欣賞的過程,能給人帶來更多的閱讀之悅閱讀之趣,讓人獲得更多教益。翻譯這部作品的過程中,我正是這樣體驗越來越多的悅趣,也引發很多深入的思考。
悅趣之一是欣賞小說的敘述方式。對我來說,形式的意識是區別小說家優劣的關鍵。小說不僅在於你寫什麼,也在於你用什麼方式來寫,後者甚至更重要。有的小說家只關心內容的精彩離奇,而敘說俗套,根本沒有形式感,而《失憶》是一部非常講究敘述方式的小說,正好也是我欣賞的方式。這裡有些個人愛好的原因。我自己本來學習過戲劇,也寫過小說,早年我就欣賞馬原的敘述方式,因此為他的《岡底斯的誘惑》寫過序。後來我自己曾經嘗試過一種如戲劇式對話體小說形式(比如我的小說《穿風衣的女人》和《歸路迢迢》的敘述方式)。這種形式像是兩個人物在台上的對話,而因為看法視角不同,可能把一個故事講述成各自不同的故事。《失憶》其實也是一種對話方式,只不過是一方始終沒有說什麼,而是主角一人喋喋不休,幾乎像是自言自語,只是偶爾停頓喘口氣而已。小說的章節由這種停頓構成,所以分章節時不編號不用標題也有其道理,因為這是一種綿綿不絕的語言流,類似現代小說中的意識流。我在讀高行健小說《靈山》中也感受到這種獨白式的語言流的悅趣。不知道是否因為這種語言流的共鳴,惺惺相惜,使得作者把諾貝爾文學獎的繡球拋給了高行健。
我在對話體小說是用兩個人的敘述來探索敘述的不同可能性,穿同一件風衣的女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故事。有人把這列小說稱為“元小說”說“後設小說”(英語是metafiction)。而在《失憶》中,因為對於同一張照片,同一本護照,同一根鐵管,主角在自言自語的分析追索中也能講出不同故事,使得敘述有往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而這正好符合一個失憶者的真實心理狀態,可謂心理現實小說和元小說兩者兼得。
悅趣之二自然還是小說處理的“失憶”這個主題。正如作者序言中說,雖然“失憶”現象在當代社會越來越普遍,但用這個主題來創作系列長篇小說還是首次。翻譯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我常常聯想到卡夫卡的小說《審判》和加繆的《局外人》。《失憶》中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審理過程”或“調查過程”其實就是卡夫卡《審判》書名一樣的詞processen。而《失憶》主角的心理狀態,那種自己都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的荒謬,我覺得《局外人》的主角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代社會的“異化”現象alienation在中國八十年代也是很熱門的話題,但在社會全面異化中已經不是話題了,這正是小說所描述的“失憶”現象之一。我們都得了不可救藥的健忘症。
悅趣之三是我很久沒讀到這類文人氣很濃的小說了,讀來欣喜。《失憶》在我看來無疑是一部學院派作家的、知識分子作家的小說。它真正用的上我最近從國內朋友那裡學到的一個新中文詞“高端”。不過中國的“高端”可能和這部小說的“高端”意義不同。如果這部小說在中國銷路不好,我也不會驚奇。因為這不是中國文學近七十年來推行的所謂“下里巴人”的大眾文學,儘管它實際有涉及到了更普遍更有深度的社會問題,它一點不缺少對社會的關注。這是一部我們的中文文學久違了的“陽春白雪”的作品,就和卡夫卡的《審批》或加繆的《局外人》一樣,這樣的高度,還很少有中文作家企及。所以,我覺得最後才真正明白了馬悅然先生向我推薦這部作品的良苦用心,而懂得了翻譯這部作品的意義。
也因為體會到翻譯這部作品的重要性,我翻譯時也有些戰戰兢兢,不僅生怕翻譯錯誤,也擔心小說的語言流風格不能流暢體現。這是一個人的自言自語,很口語化,但又不是日常生活和平民百姓的口語。據作者說,這部小說其實還有自傳性,所以敘述者其實有深厚的學養,是一個院士的敘說口吻,有一個學院派作者的語言風格。是否能夠在譯文中完美再現這種語言流,我真沒有把握。離國日久,平時使用瑞典文多了,對瑞典文的理解是進步了,而中文卻不進則退,雖然我一直堅持寫中文用中文。
慶幸我有貴人相助。《失憶》全部譯稿都經過馬悅然先生仔細校閱訂正,至少翻譯錯誤差不多都得到糾正,在此特别致謝。沒有他的推薦指點,就不可能有現在這部譯作。當過文學編輯的陳文芬女士也看過譯稿,提出很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此外也感謝我的妻子陳安娜一如既往地為我解決瑞典文方面的疑難。當然,這部小說語言風格獨特,難度很大,不妥之處難免,還希行家讀後指正。
感謝上海世紀文睿出版公司總編輯邵敏先生促成此書的翻譯出版,並親自編輯。
譯者於2012年9月18日
序言
中文版序
埃斯普馬克
這個小說系列包括七部比較短的長篇小說,形成貫穿現代社會的一個橫截面。小說是從一個瑞典人的視角去觀察的,但所呈現的圖像在全世界都應該是有效的。人們應該記得,傑出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最近還把我們的時代稱為“遺忘的時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達過相同的看法,從米蘭·昆德拉一直到戈爾·維達爾:昆德拉揭示過占領捷克的前蘇聯當權者是如何抹殺他的祖國的歷史,而維達爾把自己的祖國美國叫做“健忘症合眾國”。但是,把這個重要現象當作一個系列長篇小說的主線,這大概還是第一次。
在《失憶的時代》里,作家轉動著透鏡聚焦,向我們展示這種情境,用的是諷刺漫畫式的尖銳筆法——記憶在這裡只有四個小時的長度。這意味著,昨天你在哪裡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腦外科醫生,昨天也許是汽車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經沒有人記得前一個夜晚是和誰在一起度過的。當你按一個門鈴的時候,你會有疑問:開門的這個女人,會不會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後面的孩子,會不會是我的孩子?這個系列幾乎所有長篇小說里,都貫穿著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親人或情人的苦惱。
失憶是很適合政治權力的一種狀態——也是指和經濟活動糾纏在一起的那種權力——可謂如魚得水。因為有了失憶,就沒有什麼昨天的法律和承諾還能限制今天的權力活動的空間。你再也不用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輿論的風暴四個小時,你就得救了。
這個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單獨成篇,也是對這個社會語境的七個不同的切入視角。第一個見證人——《失憶》中的主角——是一個負責教育的官僚,至少對這方面的災難好像負有部分責任。第二個見證人是一個喜歡收買人心的報刊主編,好像對於文化方面的狀況負有部分責任(《誤解》)。第三個見證人是一位母親,為了兩個兒子犧牲了一切;兒子們則要在社會中出人頭地,還給母親一個公道(《蔑視》);第四位見證人是一個建築工人,也是工人運動的化身,而他現在開始自我檢討,評價自己的運動正確與否(《忠誠》)。下一個聲音則是一位被謀殺的首相,為我們提供了他本人作為政治家的生存狀況的版本(《仇恨》)。隨後的兩個見證人,一個是年輕的金融巨頭,對自己不負責任的經濟活動做出描述(《復仇》),另一個則是備受打擊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婦女,為我們提供她在社會之外的生活狀況的感受(《歡樂》)。
這個系列每部小說都是一幅個人肖像的細密刻畫——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會環境:好像一部社會史詩,濃縮在一個單獨的、用尖銳筆觸刻畫的人物身上。這是那些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如巴爾扎克曾經一度想實現的目標。但這個系列寫作計畫沒有這樣去複製社會現實的雄心,而只是想給社會做一次X光透視,展示一張現代人內心生活的圖片——她展示人的焦慮不安、人的熱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這些都能在我們眼前成為具體而感性的形象。其結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劇。
這七個人物,每一個都會向你發起攻擊,不僅試圖說服你,也許還想欺騙你,就像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那些人物。但是,這些小說里真正的主人公,穿過這個明顯帶有地獄色彩的社會的漫遊者——其實還是你。
2012年9月
名人推薦
小說《失憶》評論
——在埃斯普馬克《失憶》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
余華
今年六月在北京的時候,我的老朋友萬之說他把瑞典文學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翻譯成了中文,同時邀請我參加今天的會議。然後,我讀到了《失憶》。
這是一部細緻入微的書,裡面的優美讓我想起了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裡面的不安讓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釋夢》,裡面時時出現的幽默讓我想起了微笑。一個失憶者在滔滔不絕的講述里(也是自言自語)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裡的痕跡:不可知的檔案箱,一個新鮮的傷口,幾個日期,一封信,一個地址,一份發言稿,舊日曆等等生活的碎片,它們之間缺少值得信任的聯結,而且這些碎片是否真實也是可疑的,但是這些碎片比失憶者更了解他自己,作者在寫到一堆鑰匙時說:“其中一把鑰匙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底細。”
我的閱讀過程十分奇妙,就像我離家時鎖上了門,可是在路上突然詢問自己鎖門了沒有?門沒有鎖上的念頭就會逐漸控制我的思維,我會無休止地在門是否鎖上的思維里掙扎。或者說我在記憶深處尋找某個名字或者某一件往事,當我覺得自己已經接近了的時候,有人在旁邊說出了一個錯誤的名字或者錯誤的事件時,我一下子又遠離了。
我似乎讀到了真相,接著又讀到了懷疑;我似乎讀到了肯定,接著又讀到了否定。這樣的感覺像是在讀中國的歷史:建立一個朝代,推翻一個朝代,再建立一個,再推翻一個,周而復始。
因此我要告訴大家,這不是一部用銀行點鈔機的方式可以閱讀的書,而是一部應該用警察在作案現場採取指紋的方式來閱讀的書。或者說不是用喝的方式來閱讀的書,應該是用品嘗的方式來閱讀的書。喝是迅速的,但是味覺是少量的;品嘗是慢條斯理的,但是味覺是無限的。
埃斯普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語法的,而這個世界是被語法規定好的,世界對於人來說就是一個無法擺脫的困境。而語法,在這部書中意味著很多,是權力,是歷史,是現實等等,糟糕的是它們都是一個又一個的陷阱。這也是今天的主題,失憶的個人性和社會性。埃斯普馬克的這部小說,既是觀察自己的顯微鏡,也是觀察社會的放大鏡。
埃斯普馬克比我年長三十來歲,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文化里,可是《失憶》像是鬧鐘一樣喚醒了我一些沉睡中的記憶,有的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證書的記憶。我想這就是文學的意義,這也是我喜歡《失憶》的原因。
我在此舉一個例子說明。書中的失憶者始終在尋找一個L的妻子(也許仍然是一個臨時妻子),失憶者幾乎完全忘記了L的一切,但是“我的感官記住了她的頭髮垂下的樣子” 。
女性的頭髮對我和埃斯普馬克來說是同樣的迷人。時尚雜誌總是對女性的三圍津津樂道,當然三圍也不錯。然而對於埃斯普馬克和我這樣的男人來說,女性頭髮的記憶比三圍美好得多。我有一個真實的經歷,我二十來歲的時候,沒有女朋友,當然也沒有結婚,曾經在一個地方,我忘記是哪裡了,只記得自己正在走上一個台階,一個姑娘走下來,可能是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急速轉身時辮子飄揚起來了,辮梢從我臉上掃過,那個瞬間我的感官記住了她的辮梢,對於她的容貌和衣服的顏色,我一點也想不起來。這應該是我對女性最為美好的記憶之一,可是我竟然忘記了,畢竟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埃斯普馬克讓這個美好的記憶回到我身旁。
謝謝你!埃斯普馬克。
還有你,萬之,我的老朋友,你的譯文棒極了!昨晚我和思和一起讚揚了你中文的敘述才華。二十多年前你從北京坐上火車搖搖晃晃去了挪威,然後又去了瑞典,開始了你遠離中文的漂泊生涯。可是讀完中文版的《失憶》,讓我覺得你一天也沒有離開過中國,我懷疑你在遙遠北歐的生活是你虛構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