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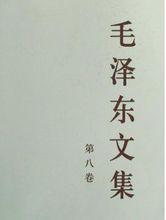 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關於調查工作》這篇文章,我不贊成現在公開發表,只在內部印給大家看看就是了。有同志說這是幾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幾段。這篇文章現在的作用在什麼地方呢?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會不懂得。為什麼呢?因為文章講的是當時民主革命的問題。民主革命時期依靠些什麼人,團結些什麼人,打倒些什麼人,這是反帝反封建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必須要向看文章的人說明這一點。
我在印發這篇文章的批語中說,這篇文章看來還有些用處,不是講全部有用。我說有一些用處,就是講文章中心點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很不容易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是在龍巖開的,推翻了正確路線,提出了一條錯誤的路線。第八次代表大會是在上杭開的,還是維持錯誤的路線。到第九次代表大會才恢復正確路線。
文章第二節講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這中間批評了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幹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是講四中全會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劉安恭為首,他和一些人剛剛來就奪取軍權,軍隊就落到了他們手裡。他們一共四五個人,都當了前委委員,直到第九次代表大會。後來中央來信,說他們挑撥紅軍內部的關係,破壞團結。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開的,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寫的,總結了那個時期的經驗。寫這篇文章之前,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不記得了,這兩篇文章我總是記得的。忽然找出一篇來了,我是高興的。那個時候產生這篇文章的詳細過程不必再講了。
這篇文章是為了解決民主革命的問題而寫的,說為了取得民主革命勝利要做調查研究,做典型的調查研究。現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後完成。
第三節講反對本本主義,這裡頭包含一個破除迷信的問題。那個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級的東西就認為是好的。比如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那個東西你拿來如何實現呢?你如果不搞些具體措施,是很難實現的。不要說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有部分的原則性錯誤,即使都是正確的,沒有具體措施,沒有調查研究,也不可能實現。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檔案,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
第四節講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現在呢?現在我們還是要做階級分析,無論城市或農村,都不能離開階級分析。最近,中央的檔案提到農村要建立貧農、下中農代表會,需要重新奪取政權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強有力的貧農、下中農代表會,因為現在還存在著階級。剝削階級,在我國大部分地區是被消滅了。地主資產階級被消滅了,但是不是一點也沒有了?要做調查研究,可能還在有一些地方沒有打倒,還在當權。大體上說,從去年十一月開始,過去的五個月,我們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現在再把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恰當地解決了就好了。至於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這一點平均主義還要。農民自己說,人是有眼睛的,不會看著他們餓飯,不照顧他們。有一位同志在小組發言講,現在的核心問題還是爭取農民,把農民團結在黨的周圍,這話說得好。我們中國有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農村,城市只一億多一點,農村五億多,一與五之比。沒有農民擁護,不管你修多少鐵路,搞多少鋼鐵,也會搞翻的。
第五節講調查工作的縱斷法和橫斷法。這兩個名詞我只用了一次,寫出這篇文章之後我自己也沒有再用過。我也不希望同志們以後寫文章、講話再用它,因為不好懂。縱斷法的特點是什麼呢?我在文章里說:“近來紅軍第四軍的同志們一般的都注意調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調查方法是錯誤的。調查的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賬”。只是收集許多材料,沒有觀點,沒有思想,“像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頂上看城郭,只能看見很小很窄的街道,許多房屋,街道上有許多人往來。至於這些人是些什麼人呢?是資本家還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產黨員還是非共產黨員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還是女人都分不清楚。這種調查結果是無益於實用的。這是縱斷調查法。這種調查法可以作我們的輔助手段,達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們的主要手段,不能達到我們的主要目的。我們的調查工作,不能停止於縱斷法,而要用橫斷法,就是要做階級分析,要做典型調查。
第六節講的內容,我看現在還有不少用處,將來也用得著。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不能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國同志幫助我們打勝仗。寫這篇文章時還沒有料想到後來的王明路線,當時立三路線也還沒有出現,瞿秋白同志的盲動主義是有了。我們黨有一個時期依靠共產國際為我們寫決議,作指示,寫綱領,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就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們寫的。
底下是第七節,講調查的技術,也就是調查的方法。第一點是要開調查會,做討論式的調查。你可提出幾個方案,跟他們討論,跟他們研究,這個方案好,還是那個方案好。要做討論式的調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確的結論。第二點是講調查會到些什麼人。各種人都要,經驗多的人要,經驗少但思想進步的人也要。從職業上說,工人也要,農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識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點是講開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處,但開調查會人太多了比較困難。第四點是講調查的綱目。綱目要事先準備,按綱目發問,這就要有一定的時間。第五點是講要親身出馬。這裡講,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都要親身出馬。我講得很寬,那個時候也有點無法無天了。一定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我們那個時候得到經驗了,知道不能單靠書面報告。第六點是講要從個別問題深入,深入解剖一個麻雀,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全國了解兩個鄉,南方一個,北方一個,對中國的農村就有一個基本概念了。
工業不同,要分行業。比如煤礦、冶金、機械等,各了解一個廠礦就差不多了。煤礦,中央有四百多個,你去全面徹底地了解一個就好辦了,別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機械行業也是這樣去了解一個工廠。這是重工業,還有輕工業,工業比農業複雜一些。深切地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往後調查別處地方或別個問題,你就容易找到門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門路。第七點是講要自己做記錄。那個時候還是我精力充沛的時候。現在調查要我做詳細的記錄,也許還可以,我想試試看。自己當記錄,這是調查的一個要點。不但要自己當主席,適當地指揮調查會的到會人,而且要自己當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於人是不行的。現在我不反對派調查組結合當地同志進行調查,這回我就派了三個調查組,一個放在浙江,一個放在湖南,一個放在廣東,結合當地省委的同志來搞。我是間接的,並沒有直接調查。現在有這樣的便利條件,過去這樣的調查難於辦到,那時我們全部人馬只有幾千人。
至於第一節講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大家都熟悉了。這個口號,就是那時候提出來的。這一次有兩個問題,一個手工業問題,一個商業問題,因為沒有調查,我就沒有發言權。我總是不相信沒有調查會有發言權的。
我們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調查研究不夠。建國後這十一年我做過兩次調查,一次是為合作化的問題,看過一百幾十篇材料,每省有幾篇,編出了一本書,叫做《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有些材料看過幾遍,研究他們為什麼搞得好,我調查研究合作化問題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還有一次是關於十大關係問題,用一個半月時間同三十四個部門的負責人討論,每天一個部門或兩天一個部門,聽他們的報告,跟他們討論,然後得出十大關係的結論,這是向上層人們,向各部部長調查。
現在全黨對情況比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級對下面的情況比較摸底了,我看應該這樣說。為什麼又講不甚了了呢?比較摸底,但還是不甚了了,我是講“不甚”,不是講你全不了了。現在局勢已經是有所好轉,但是不要滿足,不要滿足於我們現在已經比較摸底、比較清楚情況,要鼓起民眾的幹勁,同時鼓起幹部的幹勁。幹部一到民眾裡頭去,幹勁就來了。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頭不了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雲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有辦法,大家回去試試看。
這幾年出現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因為我是主席。我的責任在什麼地方呢?為什麼到現在才提倡調查工作呀?為什麼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查。為補過起見,現在我來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過一次,九中全會上又講了一次,這次會議還得講一次,不然又說我沒有講。有些問題得當面交待一下。比如這篇《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發下去的時候要向同志們解釋一下,文章主要是講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個方法是可取的。至於調查研究為了解決什麼問題,這篇文章是為了解決民主革命的問題,現在就不是解決這個問題,要講清楚這一點。此外,還有什麼橫斷法、縱斷法之類的名詞,可以不用。本本主義,現在叫教條主義,赫魯雪夫他們講我們不反對教條主義,恰恰相反,我們從來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是我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反對教條主義。教條主義這個東西,只有原理原則,沒有具體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而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
這篇文章還提出這么一個觀點,就是說,正確的策略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只能來源於調查研究。所謂策略路線是包括很寬的,包括政治路線的。比如,依靠些什麼階級,聯合些什麼階級,打倒些什麼階級,就屬於策略路線的問題。文章講到商業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對這兩個階級我們的認識始終模糊,就是寫文章這個時候,還是模糊的,對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策,沒有正確的政策,因為我們沒有做這方面的調查。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現在印出來是一個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這本書不知厚多少倍。列寧的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他用好幾年時間研究哲學史才寫出來的。列寧寫這本書是為了批判當時的唯心主義造神派的“經驗批判主義”。
我那篇文章批評社會科學研究專從書本子裡面討生活是危險的。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正是失敗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一些知識分子倒退了,蛻化了,變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他們專從書本里討生活,不到工人、農民、社會中去調查,不到民眾中去調查,不在鬥爭中逐步深入調查研究。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的軍事學。有人講我的兵法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孫子兵法》當時我就沒有看過。在遵義會議上,凱豐說:你那些東西,並不見得高明,無非是《三國演義》加《孫子兵法》。
我就問他一句:你說《孫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請你講講。他答不出來。我說:你也沒看過,你怎么曉得我就熟悉《孫子兵法》呢?凱豐他自己也沒看過《孫子兵法》,卻說我用的是《孫子兵法》。那時打仗,形勢那么緊張,誰還管得什麼孫子兵法,什麼戰鬥條令,統統都忘記了的。打仗的時候要估計敵我形勢,很快作出決策,哪個還去記起那些書呢?你們有些人不是學過四大教程嗎?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嗎?如果那樣就完全是教條主義嘛!我不是反對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我這篇文章裡頭也講了的。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不合用,只有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就是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問題上成為歷史唯物主義,才合用。馬克思創立了許多學說,如黨的學說、民族學說、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文學藝術理論等等,也都應噹噹作合用的工具來看待。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寫的《農村調查》的序言中,說到我自己做調查的態度,是必須恭謹勤勞,把人家當作同志對待。有了平等的態度,當小學生的態度,才能夠調查到一點東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你有什麼法子呢?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尋烏縣做了個調查。這個調查,我都找了些什麼人呢?找了幾個中下級幹部,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縣衙門管過錢糧的小官吏,還有一個窮秀才,此外就是尋烏縣的縣委書記。我們幾個人,談了好幾天。那些人可有話講啦!他們把那裡的全部情況,尋烏的工商業情況,各行各業的情況,都跟我講了。那個秀才,年紀相當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講了許多事情。
我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中還說過,第一次使我曉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誰呢?就是湖南衡山縣的一個獄吏。我跟他談了一兩天,他談我記。我首先講明來意,就是要調查究竟這個班房裡頭情況怎么樣,他就講了各種複雜情形。可惜這個調查材料沒有了。上井岡山後的兩次典型調查材料也損失了。損失別的不傷心,損失了這些材料我比較傷心。此外,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我發動各省來的學生抄寫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還有一個人抄寫了幾十首的。其中包括內蒙古、黑龍江的,只是沒有青海、新疆的。我對他們說:你們抄寫民歌,我發紙,每人發幾張紙。一個人長到十幾、二十幾歲,總能記得一些民歌。從這些民歌裡面可以懂得許多東西。這幾千首民歌后來丟了,非常可惜。
相關資料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福建龍巖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在關於黨的領導、思想政治工作、農村根據地、紅軍任務等問題上發生了爭論。會議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會議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前委書記。
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開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討論紅軍法規等問題,會議開了三天,由於認識不一致,未獲結果。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總結了紅軍創建以來黨在同各種錯誤思想、錯誤傾向作鬥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統一了思想認識,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案提出了建黨建軍的根本原則。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書記。
劉安恭(一八九九――一九二九),四川永川人。一九二九年被中共中央指派為中央特派員,到紅四軍指導工作。後擔任中共紅四軍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等職。在紅四軍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前敵委員會委員。
《關於調查工作》原文第五節中有“我們的主要調查方法是‘橫斷法’而不是‘縱斷法’”一句。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時,經作者校訂刪去了。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是毛澤東一九五五年主持編輯的。這部書共收入反映各地農業合作化情況的材料一百七十六篇,毛澤東為其中一百零四篇寫了按語,並為全書寫了序言。該書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彭德懷(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總指揮和前委書記。
赫魯雪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當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遵義會議,指長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凱豐,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青年團中央局書記、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