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範圍
 古文字學
古文字學廣義
既包括對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對各種古文字資料的研究。後一方面的研究繼承了金石文字之學的傳統﹐主要以各種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古文字資料(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等)為對象﹐著重於釋讀這些資料﹐弄清它們的性質﹑體例和時代﹐並闡明研究這些資料的方法﹐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認為應該稱為古銘刻學。在廣義的古文字學裡﹐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視為重點。狹義
主要以古文字本身為對象﹐著重研究漢字的起源﹐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演變﹐字形所反映的本義以及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狹義的古文字學是文字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範圍
種類
古文字資料的種類很多。按照所研究的資料的範圍﹐古文字學已經形成了甲骨學(以研究殷墟甲骨卜辭為主)﹑殷周銅器銘文研究﹑戰國文字研究﹑秦漢簡牘帛書研究(如去掉“秦漢”二字﹐可以包括對戰國簡冊帛書的研究)等分支。關係
古文字學跟不少學科有密切關係。它跟考古學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古文字資料有很多是考古發掘所提供的﹐而且發掘記錄對這些資料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用處。反過來看﹐這些資料對判斷有關墓葬或遺址的性質和時代﹐也往往能起很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器物上的銘文對研究這些器物本身也極為重要。要考釋古文字或通讀古文字資料﹐語言文字學方面的知識是必不可少的。舉例說﹐如果不懂先秦語音﹐對先秦古文字資料里的通假現象就無法正確理解。反過來看﹐古文字資料和古文字本身﹐對研究先秦以至秦漢的語言也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例如要研究商代語言﹐就幾乎只能根據商代的古文字資料。古文字的字形對研究上古的詞義和語音也有很大用處。古文字在文字學上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說了。此外﹐古典文獻學﹑古史(包括古文化史)學以至民族學等方面的知識﹐對通讀古文字資料和考釋古文字也都是需要的。同時﹐古文字資料和古文字本身﹐也都能為這些學科提供重要的研究根據。在古文字學和上述各種學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互促進的關係。發展史
漢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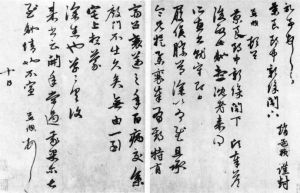 古文字學
古文字學漢代推崇古文經的那一派經學家﹐後人稱為古文學家。另一派經學家﹐反對古文經﹐只相信世代相傳的本子﹐後人稱為今文學家。古文學家為了讀通古文經﹐必須從文字學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時是文字學家。他們進行了收集古文並把古文跟當時使用的文字相對照的工作﹐有些人還進一步對漢字的構造進行了理論上的研究。《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古今字》和《隋書‧經籍志》等著錄的後漢衛敬仲(即衛宏)撰的《古文官書》等書﹐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書說的建立是後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屬於古文經系統的《周禮》。不過據近人研究﹐把六書解釋為“造字之本”﹐大概是漢代古文學家的創造。公元1世紀末﹐許慎撰寫《說文解字》﹐為古文學家對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總結。
《說文》收字的體例是“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為主﹐同時收入一些寫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釋文字的時候﹐許慎依據六書理論﹐儘可能結合字形指出字的本義。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為古文字的傳統文字學的觀點來看﹐許慎的工作也是帶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質的。可惜許慎等古文學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資料﹐時代都比較晚。在當時雖然古銅器銘文已經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這種資料的風氣卻還沒有形成﹐學者們很難加以利用。《說文》敘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書中所收的古文看來全都出自古文經﹐實際上只是戰國時代的文字。籀文的時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許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屢經傳抄的本子﹐有些字形顯然已經訛變。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義。因此許慎對古文字的發展過程缺乏正確的認識﹐他對字形的解釋和所指出的本義也往往不可信。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些缺點是很難避免的。
魏晉至宋初
從魏晉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沒有很大的進展。這一時期最受重視的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學家所說的那種古文。曹魏正始年間將古文學家傳授的《尚書》和《春秋》刻石立於太學﹐每個字都用古文﹑小篆﹑隸書三體寫刻。這就是所謂三體石經。晉武帝鹹寧五年(279﹐或謂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281)﹐在汲郡(今河南汲縣)的一個被盜掘的戰國後期魏國大墓里發現了大量竹簡書﹐共有75卷﹐10餘萬字﹐字型跟古文經相類。這就是所謂汲冢古文。這批竹書被收入官府﹐先後由荀勗﹑和嶠﹑衛恆﹑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寫定為今文。竹書原本早已不存﹐寫定之本除《穆天子傳》外也都已亡佚。據史書記載﹐南北朝時也間有古文簡冊發現﹐但是其內容一點也沒有流傳下來。在從魏晉到宋初這段時期里﹐仍有人繼續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還有人用古文刻寫碑碣或偽造典籍古本。他們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據﹐有的則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據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古文資料編成古文的字彙﹐名為《汗簡》。稍後的夏竦(985~1051)編《古文四聲韻》(1044)﹐材料來源跟《汗簡》基本相同﹐不過《汗簡》是按部首編排的﹐夏書則是按韻編排的。這兩部書雖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還是有根據的﹐是現代人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考資料。郭﹑夏之後﹐古文之學就逐漸衰微了。
在這一時期里﹐有銘文的古銅器也時有發現﹐可惜仍然沒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風氣﹐唐初在天興縣(今陝西鳳翔)發現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對石鼓文很重視﹐講字型﹑書法時往往提到它。由於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較接近﹐當時人多附會為周宣王太史籀所書。秦始皇巡行天下時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視。南北朝時石經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傳。
唐代篆文書法家李陽冰曾整理過《說文》。他根據秦刻石改了《說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為等﹐受到後人的很多批評﹐李陽冰擅改古書是不對的﹐但是他根據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文字資料糾正《說文》﹐這卻是值得重視的。他解釋字形也時出己見﹐雖多荒謬﹐但也間有可取之處。例如許慎解釋“木”字說:“從﹐下象其根”﹐他則認為整個字“象木之形”。
宋代
在宋代﹐由於金石學的興起﹐古文字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真宗鹹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陝西乾縣)所獻“史信父甗”﹐這是宋人研究古銅器銘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錄﹑研究古銅器及其銘文的風氣日盛﹐南宋時﹐關中﹑中原等發現古銅器的主要地區先後為金﹑元占據﹐蒐集新出土銅器的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但由於北宋學風的影響﹐南宋前期著錄﹑研究金文的風氣仍相當興盛﹐到後期就衰落了。宋代學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主要有北宋的楊元明(南仲)﹑歐陽修(1007~1072)﹑呂大臨(1046~1092)﹑趙明誠(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編了不少古銅器和銘文的著錄書﹐流傳至今的有呂大臨《考古圖》(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圖錄》﹑南宋趙九成《續考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1144)﹑王俅《嘯堂集古錄》和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前3種兼錄器形和銘文﹐後3種單錄銘文。呂大臨另編有《考古圖釋文》﹐按韻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彙(或謂此書為趙九成所編﹐似非)。政和年間王楚撰《鐘鼎篆韻》﹐紹興年間薛尚功撰《廣鐘鼎篆韻》﹐材料較呂書增多﹐但皆已亡佚(王書實際上還保存在元代楊的《增廣鐘鼎篆韻》里)。
殷周金文是學者們最早接觸到的早於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學者對金文的蒐集﹑著錄和研究在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他們通過較古的金文已經認識到“造書之初”象形之字“純作畫像”﹐“後世彌文﹐漸更筆劃以便於書”(《考古圖》4‧26上)。《考古圖釋文》的序對金文形體上的某些特點(如筆劃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釋金文的方法作了簡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確釋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較容易認識的。不過他們有時也有很好的見解﹐如楊南仲釋晉姜鼎銘文﹐疑“”為“旂”字﹐讀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學名家吳大澄﹑羅振玉等人以“”為“祈”之本字的說法確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繼續受到重視。南宋前期的鄭樵創石鼓文為秦篆之說﹐認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後始皇以前的刻石。時代稍後的鞏豐認為是秦襄公至獻公時的刻石。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北宋時還發現了戰國時秦王詛咒楚王於神的刻石﹐即所謂詛楚文﹐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書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學的影響。鄭樵《通志‧六書略》對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釋明顯勝過《說文》。例如《說文》說“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書略》則認為“象足趾”﹔《說文》說“步”字“從止﹑相背”﹐《六書略》則認為“象二趾相前後”﹔《說文》說“立”字“從大立一之上”﹐《六書略》則認為“像人立地之上”﹔《說文》說“走”字“從夭﹑止﹐夭者屈也”(從段注本)﹐《六書略》則說“夭”“像人之仰首張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會意字﹐《六書略》卻收在象形類里﹐鄭樵對金石文字頗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類見解﹐顯然是由於受了金石文字中較古字形的啟發。宋元間的戴侗作《六書故》﹐直接採用金文字形。由於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後人的很多批評。不過戴氏說字頗有獨到之處﹐這也是後人所承認的。如他認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從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見解。
元明
元﹑明兩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時期﹐金石學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錄古印的工作。這項工作宋人就開始做了。但是宋元時代的古印譜大都已經亡佚﹐流傳下來的如《說郛》所收的《漢晉印音圖譜》﹐資料貧乏﹐用處不大。明人所編古印譜﹐如顧氏《集古印譜》(1571)﹐內容比較豐富﹐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資料。在這一時期里﹐古文字字彙繼續有人編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據前人之書輾轉摹錄﹐沒有多大參考價值。元初楊桓《六書統》﹑明代魏校《六書精蘊》等書也都想根據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來講六書﹐這些書“杜撰字型﹐臆造偏旁”之病甚於《六書故》﹐而見解則不及《六書故》﹐不為後人所重。
清朝前期
進入清代以後﹐金石學和國小復興﹐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發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漸提高的。清初閔齊伋作《六書通》﹐後由畢弘述整理刊行﹐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鐘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彙﹐流傳很廣﹐但是內容雜亂﹐摹錄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時﹐清高宗先後命梁詩正﹑王傑等人仿《博古圖錄》體例對內府所藏古銅器加以著錄﹐編成《西清古鑒》(1751)﹑《寧壽鑑古》﹑《西清續鑒甲編》及《乙編》4書(後3書稿本民國時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從乾﹑嘉之際開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顯超過前人之處。道光以後﹐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輩出﹐陳介祺(1813~1884﹐號簠齋)是其中的代表。他們收藏的古文字資料在種類﹑數量﹑質量等方面都超過了前人。由於古文字資料的日益豐富﹐同時也由於國小﹑經學等有關學科的發達﹐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斷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緒時期達到了高峰。吳大澄(1835~1902)﹑孫讓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學者。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點仍然是金文。乾隆時﹐由於樸學的興起以及《西清古鑒》等書的編纂﹐士大夫中對金文感興趣的人逐漸增多﹐嘉慶元年(1796)﹐錢坫刻《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專收自藏之器﹐器形﹑銘文並錄。九年(1804)﹐阮元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著錄所收集的各家銘文﹐加以考釋﹐以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此後出現了很多跟錢書或阮書同類的著作﹐影響較大的有吳榮光(1773~1843)《筠清館金文》(1840)和吳式芬(1796~1856)《捃古錄金文》(1895)﹐體例都是仿阮書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學者﹐乾嘉時期可以上舉的錢坫﹑阮元為代表﹐道鹹時期有徐同柏(1775~1854)﹑許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從古堂款識學》(1886)﹐許瀚曾為吳式芬校訂《捃古錄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見解多見於此書。同光時期﹐金文研究出現高潮﹐主要學者有吳大澄﹑孫讓﹑方濬益(?~1899)﹑劉心源(1848~1915)等人。吳大澄跟金文有關的主要著作有《說文古籀補》﹑《字說》等書。《古籀補》是古文字字彙﹐所錄之字以金文為主﹐兼及石刻﹑璽印﹑貨幣和古陶文字﹐釋字頗有出自己見者。此書一改《古文四聲韻》以來按韻收字的體例﹐分別部居悉依《說文》﹐不可釋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於附錄。所錄之字皆據搨本慎重臨摹﹐跟過去那種輾轉摹錄﹐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彙大不相同。後來的古文字字彙﹐在編排的體例上大都仿照吳書。孫讓著《古籀拾遺》(1888)和《古籀餘論》(1929)﹐訂正前人考釋金文之誤。方濬益著有《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後才出版。劉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諸人對金文的考釋有很多超過前人之處。
宋代以來多把春秋戰國時鳥篆之類筆劃屈曲奇特的金文視為夏商文字。龔自珍(1792~1841)曾疑王復齋《鐘鼎款識》著錄的﹑鑄有這類銘文的“董武鍾”是吳越器。方濬益明確指出:“若薛錄之四商鍾﹑王氏所錄之董武鍾﹐要亦周器﹐乃當時自有此一體﹐如秦之有繆篆﹑殳書者”(《綴遺》卷首《彝器說》中)。這是一種進步。在把銘文跟古籍中有關的歷史資料聯繫起來進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過了前人。
清朝中期
貨幣文字真正成為古文字研究的資料是從清代開始的。蒐集﹑研究古錢幣的風氣開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來研究古錢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屬於戰國的東周時代的刀﹑布等類錢幣﹐說成太昊﹑堯﹑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時代的東西﹐解釋幣文極盡穿鑿附會之能事。直到乾隆時撰的《錢錄》(1751)﹐仍然停留在這種水平上。古幣文字的研究出現轉機﹐也在乾嘉之際﹐據蔡雲《癖談》(1827)﹐錢大昕曾說過“幣始戰國”的話﹐嘉慶時﹐初尚齡作《吉金所見錄》(1819)﹐把古刀﹑布斷歸春秋﹑戰國。先秦古幣的研究自此漸上軌道。吳大澄《古籀補》收入了不少幣文﹐劉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釋了一些幣文。乾嘉以後﹐璽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當大的進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於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譜中其實已收入不少戰國印﹐但他們不明其時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瑤田為潘氏《看篆樓印譜》作序﹐釋出戰國印中的“私璽”二字﹐並說“‘璽’但用‘爾’者﹐古文省也”(《通藝錄》卷八《看篆樓印譜敘》)。這是清人辨識先秦古印的先聲。道光十五年(1835)張廷濟(1768~1848)編《清儀閣古印偶存》﹐稱先秦印為古文印。同﹑光間﹐陳介祺編《十鍾山房印舉》﹐在漢印之前列“古璽”和“周秦”印兩類。按其內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國印﹐後者包括戰國時的秦印﹑秦代印和漢初印。陳介祺本認為周秦印是周末與秦代之物﹐古璽是三代之物。光緒四年(1878)﹐他在致吳大澄的信中說:“……朱文銅璽﹐前人謂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見﹐亦似六國文字”(五冊本《簠齋尺牘》第五冊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對古璽時代的認識已接近實際。《古籀補》收入了一些璽文。在漢印篆文方面﹐嘉慶時就有桂馥《繆篆分韻》(1796)等字彙刊行﹐摹錄印文比較謹嚴﹐勝於以前其他各類古文字字彙。
晚清
道光以後還發現了一些古文字資料的新品種﹐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漢代的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發現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於同﹑光間在山東臨淄等地發現﹐稍後又在直隸易州(今河北易縣)等地發現﹐陳介祺是第一個鑑定“三代古陶文字”(實際上大都屬於戰國時代)並加以收藏的人。吳大澄第一個認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據陳介祺藏陶的搨本寫過一些考釋﹐還在《古籀補》里收入了不少陶文。安陽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內容為卜辭)大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開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榮(1845~1900)鑑定為三代古文並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資料豐富﹐內容重要﹐時代屬商代後期﹐早於大多數銅器銘文﹐其發現在古文字學史上有重大意義。王懿榮在鑑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自殺殉國﹐所藏甲骨後歸劉鶚(1857~1909)。劉鶚選拓了一部分甲骨編為《鐵雲藏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出版。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劉鶚在序中已稱甲骨文為“殷人刀筆文字”﹐次年﹐孫讓據《藏龜》寫成《契文舉例》。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專著。此書遺稿由甲骨學的奠基者羅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發現後﹐古董商欺騙收藏家﹐把出土地點說成湯陰。羅振玉是學者中最早打聽到真實出土地點的人﹐宣統二年(1910)﹐羅振玉作《殷商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遺物﹐把甲骨文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他當時認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則是錯誤的)。此書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滅了。
清代金石學的發達﹐在專門研究《說文》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來作解釋。桂馥本是金石學家﹐他在《說文義證》里屢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說文釋例》里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說文》的字形作比較。
隨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漸深入﹐《說文》的一些錯誤就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吳大澄在《古籀補》自序里指出《說文》中古文的形體跟習見的銅器銘文不合﹐懷疑他們皆“周末七國時”文字。陳介祺也有類似看法(《古籀補》陳序)。吳﹑陳二氏還都對《說文》所收的籀文的時代表示了懷疑。從《古籀補》﹑《字說》等書中關於璽文﹑幣文和陶文的一些話可以看出﹐吳大澄已經認識到這些文字資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國”時的東西。他在《古籀補》“二”﹑“鈞”兩字下﹐還明確指出《說文》中這兩個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國銅器銘文相合﹐應是“六國時”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見吳大澄對《說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對戰國文字的研究為基礎的。對《說文》篆形以及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吳大澄﹑孫讓等人也時常根據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補》凡例第一條就說:“古器所見之字﹐有與許書字型小異者……可見古聖造字之意﹐可正小篆傳寫之訛。”
孫讓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寫成《名原》一書﹐從文字學角度總結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於圖象”﹐漢字最初“必如今所傳巴比倫﹑埃及古石刻文﹐畫成其物﹐全如作績(繪)”﹐後來由於書寫不便逐漸簡化﹐“最後整齊之以就篆引之體”﹐才成為《說文》所載的那種文字。書中還很注意把同從一個偏旁的字放在一起來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圈子﹐是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一部著作。
民國以後
到了民國時代﹐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現代的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逐漸形成﹐古文字學也逐漸加強了科學性。民國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學者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振玉對古文字的研究開始於清末﹐不過他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在民國時代進行的。羅氏對甲骨﹑銅器﹑金文拓本﹑璽印﹑封泥等古文字資料都有豐富的收藏。他既勤於著錄﹑傳布各種資料﹐也勤於研究﹑著述﹐貢獻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貞卜文字考》的基礎上寫成的《殷虛書契考釋》(1915)。此書在甲骨文字的考釋和卜辭的通讀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突破﹐為甲骨學奠定了初基。王國維是在羅振玉的影響下開始從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國維新識之字並不是很多﹐但往往對通讀卜辭有重要意義。他的主要貢獻是以甲骨卜辭與典籍互證﹐進行歷史﹑地理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和很多單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經考》﹑《史籀篇疏證》以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桐鄉徐氏印譜序》等文章。他認為古文是戰國時東方六國的文字﹐說法比吳大澄精確﹐此說現已成為定論。至於籀文究竟是不是戰國時秦國的文字﹐古文字學界尚有不同意見。
羅﹑王都已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對舊的金石學有所不滿。羅振玉主張把金石學改為古器物學(《雲窗漫稿‧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王國維曾把前人對古銅器和銘文的研究稱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國朝金文著錄表序》)﹐還時常單獨使用“古文之學”﹑“古文字之學”或“古文字學”的名稱﹐可見他傾向於把金石學分為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客觀存在的趨勢。不過從羅﹑王的研究工作來看﹐他們還未能真正擺脫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
相關研究
獨立學科
20年代以後﹐隨著現代考古學的形成﹐古器物學為考古學所吸收﹐古文字學正式成為獨立的學科﹐並且在考古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影響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發掘殷墟﹐古文字資料的出土情況開始由盜掘和偶然發現變為科學發掘。雖然由於盜掘無法禁止﹐這種轉變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義仍然十分巨大。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現了劃時代的變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為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性質開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鑑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根據器物的形制﹑花紋和銘文的字型﹑內容﹐對西周王朝的銅器進行區分所屬王世的研究﹐又對周代諸侯國銅器(大部屬於東周時代)進行分國的研究﹐寫成了《兩周金文辭大系》這部名著﹐建立了銅器銘文研究的新體系。他還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去研讀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對它們的某些內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辭通纂》和《殷契萃編》﹐在卜辭的通讀上有重要貢獻。他在收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1931)這篇論文裡﹐指出殷周銅器銘文中的很多“圖形文字”是“國族之名號”﹐一掃過去把這類文字任意釋為“子”﹑“孫”等字﹐或視為非文字的圖畫的謬說。
與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銅器銘文同時﹐參加殷墟發掘﹑負責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賓﹐對甲骨文也進行了分期斷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寫成﹑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里﹐全面論述了殷墟甲骨文斷代的根據﹐把甲骨文時代劃分為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學的水平。後來他還在甲骨文斷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補充的意見﹐如新﹑舊派的劃分等﹐這些意見引起了不少爭論。
清代以來﹐雖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卻一直沒有人認真加以探討。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語言文字學上缺乏修養﹐主要憑想像去考釋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釋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於一般文字學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時吸收古文字學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學也長期不能從一些有問題的舊觀念中解脫出來﹐唐蘭針對這種情況﹐在1935年寫成了《古文字學導論》。此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場去研究文字學”。第二部分闡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特彆強調了偏旁分析法和歷史考證法的重要性。這是古文字學的第一部理論性著作。郭沫若﹑董作賓等人從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體上屬於古銘刻學的範圍。唐蘭則把古文字學看作文字學的分支﹐把它跟古銘刻學(他稱為古器物銘學)區分了開來。不過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通過上述這幾位學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努力﹐古文字學終於擺脫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呈現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學史分作古代﹑近代﹑現代3段﹐也許可以把漢代到清代道鹹時期劃為古代﹐清代同光時期到20世紀20年代劃為近代﹐20世紀30年代以後劃為現代。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學發展的勢頭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學的發展也受到了一定影響。
大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考古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出土的古文字資料不但數量多﹐內容重要﹐而且絕大多數有科學的發掘記錄。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來越重視考古學所提供的有關知識﹐使他們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學性都有了增加﹐在新發現的資料里﹐有些品種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其中有的過去從來沒有發現過﹐有的雖然在古代曾經發現過但沒有實物遺留下來﹐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戰國間的“盟書”(民國時代曾有少量發現﹐但當時不明其性質)﹑戰國竹簡以及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等。這些資料的發現為古文字學開闢了新的領域。一些舊領域的研究工作﹐也由於新資料的發現而有了很大進展。以上對民國時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古文字學發展的大勢﹐作了一個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幾個重要研究領域為綱﹐簡單地補充一些這一時期古文字研究的情況。
甲骨學
先補充甲骨學方面的情況。在甲骨文字的考釋方面﹐羅振玉﹑王國維之外還有不少學者作出了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是唐蘭和於省吾。唐蘭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是《殷虛文字記》(講義本1934﹐新版1981)﹐於省吾的是《甲骨文字釋林》。在甲骨文斷代研究方面﹐對董作賓的意見作出補充和糾正的﹐主要有胡厚宣﹑陳夢家和日本的貝冢茂樹。貝冢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和伊藤道治合寫的《甲骨文斷代研究法的再檢討》(《東方學報》京都第23期﹐1953)。陳夢家的研究成果包括在他的《殷虛卜辭綜述》里。70年代晚期開始的李學勤等人跟蕭楠等人關於“歷組卜辭”時代問題的爭論﹐還沒有得到結論﹐但是對甲骨文斷代的研究已經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此外﹐在甲骨卜辭的文例﹑語法以及歷史﹑地理等方面問題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學者取得了成績。甲骨學的通論性著作以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為最重要。甲骨文字彙等工具書﹐主要有王襄(1876~1965)《簠室殷契類纂》(1920﹐增訂本1929)﹑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孫海波(1910~1972)《甲骨文編》和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1965)。日本島邦男(1907~1977)的《殷墟卜辭綜類》是一部有創造性的工具書。此書根據甲骨文的字形特點分部排字﹐除部分極常用的字外﹐每個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樣摹出含有這個字的所有卜辭﹐極便於研究者使用﹐1979~1983年出版了郭沫若為主編﹑胡厚宣為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這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著錄書﹐共13冊﹐收甲骨4萬餘片。70年代以前已著錄的有研究價值的甲骨文資料﹐大抵都已收入此書。傑出人物
在殷周銅器銘文的研究方面﹐除郭沫若外﹐作出比較重要貢獻的還有唐蘭﹑陳夢家﹑楊樹達﹑李學勤和日本的白川靜等人﹐唐蘭有《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2輯)等論文。陳夢家的主要著作是《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9冊至1956年第4期﹐未完)。楊樹達的主要著作是《積微居金文說》。白川靜的主要著作是《金文通釋》(1964~1984)。唐蘭和李學勤在西周銅器斷代問題上跟郭沫若有較大分歧。金文字彙等工具書有容庚的《金文編》﹑周法高主編的《金文詁林》(1975)及其《附錄》(1977)與《補》(1982)。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大型金文著錄書《殷周金文集成》預計收銅器銘文萬件以上﹐1985年已出了第一冊。《甲骨文合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的出版﹐對古文字研究無疑會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其它貢獻
在殷周時代的某些甲骨﹑銅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種用6個或3個數字組成的符號﹐其意義長期以來沒有確解。張政烺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4期)等論文中證明它們是易卦﹐解決了古文字學上的這個懸案。在民國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這一時期里﹐戰國文字的研究逐漸發展成為古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對研究戰國文字很有用的兩種古文字字彙﹕羅福頤(1905~1981)《古璽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編的《古璽文編》是修訂此書而成的)﹑顧廷龍《古陶文錄》(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編的《古錢大辭典》﹐為研究戰國幣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長沙戰國楚墓里發現了一件寫有近千字的帛書﹐這是戰國文字的重要新資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說文古籀補補》﹐值得在這裡特別提一下。此書釋出了不少戰國璽文﹐可惜由於缺乏論證﹐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古璽文字徵》就沒有吸收此書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一方面由於在民國時代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一方面由於楚簡等重要新資料不斷發現﹐戰國文字的研究迅速發展起來。通過朱德熙﹑饒宗頤﹑李學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對戰國銅器﹑竹簡﹑帛書﹑璽印﹑貨幣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王國維把戰國文字分成秦國和六國兩系﹐戰國文字研究已經進入了分國研究的階段。研究者對戰國文字的認識已經比過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帛書的研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隨著這些新資料的發現而興起的。70年代發現的幾批重要資料﹐如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和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畢﹐正在陸續刊布。此外﹐又發現了一些重要的新資料。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無疑會有很大的發展。
![古文字學[概念] 古文字學[概念]](/img/4/8f8/nBnauM3X4IDMxAzN0QzN1MTN2QTM5QDM0YzMzQTNwAzMwIzL0czLx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