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北京談話》BEIJING TALKING
《北京談話》是著名旅法中國女歌手寶羅、蘇放為製作人的中國的第一支新古典主義黑潮世界音樂組合,這支樂隊在2002年剛成立就被北京最大的英文雜誌《that’s Beijing》推薦為北京最值得去看的5個現場樂隊之一。
 BEIJING TALKING
BEIJING TALKING發展歷史
新古典主義?世界音樂?融合?宗教?新世紀?
《北京談話》BEIJING TALKING是誰?
寶羅和蘇放,是十幾年前就以低調聞名於北京獨立音樂圈中的兩個隱士般的音樂人,《北京談話》,是這個多年隱居的雙人組合的名字,多年來由於兩人都很低調,不事張揚,而且都多年來一直把“在音樂之外享受人生”放在生命的第一位,所以多年來,他們很少出來演出,即使演出基本上一年也只演一場,純粹為享受而“音樂”一次,很多獨立音樂愛好者因此都說
 如同音樂會般的氛圍
如同音樂會般的氛圍即使如此,這個2002年只在北京公開演出過2場小型現場音樂會的音樂組合卻在2003七月就被國內最大的英文雜誌《THAT’S BEIJING》評為5個北京最值得去看的現場樂隊之一,而且被推為了這5個樂隊中的第一位。並且第二場演出露面之後就立即被歐州著名的文化機構-亞洲文化中心邀請到歐洲大型城市露天音樂節作70分鐘的專場音樂會演出並受到歡呼和追捧,西班牙電視台同時將這場演出做了現場直播,其音樂質量可見一斑。
寶羅,90年代初就以一個美貌的光頭朋克女歌手的形象聞名於北京搖滾音樂圈。1987年寶羅剛以流行樂出道就獲獎於中國的首次全國流行音樂大賽-中央電視台首屆青年歌手大獎賽的第四名,1990年與流行音樂分道揚鑣,加入了北京著名的另類音樂-自我教育樂隊進入了搖滾音樂圈,並以低調而反叛的美貌女歌手形象聞名於圈內,1995年寶羅以大陸地下搖滾歌手中“第一個”的身份登上了主流的中央電視台的東方時空“九五新歌” 欄目,以《諾言》和《哪裡天涯有鮮花》兩首MV受到獨立音樂界乃至全國性的矚目和讚揚,寶羅1996年簽約於當時的全球第二大唱片公司-Warner music international集團。之後,2002年組建《北京談話》樂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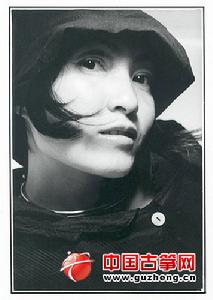 歌手寶羅
歌手寶羅蘇放,一個35歲時才改行做音樂的人,只花了6個月的時間就製作出簽約世界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寶羅第一張大碟,並在平生的第三次登台時就登上了歐洲大型露天音樂節的超級舞台放聲歌唱,離開圈子多年,卻沒有離開社會的視線,仍不時現身於《時尚COSMO POLITAN》《SELF悅己》等眾多國內一線大牌女性時尚雜誌,是為數不多的游離於音樂圈外但圈內人都知道的詞曲唱作全能的融合音樂的著名製作人之一,2002年就已經入選於798藝術區介紹國內藝術家的專著《純粹》一書。有趣的是:2010年的北京談話的現場演出還可能將首次出現寶羅蘇放合作的中國大陸第一支純正的salsa、meringe、samba等拉丁跳舞音樂的中文原創曲目。
Alain Mahé,法國音樂家,一個因用石頭來演奏出音樂而聞名巴黎的著名的新電子聲音的法國音樂家,曾在歐洲各地和世界各地與多位大師合作演出,他將在與寶羅蘇放的這次合作中首次在北京為中國聽眾端上用石頭造就的一道新聲音的大菜。
北京談話2002年開始在北京登台,他們的過去的演出傳統是:一年基本上就只演一次,絕不炒冷飯,每次演出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全新的。
 寶羅投入的演出
寶羅投入的演出《北京談話》在2002年的兩次作品發布會式的演出後就被歐洲文化機構邀請到歐洲的大型露天音樂節做大型的專場音樂會演出,並受到大批歐洲獨立音樂愛好者的喝彩和追捧。
樂隊特質
樂隊的音樂特質是本著民族文化中的血液性的鏇律感,融和古典音樂、阿拉伯音樂、印度音樂、非洲部落的原始鼓聲、教堂傳統的聖經式吟唱。製作人蘇放刻意營造的空靈、幻夢的音樂意境加上寶羅變化多端的音色和“清吟”般的返璞歸真的清澈與透明,在國際和聲里演繹民謠味道的方式形成直抵人性傷口的力量。來自歌者情感坦誠、簡約的表達,百鍊鋼成繞指柔,正是《北京談話》的震撼所在。
作品
 音樂會海報
音樂會海報成員介紹
寶羅

寶羅:主唱,製作人
蘇放:製作人、人聲。打擊樂、鍵盤、音效
評價

人們稱寶羅為中國“唯一的”搖滾女歌手,那也許是就她的行為方式而言。寶羅做過流行歌手,在80 年代轟轟烈烈的流行歌壇,飛過,無痕。直到她忽然以剃光頭的造型再度出現,開始唱自己的歌,在一些小型的演唱會上演唱,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聽到,但是只要聽到,就不會忘記,她的歌聲給人的記憶就像“有什麼碎了,再難癒合”。在她參與的眾多小型演出中的一次,她穿著白色連衣裙,無伴奏歌唱沒有字詞的“聲音”,一邊唱,一邊像小女孩跳繩一樣在台上蹦跳。這就是寶羅的風格,《天堂之聲》里收錄了她的無詞句追求純感性的清唱,“她拋棄了所有的樂器,只讓自己孤獨的嗓 子安靜流淌”。
此種女聲的情感訴求:天籟、出塵、幻想,純潔。《天堂之聲》里甚至有寶羅的歌詞朗誦,它也許想說:音樂可以沒有歌詞,也可以沒有曲子,只要它,發自心臟。 《天堂之花》寶羅
人們稱寶羅為中國“唯一的”搖滾女歌手,那也許是就她的行為方式而言。寶羅做過流行歌手,在80 年代轟轟烈烈的流行歌壇,飛過,無痕。直到她忽然以剃光頭的造型再度出現,開始唱自己的歌,在一些小型的演唱會上演唱,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聽到,但是只要聽到,就不會忘記,她的歌聲給人的記憶就像“有什麼碎了,再難癒合”。在她參與的眾多小型演出中的一次,她穿著白色連衣裙,無伴奏歌唱沒有字詞的“聲音”,一邊唱,一邊像小女孩跳繩一樣在台上蹦跳。這就是寶羅的風格,《天堂之聲》里收錄了她的無詞句追求純感性的清唱,“她拋棄了所有的樂器,只讓自己孤獨的嗓 子安靜流淌”。
此種女聲的情感訴求:天籟、出塵、幻想,純潔。《天堂之聲》里甚至有寶羅的歌詞朗誦,它也許想說:音樂可以沒有歌詞,也可以沒有曲子,只要它,發自心臟。
人們稱寶羅為中國“唯一的”搖滾女歌手,那也許是就她的行為方式而言。寶羅做過流行歌手,在80 年代轟轟烈烈的流行歌壇,飛過,無痕。直到她忽然以剃光頭的造型再度出現,開始唱自己的歌,在一些小型的演唱會上演唱,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聽到,但是只要聽到,就不會忘記,她的歌聲給人的記憶就像“有什麼碎了,再難癒合”。在她參與的眾多小型演出中的一次,她穿著白色連衣裙,無伴奏歌唱沒有字詞的“聲音”,一邊唱,一邊像小女孩跳繩一樣在台上蹦跳。這就是寶羅的風格,《天堂之聲》里收錄了她的無詞句追求純感性的清唱,“她拋棄了所有的樂器,只讓自己孤獨的嗓子安靜流淌”。
此種女聲的情感訴求:天籟、出塵、幻想,純潔。《天堂之聲》里甚至有寶羅的歌詞朗誦,它也許想說:音樂可以沒有歌詞,也可以沒有曲子,只要它,發自心臟。
寶羅,蘇放:愛人同志
寶羅:音樂家
蘇放:音樂家
——他們的關係非常明朗,曾經是愛人,而現在,是同志,排除了肉體交流的精神夥伴。
命中有所注定
蘇放第三次念到花名冊上的名字“王笑梅”時,依然無人應和,只好挨個查看大巴車裡的每一個人頭,只見一小女孩戴著一副恨不能將臉全部埋進去的大墨鏡,兩腿翹在開啟的窗戶上,塞著耳機,一幅愛誰誰的樣子。
那是1986年,走穴的歌手見了組織演出的穴頭,哪一個不是笑臉相迎?惟獨她不理睬。
在遇到命中注定需要她用整個青春時代與之相糾纏的那個男人之前,寶羅還只是一個叫做王笑梅的小女孩,從國小習各類樂器,體內天生流淌著為藝術而躁動的血液,在遭到人生第一拳出其不意的打擊——因為身高所限而被所有文藝院校拒絕在大門外——她很快學會了用不合作的方式對這個因為規則而變得荒謬的社會,抱以反叛和懷疑。瘋狂的念頭擠滿了她的腦子,冷的面孔,還有那時被正常人看作老氣橫秋,同道中人眼裡卻仙氣十足,充滿藝術氣質的著裝。儘管命運及時安排了一塊糖果順利滑入她的口中,以便讓她不要過早地非難生活——她獲得了第一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優秀歌手獎,並藉此機會成為中央台的特邀演員,被冠以歌手的身份。
就是這個不聽話的小女孩在後來的合作中成了整天尾隨蘇放身後的影子。她是那么年輕,才17歲,剛剛從安徽來到北京,一切都是新鮮而又陌生的,她又那么任性,從來不會對哪一個男人一見鍾情,只對溫柔妥協。
年長七歲,有著食草動物般溫和性情的蘇放很快充當了哥哥的角色,照顧她保護她,而她習慣並且依賴了這種照顧和保護。其實,在長達十年的伴侶關係中,她一直都是他捧在掌心的小女孩,而他則因為她迅速成長為兄長,父親,丈夫,情人,經紀人和音樂搭檔。
水瓶座的蘇放骨子裡從來都不缺少理想主義的因子,儘管他現實生活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強得多,但對他來說,那也不過是掌握得還算不錯的一門熟練工種,真正入他眼讓他著迷的竟是些與柴米油鹽不著調的東西。還在大學中文繫上學時,就被班裡女生集體評為全班最不靠譜的男生,完全是一個飄著的人。畢業後,一面在一本園藝雜誌上班,一面玩他喜歡的東西,並且成為在北京首體第一個搭建舞台組織演出的先驅。
當然,青年時代的蘇放,完全OPEN的那一面還處在休眠期,展現於外人面前的完全是AB血型的另一面:嚴肅,負責,正經,老成持重,給人以安全感。
在寶羅之前,蘇放跟女孩子的交往從不過心。那時,他對女朋友的標準:第一,漂亮,第二,不是一般的漂亮,要有一張與這個現實世界沒什麼關係的脫俗的臉。從當時蘇放對女朋友的要求足以看出,這個男人寫在臉上的溫良恭順也只是他得以將與之相反的另一半自己隱遁的一個安全面具。
寶羅摘下墨鏡的一剎那,蘇放非常震驚,簡直太漂亮了!那種漂亮是在中國是很難見到的,是他一直找一直都沒有找到的那張面孔。一次不打不成交的見面禮成為兩人捆綁式愛情馬拉松的序曲。第一次合作後,寶羅離開北京,繼續四處走穴,兩人開始通信,1988年,寶羅再次來京參加蘇放組織的音樂會。音樂會結束,寶羅留在了蘇放身邊。
寶羅是蘇放的第一個女人。
倚仗才華,又都那么有個性和力量
在蘇放眼裡,寶羅極富音樂天賦,渾身都是敏感的觸角,天生就是一塊藝術胚子,除了藝術,把她放到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格格不入,完全一無是處。而他來到她的身邊,就是為了成全她。
寶羅也厭倦了流行歌手的生活——頻繁出版翻唱專輯,四處走穴,鈔票以流水的速度左手進右手出,毫無節儉,日子在無聊中怒放,又迅速枯萎。1990年,在結束了最後一場赴西藏的演出,寶羅將她的走穴生涯劃上了句號。剃去三千煩惱絲,並一頭扎入地下搖滾圈,作為朋克樂隊“自我教育”的貝斯手和主唱,在當時名燥一時的“白紙房”,“馬克西姆”等地兒演出。那時,光頭寶羅是如此耀人眼目,“另類”這個詞也還未像今天這般成為流行。
蘇放結集當時北京搖滾圈的優秀音樂人,組成創作班底為寶羅打造新的音樂。嘗試的結果並不理想,在搖滾圈浸染了三年後,寶羅和蘇放決定離開。
1993年,蘇放將一台電腦,一個合成器,一個鍵盤抱回家,決定和寶羅自己做音樂,那一年,兩人基本完成了唱片《天堂之花》里所有作品的小樣。這期間,蘇放給寶羅製作了十分詳盡而專業的個人資料,並且順利聯繫到了剛剛搶灘內地市場的香港大地唱片的簽約機會,結果,寶羅迅速簽約又解約。1996年初,因為與製作人意見不和,再一次重複解約風波。兩個全憑自己喜好和感覺來做音樂的非專業人,倚仗才華,又都那么有個性和力量,所有的專業條框和支配都成了令他們感到不自在的束縛,哪怕不要機會,也要掙脫。
2月17日,蘇放35歲生日那天,下了一個賭注般的決定,六個月後,兩人完成了專輯《天堂之花》的所有編曲和錄音,然後將唱片寄往國外唱片公司,五個月後,收到四封要求與寶羅簽約的回信。
沒有比那幾年更完美的時光
蘇放一直在找一個女人,給她定了那么高的標準,結果找到了,漂亮,善良,有才華,又做得一手好吃的飯菜,關鍵是,她在外人眼裡的怪異和乖張和他的節拍是如此吻合,只有她可以讓他毫不猶豫不計後果地瘋狂,哪怕前面是懸崖,他也願意和她一起墜落。
那真是一段危險而過癮的日子,他被她完全迷住了,她就是他的全部世界,每時每刻每分每秒,他都在和她交流,他把所有的話都跟她一人說了,對於其他人,他已失去了對話的欲望。沒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女性朋友,他的眼睛從來不移開她半步。
那時,寶羅留著男人似的短髮,或光頭,剔除了女性所有的嫵媚,完全中性的美。身邊擠滿了追求者,今天亦如此。許多年後,蘇放回憶起當年被競爭者圍攻,還帶著自我解嘲的醋意。可是,即使一千次心顫的誘惑,也不足以讓寶羅離開蘇放,他是多么完美無缺啊,當然,他必需完美,否則何以抵禦他的競爭者?他就是她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手,他是她所需要的一切。
“白色的霧瀰漫在你身旁,泉水正沖洗著你的靈魂,你的眼睛告訴我真實,你要和我融在一起。在天堂美麗的路上,我看著你走,忘卻了我的記憶。你的眼睛告訴我,那就是愛。時光正在飛馳,而你不會消失。每一次我閉上眼睛時,都會看到你的臉。假如我會有信仰,那你就是個奇蹟。恐懼已被你擋在天外,我不再害怕。天堂之花……天堂之花……”——《天堂之花》中女聲旁白
寶羅和蘇放,互相成就了對方的完美初戀。
下部:沒有完美,完美是假的
完美破碎的那一刻
1996年,寶羅簽約“華納”。一切看上去滿意極了。誰也沒料到,因為“華納”高層變動,過百萬的宣傳計畫流產。第二年,《天堂之花》的海外版悄無聲息地上市。寶羅與“華納”再次解約。
彼時,寶羅和蘇放雖還是音樂搭檔,甚至一起一日三餐,兩人的愛情漸漸已名存實亡。
“當我們的關係發展到完美到頭的時候,我發現生活沒有未來了,自己變成了一個假人,不是真的人,好像我在自己的電影故事裡,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主人公。”
“我把他當作我所需要的角色,父親情人搭檔助手,一切,惟獨忘了,他是一個男人。最初我所吸引他的很可能成了後來的缺陷,也許他覺得跟我這樣一個半男不女的人在一起不舒服吧,可我跟他在一起已經習慣了這種狀態,非要叫我女人味,我裝不出來。而且,我總是忍不住地要求完美,音樂要完美,人也要完美,跟你越近的人你越要求他完美。蘇放說得對,沒有完美,完美是假的。”
可是在旁人眼裡,他們就是完美的代名詞。完美破碎的那一刻,朋友甚至比他們更失望,僅存的愛情理想楷模坍塌了。
寶羅和蘇放原本私定成為像薩特和波伏娃那樣的伴侶。依寶羅的個性,說好“三十年不分手”,她是一定會一根筋走到底的,哪怕她也會為誘惑所動,免不了一次小小的出軌,只要危及到兩人關係,再難忍她都會忍下,並且,絕對地坦白。可是她發現,對方的感情閘門一旦對外打開就不再關上。上一秒,她把自己身上張開的刺全部收斂起來,每日守在家裡洗衣做飯,像個試圖用乖順勤勞的美德將自己的男人重新拉回家庭的黃臉婆,下一秒,又會像個心懷嫉恨的尖刻女人一樣忍不住大哭大鬧。那時候,寶羅發現,射手座的自己無論多么自由,多么張揚,依然根除不了骨子裡的傳統。哪怕愛情已經不完美了,她也不要被人偷去誓言的失敗,對,她要贏,她一直都在贏,她受不了失敗。
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
今年四月,寶羅從法國回來,蘇放和寶羅的現男友為她舉辦了一個大PARTY。在高大男友的臂彎里,盤起長發,身著藍色碎格衣衫和黑色裹裙的寶羅像一個嬌柔的小妻子,男友忍不住當著眾人一再親吻她燦若桃花的臉龐,旁邊站著手拿酒杯的蘇放,笑得順其自然,完全看不出妒意的成份。
事實上,蘇放跟寶羅的每一個男友都相處融洽。
不止一人對寶羅和蘇放現在同志式的音樂合作做以曖昧的猜測,只有當事人最清楚不過,他們的關係非常明朗,曾經是愛人,而現在,是同志,排除了肉體交流的精神夥伴。當然,過去的完美十年得以讓他們現在還保有親人的信任和愛護。
身體的溫度大致相同,如果僅用作取暖,更換和忘記都不是多么難,而把另一個進入自己身體的靈魂硬生生拔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對女人來講。寶羅花了五年的時間才做到向另外一個人打開自己,愛一個人的時候不再背有負罪感,才在今天與蘇放的同志式合作中得以安寧。
“法國讓我真正放鬆下來,在那裡,生活很安靜,很坦然,我忽然發現,競爭對我失去了任何意義,爸爸的去世也給我很大觸動,在這個世上,沒有一個人能真正贏得什麼,到頭來,都要走向同一個結局,我對輸贏已經失去了興趣。”
寶羅把每年一大半的時間都給了法國安靜的生活。與此同時,在北京,蘇放遲到的青春正如火如荼——所有新鮮的生活都不妨嘗試一下,上拳擊課,踢足球,跳拉丁,跳弗拉名戈,上網聊天,周末請喜歡的女孩共度良宵。
“26歲認識寶羅時,我迅速長大成人,10年後,我發現,我跟寶羅一樣小,還是個孩子,甚至在某些方面,寶羅比我更成熟。那10年我提前度過了一個男人從40歲到55歲的生活。”
曾經深深地把自己的靈魂相嵌在對方體內的寶羅和蘇放,如今已分離成兩個不同的人,過著節奏不一的生活。當然,他們依然在一起,其實,始終就沒有分開,他們一直在為第二張唱片積累作品,他們組建的樂隊“北京談話”不定期地世界各地演出。就在採訪的前一天,他們還和朋友一起在酒吧跳拉丁舞至午夜兩點,不同的是,第二天拍照,向來早起早睡生活規律的寶羅一直叫嚷著身體酸痛不能再熬夜了,而蘇放則意猶未盡,拍照間隙都忍不住配合音樂扭動腰胯。
音樂合作
邀常靜聯袂演出 受北京談話邀請的常靜
受北京談話邀請的常靜古箏與搖滾樂隊的合作,呈現給大家一種跨越聽覺界限的全新音樂,不再把民樂作為一個區別於其他地區音樂的符號,拓寬了古箏的發展面,讓很多人對古箏有了新的認識,同時感受到多種音樂形式交流、碰撞所能激發的無限潛力和蘊藏的巨大探索空間。古箏加搖滾創造了全新的現代化的民族音樂。合唱《野合萬事興》
 左小祖咒與寶羅合唱《野合萬事興》
左小祖咒與寶羅合唱《野合萬事興》